ж—§й’Ҳзәҝз¬ёз®©дёҺжңӘзјқе®Ңзҡ„зүөжҢӮ
еҲқз§Ӣзҡ„йҮ‘йЈҺжј«иҝҮж·ұе··пјҢйӮ®еұҖзҡ„зӘ—жЈӮиҗҪзқҖз»ҶзўҺзҡ„ж§җеҸ¶пјҢзәўз»ізҪҗдёӯжөҒиҪ¬зҡ„йӣҫж°”жҹ“дёҠдәҶзұій»„иүІпјҢдёҺжЎҲеӨҙзҡ„жЈүзәҝжё…йҰҷзӣёжҳ жҲҗи¶ЈгҖӮжһ—еӨҸжӯЈе°Ҷ新收еӯҳзҡ„зҺ»з’ғзҪҗжҺ’еҲ—ж•ҙйҪҗпјҢй—ЁеҸЈзҡ„й“ңй“ғдјҙзқҖдёҖйҳөиҪ»зј“зҡ„и„ҡжӯҘеЈ°е“Қиө·пјҢдёҖдёӘз©ҝи—Ҹйқ’иүІж–ңиҘҹиЎ«зҡ„иҖҒеҰҮдәәжҺЁй—ЁиҖҢе…ҘпјҢжүӢйҮҢжҚ§зқҖдёҖдёӘз«№зј–й’Ҳзәҝз¬ёз®©пјҢиҫ№зјҳзј зқҖиӨӘиүІзҡ„и“қеёғжқЎгҖӮ
вҖңжҲ‘еҸ«еј жЎӮе…°пјҢвҖқиҖҒеҰҮдәәе°Ҷз¬ёз®©иҪ»иҪ»ж”ҫеңЁжҹңеҸ°дёҠпјҢжҢҮе°–жҠҡиҝҮйҮҢйқўж•ҙйҪҗз Ғж”ҫзҡ„й’ҲгҖҒзәҝгҖҒйЎ¶й’ҲпјҢвҖңжғіеҜ„иҝҷдёӘз¬ёз®©пјҢз»ҷдәҢеҚҒе№ҙеүҚиҝңе«Ғзҡ„еҘіе„ҝгҖӮвҖқз¬ёз®©йҮҢиәәзқҖдёҖ件жңӘзјқе®Ңзҡ„иҷҺеӨҙйһӢпјҢйһӢйқўз»ЈзқҖеҚҠеҸӘеЁҒйЈҺзҡ„иҷҺеӨҙпјҢй’Ҳи„ҡз»ҶеҜҶе·Ҙж•ҙпјҢйһӢеә•иҝҳзәідәҶдёҖеҚҠзҡ„еҚғеұӮеә•пјҢжЈүзәҝеёҰзқҖж·Ўж·Ўзҡ„зҡӮи§’йҰҷгҖӮ
еј жЎӮе…°иҜҙпјҢдәҢеҚҒе№ҙеүҚпјҢеҘіе„ҝжҷ“зҮ•иҰҒиҝңе«ҒеӨ–ең°пјҢеҘ№иҝһеӨңиө¶еҒҡиҷҺеӨҙйһӢпјҢжғіи®©еҘіе„ҝеёҰзқҖиҮӘе·ұзҡ„жүӢиүәе’ҢзүөжҢӮеҮәе«ҒгҖӮвҖңжҲ‘们зәҰе®ҡпјҢзӯүеҘ№з”ҹдәҶеӯ©еӯҗпјҢжҲ‘е°ұеҺ»её®еҘ№еёҰеЁғпјҢеҶҚз»ҷеӨ–еӯҷзјқдёҖж•ҙеҘ—иҷҺеӨҙйһӢеёҪгҖӮвҖқиҖҒеҰҮдәәзҡ„еЈ°йҹіеёҰзқҖжІҷе“‘пјҢзңјеә•жіӣзқҖж№ҝж„ҸпјҢвҖңеҸҜдёҙеҮәеҸ‘еүҚпјҢжҲ‘们еӣ дёәеҪ©зӨјзҡ„дәӢеҗөдәҶжһ¶пјҢжҲ‘иөҢж°”жІЎжҠҠиҷҺеӨҙйһӢз»ҷеҘ№пјҢд№ҹжІЎеҺ»йҖҒе«ҒгҖӮеҗҺжқҘеҘ№жқҘдҝЎжҲ‘д№ҹжІЎеӣһпјҢжёҗжёҗе°ұж–ӯдәҶиҒ”зі»гҖӮвҖқ
иҝҷдәӣе№ҙпјҢеҘ№дёҖзӣҙжҠҠй’Ҳзәҝз¬ёз®©ж”ҫеңЁеәҠеӨҙпјҢиҷҺеӨҙйһӢзјқдәҶжӢҶгҖҒжӢҶдәҶзјқпјҢжҖ»жғізқҖзӯүеҘіе„ҝеӣһжқҘиғҪдәІжүӢиЎҘдёҠгҖӮеҺ»е№ҙд»ҺиҝңжҲҝдәІжҲҡеҸЈдёӯеҫ—зҹҘпјҢеҘіе„ҝж—©е·Із”ҹдәҶеӨ–еӯҷпјҢеҰӮд»ҠеӨ–еӯҷйғҪиҰҒдёҠеӨ§еӯҰдәҶпјҢеҸӘжҳҜеҝғйҮҢиҝҳжғҰи®°зқҖеҪ“е№ҙжІЎжӢҝеҲ°зҡ„иҷҺеӨҙйһӢгҖӮвҖңжҲ‘жғіи®©еҘ№зҹҘйҒ“пјҢеҪ“е№ҙжҳҜеҰҲеӨӘеӣәжү§пјҢдёҚиҜҘеӣ дёәиҝҷзӮ№дәӢиҖҪиҜҜдәҶжҜҚеҘіжғ…еҲҶгҖӮвҖқеј жЎӮе…°д»ҺеҸЈиўӢйҮҢжҺҸеҮәдёҖдёӘеёғеҢ…пјҢйҮҢйқўжҳҜеҘ№иҝҷдәӣе№ҙзјқзҡ„е°ҸиўңеӯҗгҖҒе°ҸиӮҡе…ңпјҢвҖңиҝҷдёӘз¬ёз®©пјҢи—ҸзқҖжҲ‘еҜ№еҘ№жңҖж·ұзҡ„зүөжҢӮпјҢд№ҹи—ҸзқҖиҝҹжқҘдәҢеҚҒе№ҙзҡ„йҒ“жӯүгҖӮвҖқ
жһ—еӨҸйҖ’дёҠйқӣи“қиүІдҝЎзәёпјҢеј жЎӮе…°жҸҗ笔еҶҷдёӢпјҡвҖңжҷ“зҮ•пјҢжҲ‘зҡ„д№–еҘіе„ҝпјҢдәҢеҚҒе№ҙдәҶпјҢеҰҲдёҖзӣҙжӢҝзқҖиҝҷдёӘй’Ҳзәҝз¬ёз®©жғҰи®°зқҖдҪ гҖӮеҪ“е№ҙзҡ„дәӢжҳҜеҰҲдёҚеҜ№пјҢдёҚиҜҘи·ҹдҪ иөҢж°”пјҢи®©дҪ еӯӨйӣ¶йӣ¶иҝңе«ҒгҖӮиҝҷиҷҺеӨҙйһӢжҲ‘дёҖзӣҙжІЎзјқе®ҢпјҢзӯүзқҖз»ҷдҪ иЎҘпјҢд№ҹзӯүзқҖз»ҷеӨ–еӯҷзјқж–°зҡ„гҖӮж„ҝдҪ иғҪеҺҹи°…еҰҲпјҢиӢҘдҪ ж„ҝж„ҸпјҢеҰҲжғіиҝҮеҺ»зңӢзңӢдҪ пјҢзңӢзңӢеӨ–еӯҷпјҢжҠҠжІЎзјқе®Ңзҡ„зүөжҢӮйғҪиЎҘдёҠгҖӮвҖқ
еҘ№е°Ҷж—§й’Ҳзәҝз¬ёз®©гҖҒжңӘзјқе®Ңзҡ„иҷҺеӨҙйһӢгҖҒеёғеҢ…е’ҢдёҖеј иҮӘе·ұзҡ„иҝ‘з…§дёҖиө·жҠҳжҲҗеёғеё•зҡ„еҪўзҠ¶пјҢж”ҫиҝӣдёҖдёӘеҲ»зқҖзј жһқиҺІеӣҫжЎҲзҡ„зҺ»з’ғзҪҗгҖӮзҪҗйҮҢзј“зј“еҚҮиө·зұій»„иүІзҡ„йӣҫж°”пјҢйӣҫж°”дёӯпјҢвҖңеёғеё•вҖқд»ҝдҪӣиҪ»иҪ»еұ•ејҖпјҢжЈүзәҝдёҺй’Ҳи„ҡеңЁйӣҫдёӯжөҒиҪ¬пјҢдёҺзәўз»ізҪҗдёӯеҗ„иүІйӣҫж°”зӣёиһҚпјҢи—Өи”“дёҠзҡ„иҠұжңөи·ҹзқҖиҪ»иҪ»йў”йҰ–гҖӮеј жЎӮе…°зңӢзқҖйӣҫж°”пјҢжіЈдёҚжҲҗеЈ°пјҡвҖңиҝҷйӣҫж°”пјҢеғҸжһҒдәҶеҪ“е№ҙз»ҷдҪ зјқиЎЈжңҚж—¶зҡ„зҒҜе…үпјҢеҘіе„ҝдёҖе®ҡиғҪж„ҹеҸ—еҲ°жҲ‘зҡ„еҝғж„ҸгҖӮвҖқ
еј жЎӮе…°иө°еҗҺпјҢзәўз»ізҪҗзҡ„и—Өи”“иҪ»иҪ»иҲ’еұ•пјҢзұій»„иүІзҡ„йӣҫж°”дёҺд№ӢеүҚзҡ„жҡ–жЈ•иүІгҖҒжҹ”зҙ«иүІзӯүйӣҫж°”зӣёиһҚпјҢи—Өи”“дёҠејҖеҮәдёҖжңөзұій»„иүІзҡ„е°ҸиҠұпјҢж—Ғиҫ№йЈҳеҮәдёҖеј зәёжқЎпјҢжҳҜиҖҒдәәе’ҢйҳҝжЈ еҘіеЈ«зҡ„еӯ—иҝ№пјҡвҖңжңӘзјқе®Ңзҡ„зүөжҢӮпјҢдјҡеңЁж—¶е…үйҮҢз»Үе°ұдәІжғ…пјӣиҝҹжқҘзҡ„йҒ“жӯүпјҢзңҹеҝғиҮӘдјҡиһҚеҢ–йҡ”йҳӮгҖӮвҖқ
еҮ ж—ҘеҗҺпјҢдёҖдҪҚз©ҝзұіиүІйЈҺиЎЈзҡ„дёӯе№ҙеҘідәәиө°иҝӣйӮ®еұҖпјҢжүӢйҮҢжҚ§зқҖдёҖдёӘеҗҢж ·иҖҒж—§зҡ„еёғеҢ…гҖӮвҖңжҲ‘еҸ«жқҺжҷ“зҮ•пјҢвҖқеҘідәәзҡ„зңүзңјй—ҙдёҺеј жЎӮе…°жңүеҮ еҲҶзӣёдјјпјҢзңји§’иҝҳеёҰзқҖжіӘз—•пјҢвҖңжҲ‘зңӢеҲ°дәҶеҰҲеҜ„жқҘзҡ„й’Ҳзәҝз¬ёз®©е’ҢдҝЎпјҢзү№ж„Ҹиө¶иҝҮжқҘеҜ„еӣһдҝЎгҖӮвҖқжҷ“зҮ•иҜҙпјҢеҪ“е№ҙиҝңе«ҒеҗҺеҘ№д№ҹдёҖзӣҙжғҰи®°зқҖжҜҚдәІпјҢжҜҸж¬ЎзңӢеҲ°еҲ«дәәз©ҝиҷҺеӨҙйһӢпјҢе°ұжғіиө·жҜҚдәІжІЎзјқе®Ңзҡ„йӮЈдёҖеҸҢгҖӮвҖңжҲ‘д»ҺжІЎжҖӘиҝҮеҰҲпјҢеҸӘжҳҜжӢүдёҚдёӢи„ёдё»еҠЁиҒ”зі»гҖӮвҖқеҘ№жү“ејҖеёғеҢ…пјҢйҮҢйқўжҳҜдёҖ件еҘ№з»ҷжҜҚдәІз»Үзҡ„жҜӣиЎЈпјҢвҖңжғіе‘ҠиҜүеҰҲпјҢжҲ‘дёҖзӣҙзӣјзқҖеҘ№жқҘпјҢзӣјзқҖжҲ‘们жҜҚеҘіиғҪе’Ңи§ЈпјҢжҠҠиҝҷдәӣе№ҙзҡ„з©әзҷҪйғҪиЎҘдёҠгҖӮвҖқ
жһ—еӨҸеё®жҷ“зҮ•жҠҠеӣһдҝЎгҖҒжҜӣиЎЈдёҖиө·жҠҳжҲҗеҝғеҪўзҡ„еҪўзҠ¶пјҢж”ҫиҝӣзұій»„иүІйӣҫж°”зҡ„зҺ»з’ғзҪҗгҖӮйӣҫж°”зҝ»ж¶Ңй—ҙпјҢвҖңеҝғеҪўвҖқдёҺвҖңеёғеё•вҖқеңЁйӣҫдёӯзӣёйҒҮпјҢиҷҺеӨҙйһӢдёҺжҜӣиЎЈйҒҘзӣёе‘јеә”пјҢд»ҝдҪӣйҮҚзҺ°дәҶеҪ“е№ҙжҜҚеҘідҝ©зҒҜдёӢзјқиЎҘзҡ„жё©йҰЁеңәжҷҜгҖӮжҷ“зҮ•зңӢзқҖйӣҫж°”пјҢиҪ»еЈ°иҜҙпјҡвҖңеҰҲпјҢжҲ‘еҺҹи°…дҪ дәҶпјҢжҲ‘еҘҪжғідҪ гҖӮвҖқ
еӮҚжҷҡж—¶еҲҶпјҢеӨ•йҳідёәе°Ҹйҷўй•ҖдёҠдёҖеұӮжҡ–е…үпјҢеј жЎӮе…°еҸ‘жқҘдёҖеј з…§зүҮпјҢз…§зүҮдёҠжҳҜеҘ№е’Ңжҷ“зҮ•гҖҒеӨ–еӯҷеңЁе°Ҹйҷўзҡ„еҗҲеҪұпјҢдёүдәәеӣҙзқҖй’Ҳзәҝз¬ёз®©пјҢжҷ“зҮ•жӯЈеңЁз»ҷжҜҚдәІиҜ•з©ҝж–°з»Үзҡ„жҜӣиЎЈпјҢиҷҺеӨҙйһӢж”ҫеңЁдёҖж—ҒпјҢ笑容温жҡ–иҖҢйҮҠ然гҖӮжһ—еӨҸжҠҠз…§зүҮж”ҫиҝӣзҺ»з’ғзҪҗпјҢйӣҫж°”е°Ҷз…§зүҮеҢ…иЈ№пјҢдёҺзұій»„иүІзҡ„йӣҫиһҚдёәдёҖдҪ“гҖӮ
жһ—еӨҸжӢҝиө·жҜӣ笔пјҢеңЁдҝЎзәёдёҠеҶҷдёӢпјҡвҖңи“қйӣҫйӮ®еұҖзҡ„еҲқз§ӢйҮҢпјҢж—§й’Ҳзәҝз¬ёз®©и—ҸзқҖжңӘзјқе®Ңзҡ„зүөжҢӮдёҺ愧з–ҡпјҢжҜӣ衣延з»ӯзқҖжҜҚеҘій—ҙзҡ„жҖқеҝөдёҺе’Ңи§ЈпјҢжҜҸдёҖд»Ҫйҡ”йҳӮйғҪеңЁж—¶е…үйҮҢиў«дәІжғ…иһҚеҢ–пјҢжҜҸдёҖж¬ЎйҮҚйҖўйғҪжүҝиҪҪзқҖеІҒжңҲзҡ„жё©жҹ”гҖӮеҺҹжқҘпјҢжҜҚеҘіжғ…д»ҺдёҚдјҡиў«дәүеҗөйҳ»йҡ”пјҢзүөжҢӮд»ҺдёҚдјҡиў«ж—¶е…үеҶІж·ЎпјҢеҸӘиҰҒеҝғжҖҖйҒ“жӯүдёҺжҖқеҝөпјҢз»ҲиғҪи·Ёи¶Ҡеұұжө·пјҢи®©жңӘзјқе®Ңзҡ„зҲұпјҢеңЁеІҒжңҲйҮҢиҝҺжқҘжңҖжҡ–зҡ„еңҶж»ЎгҖӮвҖқ
й—ЁеҸЈзҡ„й“ңй“ғеҶҚж¬Ўе“Қиө·пјҢеҸҲжңүдәәеёҰзқҖи—ҸзқҖдәІжғ…зҡ„ж—§зү©иө°жқҘгҖӮжһ—еӨҸ笑зқҖиө·иә«пјҢйҖ’дёҠйқӣи“қиүІзҡ„дҝЎзәёгҖӮеҘ№зҹҘйҒ“пјҢиҝҷдәӣи—ҸеңЁйӣҫйҮҢзҡ„жҜҚеҘіжғ…дёҺзүөжҢӮеҝғпјҢдјҡеғҸеҲқз§Ӣзҡ„жҡ–йҳідёҖж ·пјҢеңЁж—¶е…үйҮҢжөҒж·ҢпјҢж°ёиҝңжё©жҡ–иҖҢз»өй•ҝ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ө¶е°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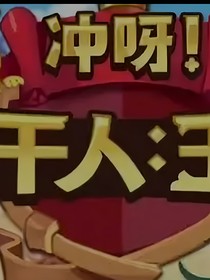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йҘје№ІдәӢи®°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еңЁејӮз•Ңзә№д№қйҫҷжӢүжЈә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Ҫ’е°ҳеҲӣдё–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家з”өи§ҶжңәиғҪз©ҝи¶ҠдёҮз•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