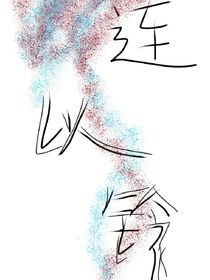第十六章
柳寻鸢没作声,低头念咒,下一瞬指尖炸开一团碧火。他拿食指沾了一点火,摁到倚影卫左眼皮上,说:“再看看。”
很快,倚影卫就变了脸色。
片刻之后,倚影卫用力揉了揉眼睛,指着冲宵塔道:“那些都是妖怪?”
“不止,还有山精魍魉死灵魁魈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乔阿普撇撇嘴,“阴傀石大概把附近所有的怪东西都引过来了。这石头发散出的气息,对人类与普通鸟兽而言是无味的毒气,但对那些低级别的妖物精怪却是莫大的吸引,好比饥饿的人闻到肉香,然后拼命要找到这块肉吞下去。害的人命越多,阴傀石就会越香。”
他的视线落回地面上,一座四五米高的四方围墙将冲霄塔圈住,墙上没有多余的装饰,只整整齐齐地刻着各种经文,一扇黑漆大门就开在正对面的墙上,并未上锁。
他朝大门走去,心想这回怕是要亏本。孰湖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妖怪,拿来做药也顶多起个强身健体的效用,可要治它弟弟,却不知要费多少心思多少药,光是料理塔外那一堆家伙就够她头痛了,而且还不知道身上带的药够不够。若不能一举驱散这些家伙,必遭反扑,那就更麻烦了。活捉降伏费时费力,大开杀戒它们又罪不至死,不过是来闻闻味道过过瘾罢了。
思索间,已然走到门前,实在不行的话,也只能靠自己杀出一条路来,也不知塔顶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唉,都怪那个混蛋,要不是他教唆孰湖烧那么多纸,他根本就不会卷到这件破事里来!
越想越生气,正伸手推门,门却自己开了。
有些人,确实要用艳若桃李来形容的。
开门的女子,比自己矮半个头,二十出头的年纪,楚腰纤细,柳眉杏眼,眸如星河,即便不笑,嫣红的嘴唇也微微上翘,自然地保持着迷人的弧度。当一个人的脸孔足够美貌时,穿什么衣裳梳什么发式都是合宜的,哪怕一件毫无装饰甚至不分性别的窄袖黑衫,以及用一条细细的红缎带简单束在身后的长发。
一旁的乔阿普愣了愣,旋即笑道:“我还以为照应这座塔的不是和尚就是尼姑呢。”
女子打量她一番,也笑:“小丫头,游塔的话,天明之后再来吧。”说罢,她微微一歪脑袋,看着乔阿普身后的倚影卫,冲他俏皮地眨眨眼,“那位可是倚影卫?这可奇了,您也跟着瞎跑?”
认识的?!
柳寻鸢和乔阿普站在他们中间,虽不知女子的身份来历,但从倚影卫骤然微妙的神情看来,应该不是个好打理的主儿。
倚影卫上前,朝她笑盈盈地一拱手:“真是好些时候不见了!”又看看她身后的大门,笑,“就是不知今晚该尊称你铃星大人,还是邱姑娘呢?”
“公务在身。”她拱手还礼,又做了个请的姿势,“请回吧,过几日再带友人来登塔赏景。”
“那今天就只能喊你铃星大人了。”倚影卫笑笑,指了指冲宵塔,小声道,“怎么,今天的公务是捉妖怪?”
女子微笑道:“倚影卫,请回。”
“我若非要现在去登塔赏夜景呢?”乔阿普把倚影卫挤到一边,笑眯眯地打量女子,“这位姐姐还是行个方便吧。这大半夜的,你一个女儿家独自在此守着一堆妖怪,我们瞧见也很担心呢。”
女子只将脸转向倚影卫,问:“你的朋友?”
“……算是吧。”
女子的视线落在孰湖身上,神色顿时冷峻起来:“你这小妖怪竟然还敢出现?!念你体弱无用,不屑取你性命,放你一马,你倒不知死活了?”
孰湖吓得“刷”一下躲到柳寻鸢身后。
“不过,中我一箭还能生龙活虎的妖怪不多。”女子看向倚影卫,“坠府几时也开始替这些龌龊的妖物解是非了?”
“暗箭伤妖不是更龌龊?”乔阿普冲她吐舌头(什么毛病),“姐姐,不如你就当没看见我?我进去一会儿就出来,你跟我家影卫在外头聊天叙旧不比你对着一堆妖怪更好?”
女子只笑不语,微一侧身,似是给她让了路。
“谢了。”乔阿普立刻往大门而去。
身后的女子,慢条斯理地拿起挂在腰间的一个秀气精致的酒囊,拔起塞子,往手里倒出几滴,也不知是水还是酒,散发出甜甜的气味。但见她微一握拳,再打开时,掌中已不见水滴,只得三枚亮闪闪的短箭。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短箭齐出,每一支都对准乔阿普的要害之处。
“小心!”离乔阿普最近的倚影卫冲上去一把推开她。
几乎同时,只听得“咔咔”几声,三支短箭凌空碎裂,落地化水。
击碎它们的,是一块石子与几片树叶。
众人回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坠翎,拍掉落在肩膀上的一片树叶,走上前对倚影卫道:“不错啊,宝刀不老,石子儿一点偏差都没有。”
“少爷?!”倚影卫诧异道,“你怎么来了?”
“睡不着,出来走走。”坠翎径直走到那女子面前。
一见来者是坠翎,女子顿时变了脸色,说不出是怎样的情绪,欢喜与期待,敬畏与仰慕都一股脑儿地涌出来,混乱地纠缠在一起。
她居然要下跪,却在膝盖触地前被坠翎拉住。
“我已离任多时,你无需如此。”坠翎说话时,并不怎么看她,只望着冲宵塔道,“这塔里有我们坠府要解决的是非,就当给我一分面子,放他们进去吧。”
女子望着他的侧脸,为难道:“上头下了命令,三天后于冲宵塔行除祟之阵,如今塔中已布下迷阵符,妖物可入不可出。我奉命驻守于此,任何闲杂人等绝不可入内。”
坠翎冷冷道:“为何还要等三日才行除祟之阵?”
“上面的意思是,既有妖物被吸引而来,索性多等几日,除掉一只不如除掉一群,少一只妖物,京城便多一分安宁。”女子回答。
“你们拿冲宵塔做饵杀妖?”乔阿普听得清清楚楚,指着冲宵塔道,“既然这么大本事,那你们早知这些天京城里枉死的人是怎么来的了?有那工夫算计妖怪,都不肯出手阻止塔顶的玩意儿继续扩散害人,反利用它继续吸引更多妖怪?”
“少一只妖,不知能救多少性命。长远来看,我们的决定没有错。”女子不为所动,“必要的牺牲也是没有法子的。”
孰湖跑到柳寻鸢脚下,着急道:“不能进了么?”
坠翎目不斜视地对柳寻鸢说:“带它进去。我在这里,你们大可来去自如。”
而此时的柳寻鸢,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女子刚才那句“妖物可入不可出”上。他倒是没问题,可是乔阿普……
明明说了不关自己的事,明明一副爱理不理的死样子,为何偏对这只妖怪网开一面……柳寻鸢看了坠翎一眼,虽有满腹疑问,但也顾不得追问,立刻带着孰湖进了大门。身后,乔阿普跟花虎也急匆匆地跟了进去。
“你要是有什么不适,一定要告诉我,听见没有?”他对乔阿普小声说。
“站住!”女子想阻止,却被倚影卫断了去路,她笑嘻嘻道:“铃星大人,别管他们,好久不见了,你就没什么知心话想跟我家少爷说说?”
“你!”她攥起了拳头,却又深知若被这个家伙拦住的话,几乎没有脱身的机会。
寒风扫过,残叶飞舞,坠翎看着她的脸,叹息:“甜如蜜糖,毒如砒霜……你以糖水铸箭的本事依然独一无二。都不需要靠近,便知守在这里的是你。”
“这算夸奖,还是指责呢。”她笑笑,举起酒囊,喝了两口,“我用十种花瓣调制的,有润肺清火之效。要尝尝么?”
“我素来不喜甜食。”坠翎的拒绝永远不会婉转。
她遗憾地耸耸肩,又喝了两口,满足地咂咂嘴。
“好喝么?”他问。
“好喝呀!”她十分真诚地表示。
“一边说好喝,一边拿它杀人。”他嘴角微扬。
“咱们的规矩,大人你……不是,少爷你该知道的。”她无奈道,“凡阻碍我司公务者,可先斩后奏。”
他摇摇头,冷笑:“狴犴司的作风,果真没有半分改变。”
……
不知为何,乔阿普没什么事,柳寻鸢倒是很难受。
他忍着头晕,捏着自己差不多空了一半的布囊。
自己算算吧,百丈高的塔啊,都爬满了妖物,得用去多少药才能在短时间内让它们失去知觉,一个接一个地落在地上。
现在,从塔顶看下去又是另一种“壮观”了,塔下堆起了小山般高的妖魅精怪,个个都以奇葩的姿势晕了过去。兔精的脚蹬在狐妖的脸上,恶心巴拉的蜈蚣精被一团更恶心的鼻涕似的精怪抱在怀里,几只鸟妖横七竖八地瘫在猫妖的身上,一会儿醒过来后希望它们来得及从猫嘴下逃生吧……
塔顶确实有一座价值不菲的金佛,整个空间里只有它最淡定,面露慈悲地注视着眼前这群不淡定的家伙。
孰湖兄弟终于在分离三天之后重聚了,可惜当弟弟的没有哥哥运气好,身上的箭伤都集中在心口的要害处,全靠它平日里身体强壮,再加上有阴傀石在身,才勉强留住了性命。
几人站在这个体型比它哥哥大出太多的家伙身旁,视线凝聚在它背上那块已经凹陷到皮肉里的,只有鸡蛋大小的黑石头。
此刻它已经不太能动弹了,出的气比进的气多。
那女子说什么已经埋下了迷阵符,虽不知这些家伙口里的符是什么材质有什么玄机,但冲宵塔上确实附着了一股类似结界的力量,就算这些妖物们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阴傀石的味道对它们而言只是毒饵,它们也无法离开冲宵塔。
如果这个家伙没有受重伤,以它的能力,这里应该是困不住它的。
这样岂不更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决一切,只要一颗药丸就能立刻终止这只孰湖的生命,然后让它那个没用的哥哥驮着阴傀石一去不回。
本来也应该是这样的。
“你不但身子没用,脑子还傻。”它缓缓开口,讥讽红着眼睛站在它身边的哥哥,“既不能打又不能杀,回来干吗?站在一旁给我鼓掌加油?”
孰湖垂着头,理亏似的不敢看自己的弟弟:“我……我带人来救你!”
它皱眉:“不用谁救我。这结界困不住我,我只需要再休息几天。”
“休息?”柳寻鸢咬牙笑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你伤成这样,你以为你还有机会休息?他们已经在计划三天后对冲霄塔来一次彻底的‘清理’了,届时,你和被你吸引来的精怪们恐怕连渣都不会剩。打败你的家伙,谁都摸不清深浅,你还是收起你的乐观吧。”
“你以为你是谁,竟来教训我?”它瞟了他一眼。
他蹲下去看着它:“百舸山的。”
闻言,它愣了愣,脱口而出:“你是夜……”
“是呀。”柳寻鸢打断它,指了指孰湖,“你的哥哥找到我,求我治你杀人如麻的病。”
它沉默片刻,呵呵地笑出来:“你也觉得我这个哥哥很蠢吧,它只知你医术精湛,却不知你杀的大概比你救的还多吧?”
“不不不,它什么都知道。”他认真道,“它知道要治你的病,就得要你的命。”
它微微一怔。
“我答应了。”他凑到它面前,伸手拍了拍它的脑袋。
“对不起……对不起!”孰湖跪在它面前,“我不想这样,可是只能这样才能不让你变成真正的怪物。”
“你……”乔阿普想劝慰,但实在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从它决定找柳寻鸢求助的那一刻起,就该知道事情只能是这样的结果。怎么劝呢?
“把我这个没用的哥哥带走吧。”它忽然对他道,“我只想跟你谈谈。”
“可以。”柳寻鸢回头,对乔阿普道:“你带这家伙去楼下等等。”
“我留下行不行?”孰湖突然哭喊出来,“这一走,我再也见不到它了呀!”
而它不为所动,甚至都不看自己的哥哥一眼,干脆闭上了眼睛。
柳寻鸢跟乔阿普使了个眼色,乔阿普点点头,直接把孰湖夹在胳肢窝下,也不管它怎么踢打哭喊,径直下楼去了。
四周终于安静下来,偶尔听到它沉重的呼吸声。
“我活了五百年,载过上千万斤的重量。”它慢慢道,“一条人命的重量,抵得过十个活人。被我从空中扔下来的,有四十二人,死在阴傀石上的,到今天有二十人。”
“嗯。一共六十二人,我记下了。”他点点头,神色没有半分波动。
“赤鳞踏火,人不可近。”它看向他,“关于你的传闻,是这么说的吧?”
他笑笑不说话。
“为何还不现火?”它的目光移到他的手上。
“很少遇到你这么急着找死的妖怪,胆子挺大嘛。听你哥哥说,你自小就比它厉害,什么都不怕。”
“怕打雷。”它诚实道,“可能那家伙自己都忘记了,我们幼时,崦嵫山一到夏季就雷雨不断。每到雷声轰鸣时,那家伙就在我身边给我哼歌。很难听。但我听着听着就能睡着。”
柳寻鸢暗暗握紧拳头,指甲嵌进掌心,留下几个血印。
“大人,”它看着他的眼睛,“你也觉得我做这一切,只是为了让我自己拥有足够保护我哥哥的能力?”
“……你不仅仅是害怕打雷吧?”
它呵呵笑了两声,道:“我很怕死在它后头。”
沉默持续了很久。
“你既是百舸山的人,自然明白妖物之中,我们孰湖是多么平平无奇的一族。没有魅惑天下的美貌,没有呼风唤雨的本事,一生中只懂得在看到走不动的或者受伤的人时,主动将其驮到想去的地方,偶尔能出几个本事大的,把一座山驮到洪水中,不让洪灾继续祸害苍生。说到底,我们只有蛮力,习惯于最简单的生活。”它的语气很平静,“母亲生下我们之后,就会离开崦嵫山,所有的孰湖都要靠自己的力量破壳,长大。我们根本不知父母是谁,在哪里,我们只认识崦嵫山里最老的那只孰湖,它教给我们各种规矩,最要紧的一条永远是要我们注意那块石碑,告诉我们每五百年,孰湖一族就会有一次‘清理’,最弱的那一个就要交出性命,因为孰湖是以力量为荣的妖怪,不能承载重量的孰湖,不配活着。”它叹了口气,“所以我的恐惧在很早很早前就开始了,因为我知道哥哥逃不过五百年。虽然它已经很努力,可是那些灵魂,根本不够。”
他笑笑:“你害怕它死在你前头的话,打雷时没人给你唱歌了?”
“我已经不怕打雷了。”它稍微转过头去,望着外头漆黑的夜空,“我们天生不能被人类以及别的妖怪们看见,除了受伤,或者临死前的一刻。”它顿了顿,又道,“孰湖是独居的妖怪,成年离开崦嵫山后,大家便各奔东西。绝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极致的孤独里度过,若能顺利活过五百年,便能回到崦嵫山与雌孰湖繁衍后代。可那仅仅是繁衍罢了。在人界的时间越久,越能明白为何我们的父母可以毫不犹豫地离开。因为在孰湖的世界里,我们不是孩子,仅仅是一种产物。”它苦笑,“被我们帮助过的人,连应该对谁说谢谢都不知道。即便遇到喜欢的人类或者妖怪,我们也不敢靠近、不敢动心。亲人、朋友、爱人,对我们而言永远只能是一个词语。”
柳寻鸢不再跟它开玩笑,默默地听它说,它应该很久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了。
“孰湖里很少会有我们这样的双胞胎。”夜空里不知道有什么,它看得很认真,甚至露出了笑容,“虽然它个子那么小,力气也小,总被欺负,可我有哥哥啊。那个跟我一起诞生在这个世界,白天一起玩耍,夜里睡在我身边的家伙。”它眼睛有些湿,“他活着,孤独就无法打败我。”它回过头,看着她,“真正虚弱的那个,是我。这些年,并非我在保护着它,而是它在支撑我。我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不过是在自私地维护自己的感受。”
“六十二条人命……”他摇头。
“被我驮到天上摔死的,按人类的标准,都算不得好人。”它缓缓道,“我不是为自己辩解,我只是不明白,孰湖从一出生就要努力地活着,就算没有干坏事,也会因为不够优秀而被清理掉。可这些人既不努力也不善良,要么挥霍时光,混吃等死,要么凭着阴谋诡计达到目的,甚至还有牺牲他人成就自己还觉得理所当然的,即便如此,他们却没有五百年一次的评判,可以轻而易举地活下去。”
“人类世界也是有你们那块‘石碑’的,每个人做了什么、做得好不好对不对,都记在上头,也不用五百年那么久,有时候五年甚至五个月五天,就会得到评判的结果。”他很少有这么正经的语气,“人类通常管这个评判的过程,叫因果。”他顿了顿,叹气,“对你也是有效的。”
“我知道自己早晚都有这结果,只是没想到是在这冲宵塔上,也没想到最后送我的人是你。”它笑笑,忽然深深地吸气,随后张开嘴,一粒拇指头大小的圆珠自它口中滚落出来,散着莹润的红光。
吐出这珠子之后,它本来就不好的脸色更难看了。
“我若是死了,内丹也就跟着没了。”它吃力地说,“不如这会儿吐出来,你替我交给它。吞了这个,它也许会长点力气。”
他皱眉:“失了内丹,你形神俱灭。有内丹在身,即便死去,起码精魄不散,也许还能有再入轮回的可能。你确定要这样?”他看了看地上的珠子,“你现在吞回去还来得及。”
“就这样吧。”它无力地趴下来,面白如纸,闭上眼睛,“对我这种妖怪的下场,你应拍手叫好才是。”
“是的,我并不同情你。”他不客气道,“但你并不让我感到恶心。只是觉得你不比你口中说的没用的哥哥聪明多少,确实是如假包换的亲兄弟。”
它费力地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