Á¨¨ÂÖ≠Á´Ý
……天空褪去了夜晚的忧郁沉闷,朝霞飘飘,又开始了光彩照人的新的一天……
……他瘫在岸上,眼里没了光……
啪嚓!
‰∏ĉ∏™Áì∑Á¢óÊéâÂú®Âú∞‰∏äË£ÇÊàêÂáÝÁì£Ôºå‰ªñÁåõÂú∞‰ªéÂàöÂàö‰∏ÄÁû¨Èó¥ÁöÑÂπªËßâÈáåÊÉäÈÜí„ÄÇ
一睁眼,眼前依然一片混沌,适应了好久才看清东西。估计是雄黄的劲儿还没过,他只觉浑身疼得钻心。
眉心那道蛇印,烫得惊人。
‚Äî‚ÄîÁé∞Âú®ÁöѱÄÈù¢Â∞±ÊòØÔºå§ßÂçä§ú‰∏çÁù°ËßâÂéªÂé®ÊàøÊ∫úËææÔºåÁªìÊûúÂ∏Ö‰∏çËøá‰∏âÁßíÂèëÁé∞Ëá™Â∑±ÊóÝÊ≥ïÂõûÂçßÂƧԺå‰∏ÄÂá∫Èó®Â∞±Èù¢‰∏¥ÁùÄÊôïÂÄíÁöÑÈ£éÈô©„ÄÇ
ÊÉ≥˱°‰∏ĉ∏ãÔºåÊñ∞Êù•ÁöÑÂé®Â≠êÂçä§úÊôïÂú®ÂçßÂƧÂíåÂé®Êàø‰πãÈó¥ÔºåÂ∞ëÁà∑‰ºöÊÄé‰πàÊÉ≥ÔºüÂÝÇÂÝÇÂùÝÂ∫úÁ©∑Âà∞‰∏çÁªôÂé®Â≠êÈ•≠ÂêÉÂغËá¥Âé®Â≠êÈ•øÊôïÔºü
但是他是谁啊,他是柳寻鸢!大丈夫能屈能伸……哪里跌倒哪里睡一觉就好了。
“喂,龙雀,我先睡了,天亮叫我。”
他解开外套披在身上,权当毯子盖在身上,然后真的闭上眼睛。
龙雀在一旁歪着脑袋思考。
哦!茅塞顿开。
此乃阳谋,天亮叫醒他,大家只会认为柳寻鸢乐岗敬业天刚亮就干活,而不会怀疑他是半夜偷吃在厨房过夜的闲杂人等。
妙计。不愧是老妖怪。
‰∫éÊòØÊ∏ÖÊô®Ôºå±ïÂ∏àÂÇÖÂú®Âãâº∫Âñù‰∏ãÈÇ£Á¢óÈ£òÁùÄÂæƶôÁ≥äÂë≥ÁöÑÁ≤•Êó∂ÔºåÂøç‰∏ç‰ΩèÈóƉªñÔºàșljªñÔºâÔºö‚Äú‰ΩÝÂ∞±ÈùûÂæóËá™Â∑±‰∫≤Êâã‰∏ãÂé®ÔºüÊàëÊï¢ÊãÖ‰øùËä±ËôéÂÅöÈ•≠ÈÉΩÊØî‰ΩÝ•ΩÂêÉ„ÄÇ‚Äù
可柳寻鸢隔了老半天才回一句:“下次不做了。”
Ê≠£Â∏∏ÊÉÖÂܵ‰∏ãÔºåËØ¥ËøôËØùÊó∂‰ªñÂ∫îËØ•Áøª‰∏™ÁôΩÁúºÔºå‰∏ÄËÑ∏‚ÄúÊàëÂ∞±ÊòØÂèõÈÄ܉ΩÝËÉΩÊääÊàëÊÄé‰πàÂäû‚ÄùÁöщ∏ç±ë„ÄljΩÜËøôʨ°‰ªñÂÅèÊ≤°ÊúâÔºåËØ≠Ê∞îÁâπÂà´Ê≠£Â∏∏„ÄÇ
这么正常,太不正常了。
总之他说了那句话之后,早餐的气氛突然有了一丝微妙的正经与严肃。虽然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Âè™ÊòØË㶉∫ÜÂùÝÂ∫ú‰∏ä‰∏ãÁöщ∫∫Ôºå‰πü‰∏çÁü•Ëøò˶ÅÂêɧö‰πÖ‰∏çÊò؉∫∫ÂêÉÁöщ∏úË•ø‚Ķ‚ĶÂÄöÂΩ±Âç´‰πüÊòØÔºå§߉∏ç‰∫ÜÂÜçËØ∑‰∏™Âé®Â≠êÂòõÔºåÊääÊü≥ÂتÈ∏¢ÊâîÂéªÊ¥óË°£Êâ´Âú∞§ßÂÆ∂ËÇØÂÆöÂèåÊâã˵ûÊàêÁöܧßʨ¢Âñú„ÄÇ
‰∏çËøáËøôÂáݧ©Â•ΩÂÉèÈÉΩÊ≤°ËßÅÁùÄÂÄöÂΩ±Âç´ÔºåËøûÂêÉÈ•≠ÁöÑÊó∂ÂÄôÈÉΩ‰∏çËßÅ•πÁöÑË∏™ÂΩ±„ÄÇÂÅå§ßÁöÑÂùÝÂ∫úÈáåÔºåË∞ÅÂú®Ë∞ʼn∏çÂú®ÔºåÊĪÊòØÂæóËøá‰∏äÂ•Ω‰∫õÊó∂ÂÄôÊâçËÉΩÂØüËßâÔºåÊØïÁ´üËøôÈáåÂú∞§߉∫∫Â∞ëÔºåÂêå‰∏ıãÊ™ê‰∏ã‰πü‰∏çËßÅÂæó§©Â§©ËÉΩÁ¢∞‰∏ä„ÄljΩèÂú®ËøôÂ∫ßÂÆÖÂ≠êÈáåÁöÑÂÆ∂‰ºô‰ª¨Ôºå§ß§öÊï∞ÈÉΩÊ≤°ÊúâÂ≠òÂú®ÊÑüÔºåÈô§‰∫ÜÈÇ£‰ΩçÂ∞ëÁà∑Ôºå‰∏çÊòæ±±‰∏çÈú≤Ê∞¥ÔºåÊĪÊòØÂàªÊÑèÊî∂ÊïõÔºåÂÆÅÂèØÁã¨Â§Ñ‰∫éÂɪÈùôÂú∞Ëت˵ÑÊ≤ªÈÄöÈâ¥Ôºå‰πüÊáíÂæó‰∏é‰∫∫‰∫§ÈôÖÔºåÂπ≥Êó•Èá剪ñË∑ü‰π¶ËØ¥ËØùÁöÑÊó∂ÂÄôÈÉΩÊØîË∑ü‰∫∫ËØ¥ËØùÁöÑÊó∂ÂÄô§ö„ÄljΩ܉πüÊÄ™‰∫ÜԺ剪ñË∂äÊòØËøúÁ¶ª‰∫∫Áæ§ÔºåË∂äÊÉπ‰∫∫ÁïôÊÑèÔºåÂèçÊ≠£Êü≥ÂتÈ∏¢ÈùûÂ∏∏ÁïôÊÑè‚Ķ‚ĶË∞ʼnºöÂøΩËß܉∏ĉ∏™‰ø°ÊÅØÁ¥ÝÂæàÈöæÈóªË∑üËá™Â∑±Ê≠£Â•ΩÁõ∏ÂÖãÁöÑÈõá‰∏ªÂë¢ÔºåÊëäÊâã„ÄÇ
镜头:我转!
“客官,到啦。”撑船的艄公抹了抹额头上的汗。
ÊúõÁùÄÁúºÂâçÁöÑʵÅÊ∞¥‰∏éËøú±±ÂèëÊÑ£ÁöÑÂÄöÂΩ±Âç´ÔºåÂú®Â∞èËàπÈùÝÂ≤∏Êó∂ÁöÑÈ¢ÝÁ∞∏ÈáåÂõûËøáÁ•ûÊù•„ÄÇ
“多谢船家。”她付了钱,向对方拱手相谢后,方才拎上包袱下了船。
ÊĪÊúâÂçÅÊù•Âπ¥‰∫ÜÂêßÔºåËøûÊ∞¥‰π°ËøòÊòØËÄÅÊÝ∑Â≠êÔºå‰∏ÄÂà∞ÁßãÊó•Ôºåʺ´Â±±ÈÅçÈáéÈÉΩÊòØÊ°ÇËä±È¶ôÊ∞îÔºåËøûÊ≤≥Ê∞¥ÈÉΩË¢´ÊüìÂá∫‰∫ÜÁîúÂë≥‰ººÁöÑÔºåÁ∫µÁÑ∂Â∑≤ÊòØÊ∑±ÁßãÔºåÈÇ£‰∫õ±û‰∫éÈùí±±ÁßÄÊ∞¥ÁöÑÂë≥ÈÅìËøòÊòØÊÇÝÊÇÝÁÑ∂ÁÑ∂Âú∞È£òÊï£ÁùÄ„ÄÇ
ÂÄöÂΩ±Âç´Ê∑±Ê∑±Âê∏‰∫ÜÂè£Ê∞îÔºåË∏è‰∏äÈÇ£Êù°Ëµ∞ËøáÊóÝÊï∞ʨ°ÁöÑÁü≥ÊùøË∑ØÔºåÂæÄÈÇ£ÁâáÈöêÂú®Â±±‰π°Ê∑±Â§ÑÁöÑÂÆÖÂ≠ê˵∞Â骄ÄÇ
ÊåéÂú®ËÇ©‰∏äÁöÑÂåÖË¢±Ê≤âÁî∏Áî∏ÁöÑÔºåÈá姥ˣÖÂæóÊúħöÁöÑÔºåÊòØÁî®ÂêÑÁßçÊûúÂ≠êÂà∂ÊàêÁöÑËúúÈ•Ø„ÄÇ•πÊù•Êó∂ÔºåÂú®‰∫¨ÂüéÈáåÊúÄÂá∫ÂêçÁöÑÈ£üÈì∫Èáå‰π∞‰∫Ü•Ω§öÂåÖÔºåÁîüÊÄï˶ÅÈÄÅÁöщ∫∫‰∏ç§üÂêÉÔºåÂøÉÂøÉÂøµÂøµË¶ÅÊääÈì∫Â≠êÈáåÊúÄ•ΩÂêÉÁöÑËúúÈ•ØÈÉΩ‰π∞‰∏ãÊù•‰ººÁöÑ„ÄÇËÄÅÊùøÊó©Â∑≤ÁÜüÊÇâ•π‰∫ÜÔºåÂõ݉∏∫Ëøô‰∫õÂπ¥Êù•ÔºåÂÄöÂΩ±Âç´ÊØèÂπ¥ÈÉΩÂú®Â∑Ɖ∏ç§öÁöÑÊó∂ÂÄôÂéªÂ∫óÈáåÔºåÂêéÊù•Áü•ÈÅì•πÊòØÂùÝÂ∫úÁöÑÂΩ±Âç´‰πãÂêéÔºåËÄÅÊùøÊõæË°®Á§∫Âè؉ª•Áõ¥Êé•ÈÄÅ˥߉∏äÈó®Ôºå‰∏çÂä≥ÂÄöÂΩ±Âç´‰∫≤Ëá™Êù•‰∏ÄË∂üÔºå‰ΩÜ•π©âÊãí‰∫ÜËÄÅÊùøÁöÑ•ΩÊÑèÔºåËØ¥ËøòÊòØËá™Â∑±‰∫≤Ëá™Êù•ÊåëÈÄâÊØîËæÉÂ•Ω„ÄÇÊØè‰∏Äʨ°Â•πÈÉΩÊåëÂæóÁâπÂà´ËƧÁúüÔºå‰∏ç§üÁîúÁöÑÔºåÊûúËÇâ‰∏ç§üÈ•±Êª°ÁöÑÔºåÈÉΩ‰∏ç˶ńÄÇËÄÅÊùøÊÑüÂèπ‰∏çÁü•ÊòØË∞ÅËøô‰πà•ΩÂè£Á¶èÔºåËÉΩËÆ©ÂÄöÂΩ±Âç´Â¶ÇÊ≠§Ë¥πÂøÉÔºåÊØèʨ°Â•πÈÉΩÂè™ÊòØÁ¨ëÁ¨ëÔºåËØ¥‰∏ĉ∏™ËÄÅÊúãÂèãÁà±ÂêÉËúúÈ•Ø„ÄÇ
ËôΩÁÑ∂ÂæÄËøôÊù°Áü≥ÊùøË∑؉∏äÊù•Âõû‰∫ܧöÂπ¥Ôºå‰ΩÜÊØèʨ°Ë∏è‰∏äÂéªÔºåÂøɧ¥‰æùÁÑ∂‰ºöÂÉèÊòØÁ¨¨‰∏Äʨ°ÂéªËßÅÂ֨©ÜÁöÑÂ∞è™≥¶áÔºåÂèàÊàñÊòØÂú®Â§ñÊãºÊêèÊï∞Â𥉪çÊóßÂ≠ëÁÑ∂‰∏ÄË∫´ÁöÑÊ∏∏Â≠êÔºåÂÖç‰∏ç‰∫ÜÁîüÂá∫‰∏ĉ∏ù•ΩÁ¨ëÂèàÊÄÖÁÑ∂ÁöÑÂ∞èÁ¥ßº݄ÄÇ
ÂèØ•πÊòØÂùÝÂ∫úÊúÄÊúâÁî®ÁöÑÂΩ±Âç´ÂïäÔºå‰∏çÊòØÊâ≠ÊçèÁöÑÂ∞è™≥¶áÔºåÊõ¥‰∏çÊò؉∏ĉ∫ãÊóÝÊàêÁöÑʵ™Ëç°Ê∏∏Â≠êÔºå‰ΩÜËøôÁßçÁ¥ßºÝÔºåÊØè‰∏ÄÂπ¥Ëµ∞‰∏äËøôÊù°Áü≥ÊùøË∑ØÊó∂ÔºåÈÉΩÊóÝÊ≥ïÈÅøÂÖçÂú∞Ê∂åÂá∫Êù•„ÄÇ
ËøôÊù°Ë∑ØÁöÑÊú´Â∞æÔºåÊòØËøûÊ∞¥‰π°ÈáåÊúÄËëóÂêçÁöщ∏ÄÂÆ∂‰∫∫ÔºåÁî∑‰∏ª‰∫∫ÂßìÈôÜÔºåÂêçÊæÑÔºåÂÅöÁöÑÊòØÊïô‰π¶ËÇ≤‰∫∫ÁöÑË°åÂΩì„ÄÇÈôÜÂÆ∂‰π¶Èô¢‰∏ç‰ΩÜÊòØËøûÊ∞¥‰π°ÈáåÁöÑËç£ËÄĉπãÂú∞ÔºåÂêç£∞ËøúÊí≠ÔºåÂÖ∂‰ªñÂ∑ûÂéøÁöÑÁôæÂßì‰∏çËøúÂçÉÁôæÈáå‰πü˶ÅÂ∞ÜÂ≠©Â≠êÈÄÅÊù•ËøôÈáåÔºåÂéüÂõÝÊòØÈôÜÂÆ∂‰π¶Èô¢ÂºÄÈô¢‰∫åÂçÅÂπ¥Êù•Ôºå‰π¶Èô¢Â≠¶Â≠ê‰∏≠‰∏≠‰π°ËØïËÄÖÊóÝÊï∞ÔºåÊõ¥Âá∫Ëøõ£´Êï∞ÂêçÔºåËá™Ê≠§‰ªïÈÄî‰∫®ÈÄöÔºåÈùí‰∫ëÁõ¥‰∏äÔºåÊïÖËÄ剺óÂÆ∂Áà∂ÊØçÊó݉∏牪•ÈÄÅÂ≠êÂÖ•Ê≠§‰π¶Èô¢‰∏∫Ë磄ÄÇËÄåÈôÜÊæÑÊú¨‰∫∫Êõ¥Êàê‰∏∫‰∫ÜËøûÊ∞¥‰π°ÈáåÊûÅÂèóÂ∞äÈáçÁöщ∫∫Áâ©ÔºåÂ∞ΩÁÆ°Âè™ÂæóÂõõÂçÅÊù•Â≤ÅÁöÑÂπ¥Á∫™Ôºå‰Ω܉∏äËá≥ÂÆòË¥æ‰∏ãËá≥‰π°Ê∞ëÔºåÊó݉∏çÂ∞䉪ñ‰∏Ä£∞‚ÄúÈôܧ´Â≠ê‚Äù„ÄÇ
•πË∑üÈôÜÊæÑÊòØÂèëÂ∞èÔºåÊÉ≥ÂΩìÂπ¥‰∏Ä˵∑Áé©Ê≥•Â∑¥ÊçâÊ≥•È≥ÖÁöÑ•ΩÂèã„ÄÇÊúâ‰∏ÄÂõû•πÊ∑òÊ∞îÔºåËêΩËøõ‰∫ÜÊùëÂâçÁöÑÊ≤≥ÈáåÔºåÊòØÈôÜÊæÑ•ã‰∏çÈ°æË∫´Âú∞Êää•πÊïë‰∏äÊù•Ôºå‰∏§‰∏™‰∫∫‰∏Ä˵∑Êå®ÊâìÁΩöË∑™ÔºåÊúÄÂêéÊòØÂπ¥ÂÑøÂÅ∑ÂÅ∑Êãø‰∫Üȶí§¥Áªô‰ªñ‰ª¨„ÄÇÂπ¥ÂÑøÊò؉ªñ‰ª¨ÁöÑË∑ü±ÅËô´Ôºå‰πüÊò؉ªñ‰ª¨ÂÖ±ÂêåÁöÑÂ∞è¶π¶πÔºåÊùëÂ≠êÈáå‰πüÊúâ‰∏çÂ∞ëÂ≠©Â≠êÔºå‰ΩÜÂè™Êú≪ñ‰ª¨‰∏â‰∏™ÊÑüÊÉÖÊúÄÂ•Ω„ÄǶÇÊûúÂΩìÂπ¥ÁöÑÁöáÂ∏ùÊ≤°ÊúâÊääʱü±±Ââ≤ËÆ©Áªô§ñÊóèÔºå¶ÇÊûú§©‰∏ãÊ≤°ÊúâÊàòÁÅ´ËøûÁªµÔºå‰ªñ‰ª¨Áöщ∫∫ÁîüËΩ®ËøπÂ∫îËØ•ÂêåÊó∂‰∏ãÁöÑÊôÆÈÄö‰∫∫‰∏ÄÊÝ∑ÔºåÂπ≥ÂÆâÈïø§ßÔºå®∂¶ªÁîüÂ≠êÔºåÈôÜÊæÑÁöщπ¶ÂøµÂæóÊúÄ•ΩÔºåÊ≤°ÂáÜÂ∞ÜÊù•ËÉΩÂÅöÁä∂ÂÖÉÔºå•πË∑üÊñØÊñØÊñáÊñáÁöÑÈôÜÊæÑÊ≠£Â•ΩÁõ∏ÂèçÔºåÂøµ‰π¶Ê≤°ÊúâÂì™Ê¨°‰∏çÂøµÂà∞ÊâìÁûåÁù°ÔºåÂîØÊúâÂ∏Æ•πÂÅöÁîüÊÑèÁöÑÁàπ®òÁÆóË¥¶Êó∂ÁÆóÂæóÂèàÂø´ÂèàÂáÜÔºåÂπ≥Êó•ÈáåËøòÂñúʨ¢ËàûÂàĺÑÊû™ÔºåÂè™Ë¶ÅÂê¨Âà∞ÈôÑËøëÊúâË∞ÅÊã≥ËÑö‰∫ÜÂæóÔºåÂ∞±Ë¶ÅÂéöÁùÄËÑ∏ÁöÆÂéªÊãúÂ∏à„Älj∏§‰∫∫Âî؉∏ÄÁõ∏ÂêåÁöщ∏ÄÁÇπÔºåÊò؉ªñ‰ª¨ÈÉΩÂñúʨ¢ÂíåÂπ¥ÂÑøÁé©„ÄÇ
Âπ¥ÂÑøÈïøÂæóʺlj∫ÆÔºåËØ¥ËØùÁªÜ£∞ÁªÜÊ∞îԺ剪ñ‰ª¨ÊúÄÂñúʨ¢Â•π‰∏ÄËæπÊãøÊâãÁª¢Áªô‰ªñ‰ª¨Êì¶ÊéâËÑ∏‰∏äÁöÑʱóÔºå‰∏ÄËæπÂóîÊÄ™ÁùÄËØ¥‰ªñ‰ª¨‰∏çÊò؉∫∫ÊòØÁå¥Â≠ê„ÄÇÊØèʨ°Âõ݉∏∫Ê∑òÊ∞îÊå®ÊâìÊå®È•øÊó∂Ôºå•πÊĪÊòØ®áʪ¥Êª¥Âú∞ËإʥªËØ•ÔºåÁÑ∂ÂêéÊâ≠Ë∫´Â∞±Ëµ∞ÔºåÂÜçË∂ÅÁùħ߉∫∫‰∏çÂú®Êó∂ÔºåÈÄÅÊ∞¥ÈÄÅÈ•≠„ÄÇÊØèʨ°Âè™Ë¶ÅÂê¨Âà∞•πËØ¥ËØùÔºåÁîöËá≥Âè™Ë¶ÅÂê¨Âà∞•π˵∞Êù•Êó∂ÁöÑËÑöÊ≠•Â£∞ÔºåÈóªÂà∞•πÂèëÈó¥ÈöêÁ∫¶ÁöÑȶôÊ∞îÔºåÊå®ÊâìÁöÑÂú∞ÊñπÈÉΩÁ´ãÂઉ∏çÁñº‰∫܉ººÁöÑ„ÄÇ
ËôΩÁÑ∂ÈÇ£‰ºöÂÑøÂπ¥Á∫™Â∞èÔºåÂ∞ö‰∏çÁü•‰Ωï‰∏∫Áî∑•≥‰πãÊÉÖÔºå‰ΩÜÈôÜÊæÑÈöêÈöêËßâÂæóÔºå¶ÇÊûúÈïø§߉∫Ü®∂™≥¶áÔºåÈÇ£ËÇØÂÆöÂ∞±ÊòØÂπ¥ÂÑø‰∫Ü„ÄÇÂáÝÂÆ∂§߉∫∫‰πüÁúãÂú®ÁúºÈáåÔºåÂè™ÊÉ≥ÁùÄÁ≠≪ñ‰ª¨ÂÜçÈïø§߉∫õÔºåÂ∞±Êää‰∫≤‰∫ãÂÆö‰∫ÜÂêß„ÄÇ
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长大,国乱了,家也散了,乱世儿女,流离失所。
一场战火,年儿被寒霖人掳走,而她没了爹娘没了家,随一位亲戚去了千里之外的南方,陆澄也跟着父母去别处逃难,原本平静安好的生活一去不回。
ÈÇ£ÂáÝÂπ¥Ôºå•πÁöÑÊó•Â≠êÁâπÂà´ÈöæÔºåÊâÄË∞ì‰∫≤ÊàöÔºå‰∏çËøáÊòØÊâìÁùÄÊî∂ÁïôÁöÑÂπåÂ≠êÔºåÂ∞Ü•πÂ∏¶Âà∞ºÇÂú∞‰Ωú‰∏∫Á´•Â∑•ÂçñÊéâÁΩ¢‰∫Ü„ÄÇÁäπËÆ∞ÂæóÂú®ÈÇ£ÊöóÊóݧ©Êó•ÁöÑÁüøÊ¥ûÈáåÔºå•πË∑ü§߉∫∫‰ª¨Âπ≤‰∏ÄÊÝ∑ÁöÑÈáçÊ¥ªÔºåÁ¥ØÂà∞ÊôïÂÄí‰πüÊ≤°Êú≺ëÊÅØÁöÑÂèØËÉΩÔºåÈ•øÊ≠ª‰∫ÜÔºåÁóÖÊ≠ª‰∫ÜÔºåÂ∞±Êä¨Âá∫ÂéªÈöè‰æøÂüãÊéâ„ÄÇ•πÈÄÉË∑ëËøáÊóÝÊï∞ʨ°ÔºåÈÉΩË¢´ÊäìÂõûÊù•Êâì‰∫܉∏™ÂçäÊ≠ª„ÄÇÊúÄÂêé‰∏Äʨ°ÈÄÉË∑ëÔºåÂ∑•Â§¥‰∏ã‰∫ÜÂëΩ‰ª§Ôºå˶ÅÊ¥ªÊ¥ªÁÝçÊéâ•π‰∏§Âè™ËÑöÁªôÊâÄÊúâ‰∫∫ÂÅö‰∏™‚ÄúʶúÊÝ∑‚ÄùÔºå‰∫éÊòØ•πË¢´Áªë˵∑Êù•ÈÄÅÂà∞‰∫ÜÈ´ò‰∏æÁöѧßÂàĉ∏ã„ÄÇ
千钧一发之际,有人挡下了那把刀,反手就取了工头的性命。
非法开采的私矿被捣毁,另一拨不知是哪里来的江湖人士,把操纵苦工草菅人命的家伙杀得落花流水。
那年她还不到十五岁。
‰øù‰Ωè•πÂèåËÑöÁöщ∫∫Êî∂Áïô‰∫Ü•π„ÄÇÈÇ£‰∏™Áî∑‰∫∫ËØ¥ÔºåÂ•Ω‰∏´Â§¥ÔºåÂàÄÈÉΩÊû∂‰∏ä‰∫ÜÔºå‰ΩÝËøûÂìºÈÉΩ‰∏çÂ캉∏Ä£∞ÔºåÂ∞èÂ∞èÂπ¥Á∫™Â∞±Êò؉∏™ÁãÝËßíËâ≤ÂïäÂìàÂìà„ÄÇ
ÁãÝËßíËâ≤ÔºüËã•ÁúüÊòØÁãÝËßíËâ≤ÔºåÂèàÊÄ鉺öÊàê‰∏∫‰ªñ‰∫∫Ê°à‰∏äÁöÑȱºËÇâ„ÄÇ
但不管怎么说,她终于脱离了人生中最暗黑困苦的日子,跟着男人回了他的家。
Êî∂Áïô‰ªñÁöÑÁî∑‰∫∫ÔºåÂßìÂùÝ„ÄÇ
Ëá≥Ê≠§Ôºå•πÂÜçÊú™Á¶ªÂºÄËøáÂùÝÂÆ∂Ժ剪éÊå£ÊâéʱÇÁîüÁöÑËã¶Â≠©Â≠êÂà∞ÂùÝÂ∫úÁöÑÂΩ±Âç´Ôºå•πÊé•ÂèóËøôÊÝ∑Áöщ∫∫Áîü„ÄÇ
ËÆ∞ÂæóÊòØÂú®Â∞ëÁà∑Âá∫ÁîüÂêéÔºå•π‰∏∫ÂÖ¨‰∫ãÂ骉∫܉∏ÄË∂üÊñ∞Ê¥≤Ôºå‰∏çÊõæÊÉ≥Âú®‰∏ÄÈó¥ÈùíÊ•ºÂ§ñËßÅÂà∞‰∫ÜË¢´ÂÆ¢‰∫∫Á∫ÝÁºÝÁöÑÂπ¥ÂÑø„ÄÇÊó∂Èöî§öÂπ¥ÔºåÈù¢ÂÆπÂ∑≤ÊîπÔºå‰Ω܉∏§‰∫∫Âç¥ÊØ´‰∏çË¥πÂäõÂú∞ËƧÂá∫‰∫ÜÂΩºÊ≠§Ôºå‰∏ĉ∏™ÊÉäÂñúÔºå‰∏ĉ∏™ÁæûÊÑßÔºå•π˵∂˵∞ÈÇ£‰∏™ÊóÝ˵ñÔºåÂ∑≤ÊîπÂêçÂè´Â∞èËâ≥Á∫¢ÁöÑÂπ¥ÂÑøʪ°ËÑ∏ÈÄöÁ∫¢ÔºåÁ¨®ÊãôÂú∞Êé©È•∞ÁùÄËإ•πËƧÈîô‰∫∫‰∫Ü„ÄÇ
ÊÄé‰πà‰ºöËƧÈîôÔºå•πË¥¶Êú¨‰∏äÁöщ∏áÂçÉÊù°Êï∞ÁõÆÔºåÂêÑÁßçÊ≠¶ÂäüÁßòÁ±ç‰∏äÁúºËä±Áº≠‰π±ÁöÑÊãõÊï∞Ôºå•πÂ∞ö‰∏î‰∏牺öËƧÈîôÂàÜÊØ´Ôºå‰∏ĉ∏™Âú®Â•π‰∏ÄÁîü‰∏≠ÊúÄÁæé•ΩÁöÑÊó∂ÂÖâÈáåÂçÝÊçƉ∫܉∏çÂèØÊõø‰ª£ÁöщΩçÁΩÆÁöÑ•ΩÂßê¶πÔºåÂèàÊÄé‰πà‰ºöËƧÈîô„ÄÇ
那天,她女扮男装,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老鸨,“包”了小艳红一晚。
“奴家名唤小艳红……”
这应该是她对每个客人都说过的话。可在她这里,却听得特别刺耳。
ÁÅØÁÅ´Ë∑≥Ë∑ÉÔºåÁÉõÊ≥™ÊóÝ£∞Ôºåʵì¶ÜËâ≥ÊäπÁöÑ•πÔºåÂú®Â•πÁúºÈáåÂç¥ËøòÊòØÂΩìÂπ¥ÈÇ£‰∏™Â®áÊÜ®ÂèØÁà±ÁöÑÂπ¥ÂÑø¶π¶π„ÄÇ
•πÊëò‰∫ÜÂ∏ΩÂ≠êÔºåÂù¶ÁôΩÔºö‚ÄúÂπ¥ÂÑøÔºåÊàëÂèØËøòËƧËØ܉ΩÝÂ뢄ÄÇ‚Äù
对方眼里划过一丝空荡荡的希望,转瞬又被吞没。
……
•πËØ¥ÂΩìÂπ¥Ë¢´ÂØíÈúñ‰∫∫Êé≥˵∞‰πãÂêéÔºå•πË∂ŧúÈÄɉ∫Ü„ÄÇÂèØ•πÈÇ£Êó∂ËøòÈÇ£‰πàÂ∞èÔºåÂèà‰∏çÁü•Ë∫´Âú®‰ΩïÊñπÔºå˵∞ÊäïÊóÝË∑؉πãÈôÖÔºåË¢´‰∏ĉ∏™Â•π‰ª•‰∏∫•ΩÂøÉÁöѧ߮òÊïë‰∫ÜÔºåËøòÊää•πÂ∏¶ÂõûÂÆ∂‰∏≠•ΩÂêÉÂ•Ω‰Ωè„Älj∏ç‰πÖ‰πãÂêéÔºå•πÂ∞±Ë¢´ÈÄÅÂà∞‰∫ÜËøôÈáå„ÄÇ•πÁü•ÈÅìËøôÈáåÊò؉∏ç•ΩÁöÑÂú∞ÊñπÔºå‰ΩÜ•πÊóÝËÉΩ‰∏∫ÂäõÔºåË∑ëËøáÔºåÂèçÊäóËøáÔºå‰ΩÜÊØèʨ°Êç¢Êù•ÁöÑÈÉΩÊòØÂêÑÁßçÁãÝÊØíÁöÑÊÉ©ÁΩö„ÄÇ•πÊÉ≥ËøáËá™Â∞ΩÔºå‰ΩÜÊúÄÁªàËøòÊòØÊîæºɉ∫ÜÔºåÂú®ËøôÁÉüËä±Âú∞Èáå±àËæ±Âú∞Ê¥ª‰∏ãÊù•„ÄÇ
Èǣ§©Â•πÊãâÁùÄ•πÁöÑË°£Ë¢ñÔºåÂÉèÂ∞èÊó∂ÂÄô‰∏ÄÊÝ∑ÔºåÊÖ¢ÊÖ¢ÊääËøôÂçÅÊù•Âπ¥ÁöÑÈÅ≠ÈÅáËÆ≤Áªô•πÂê¨Ôºå•πÁöÑ£∞Èü≥ËøòÊòØÁªÜÁªÜÊüîÊüîԺ剪ø‰Ωõ‰ªéÊù•Ê≤°ÊúâÁªèÂéÜËøቪª‰ΩïÁ£®Èöæ„ÄÇÂèØÊòØ•πËØ¥ÁöÑÊØè‰∏™Â≠óÔºå•πÂê¨Ëµ∑Êù•ÈÉΩÂÉèÊâéÂà∞Ëá™Â∑±Ë∫´‰∏äÁöÑÂàÄÔºåÁâπÂà´Áñº„ÄÇ
那天清晨,她笑着说,若当年一切如常,她应该当陆澄的媳妇,然后幸福美满,长命百岁。
•πÁö±ÁúâÔºåËØ¥ÔºåÊàëÊõø‰ΩÝ˵éË∫´„ÄÇ
说到做到。
数月后,她带着年儿来到连水乡,说以后就住在这里吧。
她很喜欢,说此地景色如画,恬淡安宁。
她说不止,还有故交在此。
陆家书院前,陆澄看着年儿,呆立片刻,旋即泣不成声。
•πÂØπÂπ¥ÂÑøÈÅìÔºåÂΩìÂπ¥‰∏ÄÂà´ÔºåÂêÑ•î‰∏úË•øÔºåÊàë‰∏ÄÁõ¥ÂتÊâæ‰Ω݉ª¨Áöщ∏ãËêΩÔºåÊĪÁÆó§©ÊúâÁúºÔºåÂâçÂπ¥Ë¢´ÊàëÂتÂà∞‰∫ÜÈôÜÊæÑԺ剪äÂπ¥Ë¢´ÊàëÈÅáÂà∞‰∫܉ΩÝ„ÄÇ
那个深秋的夜晚,他们三个在陆澄家的院子里烧肉煮酒,只说开心事。彼此缺失的那十年,如杯中烈酒,一口咽下去,再不提起。
她在连水乡住了一个月,和陆澄一道帮年儿收拾新居,采买物品,只是在年儿掏出手帕给她擦汗时,她躲开了。
Â∞öÊú™Â®∂‰∫≤ÁöÑÈôÜÊæÑÂØπÂπ¥ÂÑø‰æùÁÑ∂‰ΩìË¥¥Â§áËá≥ÔºåÂÅ∂Â∞îËøò‰ºöÂÉèÂ∞èÊó∂ÂÄôÈÇ£ÊÝ∑ÊÉ≥Âá∫ÂêÑÁßçÊ≥ïÂ≠êÈÄó•πºÄÂøÉ„ÄÇÂèØÊòØ•πÂú®Á¨ëÂá∫Êù•ÁöÑÂêåÊó∂ÔºåÂç¥ÂèàÊĪÂøç‰∏ç‰ΩèÂêëÊ≤âȪòÁöÑ•πÊäïÊù•ÊÄÖÁÑ∂Ëã•Â§±Áöщ∏ÄÁû•„ÄÇ
•πÂΩìÁÑ∂Áü•ÈÅì•πÂøÉÈáåÂú®ÊÉ≥‰ªÄ‰πàÔºåÂèØÊò؉∏çË°åÔºå•π‰∏çËÉΩÂØπ•πÁöщΩôÁîüÊú≪ª‰ΩïÊâøËØ∫ÔºåÂõ݉∏∫•πÊòØÂùÝÂÆ∂Áöщ∫∫„ÄÇË∑üÁùÄ•πÔºåÂ∞±ÊÑèÂë≥ÁùÄ˶ÅÈöèÊó∂Èù¢ÂØπÊù•Ëá™Ê±üÊπñ‰∏≠ÂêÑÁßçÂêÑÊÝ∑ÁöÑÈ∫ªÁɶ‰∏éÂç±Èô©Ôºå•πÁîöËá≥ÈÉΩ‰∏çËÉΩÁ°ÆÂÆöËá™Â∑±ËÉΩÊ¥ªÂà∞Â왉∏™Êó∂ÂÄôÔºåÂèà¶ljΩïÁªô•πÂÆâÁ®≥„ÄÇ˶ÅÈô™Âú®Â•πË∫´ËæπÁöщ∫∫ÔºåÁªùÂØπ‰∏çËØ•ÊòØ•π„ÄÇ
陆澄还是很喜欢年儿的,她看得出来。
留在一个教书先生身边,比留在一个刀头舔血的江湖人身边好多了。
离开连水乡时,她同陆澄与年儿约好,以后每年这个时候,她都来连水乡探望。
上船前,年儿叫住了她。
她回头,其实有点害怕,如果她不明白自己的用心,突然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要怎么办。
而她只是笑着说:“以后来时,给我带蜜饯吃。”
•πÊùæ‰∫܉∏ÄÂè£Ê∞îÔºåËøôÂ∞±ÊòØÊúÄ•ΩÁöÑÁªìÊûú‰∫ÜÂêß„ÄÇÊää‰ΩÝÂ∏¶ÂõûÂ∫îÊúâÁöÑÂÆâÂÆÅÔºåÂÅö‰∏ĉ∏™ÊØèÂπ¥ÈÉΩÁªô‰ΩÝÂ∏¶ËúúÈ•ØÁöÑËÄÅÊúãÂèãÔºåÁÑ∂ÂêéËøúËøúÂú∞Áúã‰ΩÝÂπ∏Á¶èÁùÄ„ÄÇ
‰∏¥Âà´‰πãÈôÖÔºå•πÂèàËøîÂõûÂéªÊãç‰∫ÜÊãçÈôÜÊæÑÁöÑËÇ©ËÜÄÔºåÂú®‰ªñËÄ≥Áïî‰Ωé£∞ÈÅìÔºö‚ÄúÊà뉪¨ÊúÄÁñºÁà±ÁöѶπ¶πԺ剪•Âêé‰ΩÝ•Ω•ΩÂæÖ•π„ÄÇ‚Äù
陆澄微愕,旋即用力点了点头。
她上了船,水声淙淙,岸边送别的人越来越远。
ÂáÝÂπ¥ÂêéÔºåÂπ¥ÂÑø‰∏éÈôÜÊæÑÊàê‰∫≤„ÄÇ
•π‰πüÊ≤°ÊúâÈ£üË®ÄÔºåÁ∫µÁÑ∂ÊòØÂú®ÂùÝÂÆ∂ÈÅ≠ÈÄ¢ÂèòÊïÖÁöÑÈÇ£‰∫õÂπ¥ÊúàÔºå•π‰æùÁÑ∂Âú®ÊØèÂπ¥ÁöÑËøô‰∏™Êó∂ÂÄôÂéªËøûÊ∞¥‰π°ÔºåÊØèʨ°ÈÉΩÂ∏¶ÁùÄʪ°Êª°‰∏ħßÂåÖÁöÑËúúÈ•Ø„ÄÇ
她从不告诉他们自己具体在干什么住在哪里,只说在一个大户人家管事,挺忙的。
他们不是江湖人,何必知晓江湖事。
灰蒙蒙的天空忽然飘起了微雨,空气骤然湿凉起来。
一贯书声琅琅的陆家书院,此刻却一反常态地安静,大门上挂着锁,门前一地残败的落叶。
她皱眉,往附近去找了个乡民打探,问陆家书院出什么事了。
那乡民直叹气,说:“是陆夫人出事了呀。”
她心下一惊:“陆夫人出了什么事?”
‚ÄúÊùĉ∫∫Âï¶ÔºÅ‚Äù‰π°Ê∞ëÁõ¥Êë᧥Ժå‚ÄúÈÇ£‰πàÊ∏©ÊüîË¥§Ê∑ëÁöщ∏ĉ∏™Â•≥Â≠êÔºåÊÉ≥‰∏çÂà∞Á´üËÉΩ‰∏ãÈÇ£ÊÝ∑ÁöÑÁãÝÊâãԺłÄù
脑袋里突然“嗡”的一声,乡民的脸跟声音都一下子飘出很远。
杀人?她连蟑螂都怕,拿什么胆子去杀人?
“杀了谁?”她定定神。
‚ÄúÂàò§´Â≠êÂïäԺłÄù‰π°Ê∞ëÈÅìÔºå‚ÄúÂéªÂπ¥ÁßãÂêéÂú®Âí±‰ª¨ËøôÂÑøÊñ∞ºĉ∫܉∏ħÑÁßÅ°æÔºåÈÇ£‰ΩçÂàò§´Â≠êËØ¥ËØùÁãǶÑÔºåÂØπÈôÜÂÆ∂‰π¶Èô¢ÂæàÊò؉∏ç±ëÔºåÂê¨ËØ¥Ëøò‰Ωø‰∫܉∫õÊâãÊƵԺåÊää‰π¶Èô¢ÁöÑÂ≠¶ÁîüÊ䢉∫ÜËøáÂ骄Älj∏çÂ∞ë‰∫∫ÈÉΩÊõøÈôܧ´Â≠êÊ䱉∏çÂπ≥Ôºå‰ΩÜÈôܧ´Â≠êÂøÉÁúºÂ•ΩËÑæÊ∞î•ΩԺ剪é‰∏ç‰∏é‰πã‰∫âÊâßÔºåÂèçËÄå§Ñ§ÑÁõ∏ËÆ©„Älj∏çÊâøÊÉ≥ÂàöÂàöËøá‰∫܉∏âÊúàÔºåÂàò§´Â≠êÂ∞±Ê®™Ê≠ªË°ó§¥ÔºåËÄåÊãøÂàÄÁÝçÊùĉ∫∫ÁöÑÔºåÊ≠£ÊòØÈôܧ´‰∫∫„ÄljºóÁõÆÁùΩÁùΩÂïäÔºåÂîâÔºÅÁúºÁúãÁùÄ•πË¢´ÊäºËøõÂéøË°ôÔºåÂê¨ËØ¥ËøáÂáÝÊó•Â∞±Ë¶ÅÊäºÈÄÅÂ∑ûÂ∫úÂèóÂÆ°ÔºåËøôÊÝ∑ÁöѧßÁΩ™ÔºåËÇØÂÆöÊòØÊ≤°Ê¥ªË∑ØÁöÑÂëÄ„Äǧ™ÂèØÊÉú‰∫ÜÔºåÈôܧ´‰∫∫ÊÄéÁöÑÈÇ£‰πàÊÉ≥‰∏çºÄÔºåÂπ≥Êó•ÈáåÈÇ£Ëà¨ÂíåÊ∞îÁöщ∏ĉ∏™Â•≥‰∫∫„ÄÇ‚Äù
她咬咬牙,问:“陆夫子现在何处?我见书院里大门紧闭。”
‚Äú‰ªñÂëÄÔºå‚Äù‰π°Ê∞ëÊóÝÊØîÊÉãÊÉúÔºå‚ÄúËá™ÊâìÈôܧ´‰∫∫Âá∫‰∫ã‰πãÂêéԺ剪ñ‰π¶Èô¢‰πü‰∏çºĉ∫ÜԺ姩§©ÈÉΩÂú®ÈõÜÂ∏lj∏úËæπÈÇ£Èó¥ÈÖíÈì∫Èáå‰π∞ÈÜâÔºåÊØèʨ°Âñù§ö‰∫ÜÈÉΩÊòØË¢´‰∫∫ÊâõÂõûÂéªÁöÑ„ÄÇ‚Äù
道了谢,她飞快地朝那间酒铺奔去。
Âõ݉∏∫‰∏ãÈõ®Ôºå‰π°ÈáåÁöÑÈõÜÂ∏lj∏äÊ≤°‰ªÄ‰πà‰∫∫ÔºåÂõõÂë®ÂÜ∑Ê∏ÖÊ∏ÖÁöÑÔºåÈÖíÈì∫ÁöÑÂ∫óÊãõÂú®È£éÈõ®Èáå‰π±ÊôÉÁùÄÔºåÊ雷∏™Â∫óÈáåÂè™ÂæóÈôÜÊæщ∏ĉ∏™ÂÆ¢‰∫∫ÔºåÁ∫¢Áùĉ∏ĺÝËÑ∏ÔºåÂñù‰∫܉∏ÄÊùØÂèà‰∏ÄÊùØ„Älj∏âÂçÅÊù•Â≤ÅÁöщªñÔºåÊÜîÊÇ¥ÂæóÂÉè‰∏ĉ∏™Â∞ÜÊ≠ªÁöÑËÄʼn∫∫„ÄÇ
她一把夺过了陆澄的酒壶。
ÈôÜÊæÑÈÜâÁúºËø∑ËíôÂú∞ÁúãÁùÄ•πÔºåÊÑ£‰∫ÜÂçäÊôåÔºåÁ¨ëÂá∫Êù•Ôºö‚ÄúÊò؉ΩÝÂïäԺʼnΩÝÊù•Âï¶Ôºü‚Äù
她没答话,径直往酒铺的厨房跟后院里看了一遍,然后回来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将其拖到后院的水缸前,硬是将他的脑袋摁进了水里。
陆澄拼命挣扎,她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才松了手。“清醒了没?”她蹲下来,冷看着瘫坐在地大口喘气的陆澄。
ÈôÜÊæÑÊÑ£‰∫ÜÂ•Ω‰∏ĉºöÂÑøÔºåÊâçÁ™ÅÁÑ∂Êäì‰Ωè•πÁöÑÊâãËáÇÔºåÂÖ®ÊóÝÂπ≥Êó•ÈáåË∞¶Ë∞¶ÂêõÂ≠êÁöÑ•ΩÊ®°ÊÝ∑ÔºåÂè∑Âì≠ÈÅìÔºö‚Äú‰ΩÝÊù•Êôö‰∫ÜÔºÅÊù•Êôö‰∫ÜԺŕπË¢´ÂÖ≥˵∑Êù•‰∫܂Ķ‚Ķ‰∏ÄÂÆö‰ºöË¢´ÁÝ秥ÁöÑԺłÄù
•πÂí¨ÁâôÔºö‚ÄúÂëäËØâÊàë‰∫ãÊÉÖÁöÑÂßãÊú´„ÄÇ•π‰∏çÊò؉ºöÂΩìË°óÊãøÂàÄÁÝç‰∫∫Áöщ∫∫ԺłÄù
‚ÄúÊÄ™ÊàëÔºåÈÉΩÊÄ™ÊàëԺłÄùÈôÜÊæÑÂêéÊÇî‰∏çÂ∑≤Ôºå‚ÄúÊàë‰∏çËøáÊòØÁßÅÂ∫ï‰∏ãÂêå•πÊä±ÊÄ®‰∫ÜÂáÝ£∞Âàò§´Â≠êÁöщ∏çÊòØÔºåÊ≤°ÊÉ≥Âà∞•πÁ´üÁÑ∂‚Ķ‚ĶÁ´üÁÑ∂ÂÅöÂá∫ËøôÊÝ∑ÁöÑÂǪ‰∫ã„ÄÇÊàëË∑ü•πËÆ≤ËøáÔºå‰∏çËÆ∫Âàò§´Â≠ê¶ljΩïÁõõÊ∞îÂáå‰∫∫Ôºå¶ljΩï‰ΩøÊâãÊƵÊä¢Êà뉪¨ÁöÑÂ≠¶ÁîüÔºåÈÉΩ‰∏ç˶ÅÁ¥ßÔºåÊà뉪¨Âè™ÁÆ°ÂÅö•ΩËá™Â∑±ÁöÑÊú¨Âà܉æøÊòØ„ÄÇÊÉ≥Êù•ÊòØËøô‰∫õÊó•Â≠êÂàò§´Â≠êʨ∫‰∫∫§™Áîö‚Ķ‚Ķ‰ΩÝÁü•ÈÅìÔºå•πÂèà‰∏çÊòØÈÇ£Áß牺öÊääÂøɧ¥ÈÉÅÁªìÊåÇÂú®Âò¥‰∏äÁöщ∫∫ÔºåÊĪÊòØÁßØÂú®ÂøÉÈáå‚Ķ‚ĶÊàëÔºåÊàë‰∏çÁü•ÈÅìËØ•ÊÄé‰πàÂäû„ÄÇÂá∫‰∫ãÊó∂ÊàëÂ∞±ÊÉ≥Êâæ‰ΩÝÔºåÂèØÊàëÊÝπÊú¨Êâæ‰∏çÂà∞‰ΩÝÂïä„ÄÇ‚Äù‰ªñÁ™ÅÁÑ∂Ë∑™‰∏ãÊù•Ôºå‚ÄúÊàë‰∏çÊÉ≥ÁúãÁùÄ•πÊ≠ªÔºåÂèØÊàëÊïë‰∏ç‰∫Ü•πÔºåÊïë‰∏ç‰∫Ü•πÂïäԺʼnΩÝÂ∏ÆÂ∏ÆÊàëÔºÅÁúãÂú®Êà뉪¨Â§öÂπ¥ËÄÅÂèãÁöÑÊÉÖÂà܉∏äԺłÄù
‚Äú‰ΩÝ˵∑Êù•ÔºÅ‚Äù•πÁ°¨ÊòØÂ∞ÜÈôÜÊæÑÊãñ˵∑Êù•Ôºå‚ÄúÂì≠Êú≪ĉπàÁî®ÔºÅ‰ΩÝËøòÊò؉∏çÊò؉∏™Áà∑‰ª¨ÂÑøԺłÄù
陆澄痛苦地摇头:“我什么都不是!我只会教人念书识字,博取功名……我什么都不会!”
“陆澄!”她怒道,“我还在!今时今日,只要我在,没有人能伤害年儿!”
ÈôÜÊæщºº‰πéÁúãÂà∞‰∫܉∏ĉ∏ùÂ∏åÊúõÔºå‰ΩÜËΩ¨ÁúºÂèàË¢´ÁªùÊúõÊ∑πÊ≤°ÔºàËøôÊƵÁ•ûÊÄÅÊèèÂÜôÊúâÁÇπÁúºÁÜüÔºâÔºö‚Äú‰∫∫Âú®Â§ßÁâ¢ÔºåËøòËÉΩÊÄéÊÝ∑Ôºüʪ°Ë°óÁöщ∫∫ÈÉΩÁúãÂà∞•πÊùĉ∫∫‚Ķ‚ĶÊàëËøûÂñäÂܧÁöÑÊú∫‰ºöÈÉΩÊ≤°Êúâ„ÄÇ‚Äù
‚Äú‰∫§ÁªôÊàë§ÑÁêÜ„ÄÇ‚Äù•πÊùæºÄÈôÜÊæÑÔºå‚Äú‰ªä§©Ôºå‰ΩÝÂ∞±ÂΩ쉪éÊú™ËßÅËøáÊàë„ÄÇ‚Äù
陆澄一愣。
ÁøåÊó•ÔºåÂéøË°ôÈáåÁÇ∏ºĉ∫ÜÈîÖÔºåÂΩìË°óÊùĉ∫∫ÁöÑÂá∂ÁäØÈôÜÊ∞èË¢´Ë∂ŧúÂä´Ëµ∞ÔºåËÄåÂá݉∏™ÊôïËøáÂéªÁöÑË°ôÂΩπÈÜíÊù•ÂêéËøûÂä´Áã±ËÄÖÊòØÁî∑ÊòØ•≥ÈÉΩ‰∏çÁü•ÈÅìÔºåÂè™ÁúãËßʼn∫܉∏ÄÈÅìÂΩ¢Â¶ÇȨºÈ≠ÖÁöÑȪëÂΩ±ÔºåÂæĉªñ‰ª¨Ë∫´‰∏äÁöÑÁ©¥ÈÅì‰∏ÄÁÇπԺ剪ñ‰ª¨‰æø§±‰∫ÜÁü•ËßâÔºåËÄåÁé∞Âú∫‰πüÊú™ÊõæÁïô‰∏㉪ª‰ΩïËõõ‰∏ùÈ©¨Ëøπ„ÄÇ
‰∏ÄÊ°àÊú™ÁªìÔºåÂèàÁîü‰∏ÄÊ°àÔºå‰∏¢ÁöÑËøòÊò؉∏ĉ∏™Êùĉ∫∫ÁäØÔºåÂéøË°ô‰∏ä‰∏ãÊó݉∏秥ÁóõËá≥ÊûÅ„ÄÇ
‰∏≠ÂçàÔºåÊü≥ÂتÈ∏¢Ë¢´Ë¶ÅʱǧöÂÅö‰∏§‰∫∫‰ªΩÁöÑÈ•≠ËèúÔºåÂéüÂõÝÊòØÂÄöÂΩ±Âç´ÂõûÊù•‰∫ÜԺ剪•ÂèäËøò§öÂ∏¶‰∫܉∏ĉΩçÂÆ¢‰∫∫„ÄÇ
这顿饭,在相当神奇的氛围里开始。
倚影卫时不时给身旁那位妇人夹菜添汤,关怀备至但又留意分寸。
ÂùÝÁøéÂÖ®Á®ãÂè™ËØ¥‰∫܉∏ÄÂè•ËØùÔºåÂØπÈǣ¶á‰∫∫Ôºö‚ÄúÈôܧ´‰∫∫Êó¢ÊòØÂÄöÂΩ±Âç´ÊïÖ‰∫§Ôºå‰æøÊòØÂùÝÂ∫úÁöÑÂÆ¢‰∫∫Ôºå‰∏îÂÆâÂøɉΩè‰∏ã„ÄÇ‚Äù
陆夫人起身还礼道谢,死里逃生后的惊惶却始终按捺不下,连举筷拿碗都小心翼翼到微微发抖。
Á∫µÁÑ∂Ëøô•≥Â≠ê‚Ķ‚ĶÂàöÊùĉ∫܉∫∫Ôºå‰Ω܉ªçÊòØÂæà•ΩÁúãÁöÑÔºåÂπ≥Êó∂ÁöÑÂßøÂÆπÊÉ≥ÂøÖÊõ¥Âºï‰∫∫Ê≥®ÁõÆ„ÄljπîÈòøÊôƉ∏ÄËæπÂñùʱ§‰∏ÄËæπÁõØÁùÄ•πÊ≠ªÊ≠ªÂú∞ÁúãÔºå•ΩÂáÝʨ°Â•πÊóÝÊÑè‰∏≠Ë߶Âà∞‰πîÈòøÊôÆÁöÑËßÜÁ∫øÔºåÊÝπÊú¨‰∏çÊï¢ÂÅúÁïôÔºåÁ´ãÂàªÂü㧥ÁúãËá™Â∑±ÁöÑÁ¢óÔºåÂ∞èÂè£Â∞èÂ裉∏çÊñ≠Âú∞ÂêÉËèú„Äljº∞ËÆ°‰ª•Â•πÊ≠§ÂàªÁöÑÂøÉÊÉÖËÇØÂÆöÊóÝÊ≥ïÂàÜËæ®È•≠ËèúÁöÑÂë≥ÈÅìÔºåÊØïÁ´üÊü≥ÂتÈ∏¢ÁöÑÊâãËâ∫ÔºåËÉΩ‰∏ÄÂè£Ê镉∏ÄÂè£Âêɉ∏ãÂéªÁöщ∫∫‰∏çÊòØËà姥ÊúâÈóÆÈ¢òÂ∞±ÊòØÂøÉÁêÜÊúâÈóÆÈ¢ò„ÄÇËôΩÁÑ∂‰ªñÊúÄËøëÂÅöÈ•≠ËƧÁúü‰∫܉∏çÂ∞ëÔºåÂπ∂‰∏îÊáÇÂæóÂéªÂ§ñ§¥ÁöÑÈ•≠ȶÜÊâìÂåÖÔºå‰ΩÜ•π‰∏çÂÅúÂú®ÂêÉÁöÑÈÇ£ÁõòËèúÊòéÊòéÊòØÊü≥ÂتÈ∏¢ÁöÑÊâãÁ¨îÔºåÁÇíÂæóÂèàÂí∏ÂèàÂπ≤„ÄÇ
ÂùÝÂ∫úÁöÑÈ•≠Ê°åÊØ•ÂâçÁÉ≠Èóπ§ö‰∫ÜÔºåÂú®ÂùÝÁøéÁöÑ˶Åʱlj∏ãÔºå‰πîÈòøÊôÆÊü≥ÂتÈ∏¢‰ª•ÂêéÈÉΩÊù•Ë∑ü‰ªñ‰ª¨‰∏ÄÈÅìÂêÉÈ•≠ÔºåÊØïÁ´ü‰ª•Ââç‰∏ÄÂà∞È•≠ÁÇπÔºåÊ°å‰∏äÂ∞±‰ªñÂíå±ïÂ∏àÂÇÖ§ñÂä݉∏ĉ∏™ÂÄöÂΩ±Âç´Ôºå‰∫∫Â∞ëÂêɉ∏úË•øÈÉΩ‰∏çȶô„ÄljπîÈòøÊôÆÂøÉËØ¥ÔºåÂè™Ë¶ÅÂì•ÊéåÂã∫Ôºå‰ΩÝÊääÂÖ®‰∫¨ÂüéÁöщ∫∫ÈÉΩ°û‰ΩÝÂÆ∂È•≠Ê°å‰∏äÔºåÈÉΩ‰∏牺öÂêÉÂæóȶô„ÄljΩÜÊòØ•π‰ªçÁÑ∂ÈùûÂ∏∏ÊÑâÂø´Âú∞Êé•Âèó‰∫ÜÂùÝÁøéÁöÑÈÇÄËØ∑ÔºåËÉΩ‰∏äÂùÝÂÆ∂ÁöÑÈ•≠Ê°åÔºåËèúÂ•Ω‰∏ç•ΩÂêÉÂÖà‰∏çËØ¥Ôºå˵∑ÁÝÅËøôÊÝ∑ÊØ觩ÈÉΩËÉΩÂú®Âõ∫ÂÆöÊó∂Èó¥Ê≠áÁùĉ∫ÜÂëÄÔºåÁæéʪãʪã„ÄÇ
‚ÄúÊù•Êù•ÔºåÈôܧ´‰∫∫‰ΩÝÂêɉ∏™È∏°ËÖø„ÄÇ‚Äù‰πîÈòøÊôÆÂçÅÂàÜ•ΩÂÆ¢Âú∞ÊääÊü≥ÂتÈ∏¢ÊâìÂåÖÂõûÊù•ÁöÑÈ•ïȧÆÊ•ºÁöÑÈÖ±È∏°ËÖø§πÂà∞Èôܧ´‰∫∫Á¢óÈáå„ÄÇ
要是平时,柳寻鸢肯定会和她骂一会儿,但是今天没有。
这么正常,太不正常了。
±ïÂ∏àÂÇÖ˵∂Á¥ß§π‰∫܉∏ÄÊÝπÈùíËèúÊîæÂà∞Êü≥ÂتÈ∏¢Á¢óÈáåÔºåÂäùÈÅìÔºö‚ÄúÂêÉÈ•≠ÂêÉÈ•≠ÔºåÈ£ü‰∏çË®ÄÂØù‰∏çËØ≠„ÄÇ‚Äù
柳寻鸢嫌弃地把青菜填进嘴里,半路上却被蹲在乔阿普腿上的花虎把菜叼走了。
‚Äú‰ªÄ‰πàÊó∂ÂÄôÁå´‰πüËÉΩ‰∏äÊ°åÂêÉÈ•≠‰∫ÜԺłÄùÊü≥ÂتÈ∏¢ËÑ∏Ëâ≤Êúâ‰∏ÄÁÇπÁôΩÔºå‚Äú‰ΩÝÁöÑÁå´Âò¥Á¢∞Âà∞ÊàëÁöÑÁ≠∑Â≠ê‰∫ÜÔºÅÊ≤æ‰∏äÁå´Âè£Ê∞¥ÊàëËøòÊÄé‰πàÂêÉԺłÄù
‚ÄúÁå´‰∏∫Â∏çËÉΩ‰∏Ä˵∑ÂêÉÈ•≠Ôºü‰ºóÁîüÂπ≥Á≠âÂïäÊü≥ÂتÈ∏¢„ÄÇ‚Äù‰πîÈòøÊôÆÂçÅÂàÜÊóÝËæú„ÄÇ
ÁúãÁùÄÁúºÂâçËøôÂá݉∏™ËÉ°ÈóπÁöÑÂπ¥ËΩª‰∫∫ÔºåÈôܧ´‰∫∫Êúâ‰∫õÂ∞¥Â∞¨Âú∞Á¨ë‰∫ÜÁ¨ëÔºåËΩªÂ£∞ÂØπÂÄöÂΩ±Âç´ÈÅìÔºö‚ÄúÂÄöÂßêÂßêÔºåÊÉ≥‰∏çÂà∞‰ΩÝËøôÈáå¶ÇÊ≠§ÁÉ≠Èóπ„ÄÇ‚Äù
ÂÄöÂΩ±Âç´ÊóÝ•àÈÅìÔºö‚ÄúÈô§‰∫ÜÊàëÂÆ∂Â∞ëÁà∑Á®≥ÈáçÔºåÂÖ∂‰ªñ‰∫∫Âòõ‚Ķ‚Ķ‰ΩÝËé´Ë¢´‰ªñ‰ª¨ÂêìÂà∞Êâç•ΩÔºåËøô‰∫õÂ∞èÂ≠ê‰∏´Â§¥Âè™Ë¶ÅËÅöÂú®‰∏Ä˵∑ÔºåÂÖç‰∏ç‰∫ÜÊâìÊâìÈóπÈóπ„ÄÇ‚Äù
•πËøûÂøôÊëÜÊâãÔºö‚Äú‰∏çÊâìÁ¥ß‰∏çÊâìÁ¥ßÔºåËøôÊÝ∑Êå∫•ΩÔºå‰∏ħßÂÆ∂Â≠ê‰∫∫Âú®‰∏Ä˵∑Ôºå§öÁÉ≠Èóπ„Älj∏çÂÉèÊà뉪¨ÂÆ∂Ôºå‰∏ÄÂπ¥Âà∞§¥È•≠Ê°å‰∏äÈÉΩÂè™ÊúâÊàëË∑üÊæÑÂì•Â앉∏§‰∫∫ÔºåÂÜ∑Ê∏ÖÊ∏ÖÁöÑ„ÄÇ‚Äù
ÈóªË®ÄÔºåÂùÝÁøéÂøΩÁÑ∂ÈóÆÈÅìÔºö‚ÄúÂê¨Èôܧ´‰∫∫ËøôËà¨ËÆ≤ÔºåËé´ÈùûÂÑø•≥Âú®ËøúÊñπÔºü‚Äù
‚ÄúËã•Âú®ËøúÊñπÂÄí‰πüÁΩ¢‰∫Ü„ÄÇ‚Äù•πËã¶Á¨ëÁùÄÊëáÊë᧥Ժå‚ÄúÊÉ≠ÊÑßÔºåÊà뉪¨Â§´Â¶áËá≥‰ªäËÜù‰∏ãÁäπËôö„ÄÇÂΩìÂπ¥‰πüÊõæÊúâËøá‰∏ĉ∏™Â≠©Â≠êÔºåÂèØÊÉúÂ∞öÊú™Âá∫‰∏ñ‰æø§≠Êäò‰∫ÜÔºå‰πãÂêéÊàëÂÜçÊóÝÊâÄÂá∫„ÄÇ‚Äù
“来来,继续吃。”倚影卫赶紧出来打断这个沉重的话题,“过去的事不要想了,以后都会好起来的。”
‰πüËÆ∏ÔºåÂÖ®‰∫¨ÂüéÈáåÂè™ÊúâÂùÝÂ∫úÁöщ∫∫Êâ牺ö§ßËÉÜÊàêËøôÊÝ∑Ôºå‰∏ç‰ΩÜÊï¢Êî∂Áïô‰∏ĉ∏™ÈìÅÂÆöË¢´ÈóÆÊñ©ÁöÑÊùĉ∫∫ÁäØÔºåËøòËÉΩËã•ÊóÝÂÖ∂‰∫ãÂú∞‰∏é‰πãÂêåÊ°åÂêÉÈ•≠ÔºåÈó≤ËØùÂÆ∂Â∏∏„ÄÇ
ÂÄöÂΩ±Âç´‰∏ÄÂõûÊù•Ôºå‰æøÂ∑≤Â∞ÜÊ≠§Ë°åÁöÑÈÅ≠ÈÅá‰∏éÈôܧ´‰∫∫ÁöÑÊù•ÂéÜËÉåÊôØÊ∏ÖÊ∏ÖÊ•öÊ•öÂú∞‰∫§ÂæÖÁªô‰∫ÜÂùÝÂ∞ëÁà∑ÔºåËÄå‰πîÈòøÊôÆËøô‰∏™ÂÅ∑Âê¨ÁöѧßÂò¥Â∑¥‰∏ÄËΩ¨Â§¥Â∞±ÁÇπʪ¥‰∏çʺèÂú∞ÊääËøô‰ª∂‰∫ãÂΩì‰Ωú‰∏ĉ∏™Â§ßÂÖ´Âç¶ËÆ≤ÁªôÊü≥ÂتÈ∏¢Âꨉ∫Ü„ÄljΩÜÈóÆÈ¢òÊòØÔºå•πÁöÑÈáçÁÇπÁ´üÁÑ∂‰∏çÊòØÈôܧ´‰∫∫ÊòØÊùĉ∫∫ÁäØÔºåËÄåÊòØÂÄöÂΩ±Âç´Â±ÖÁÑ∂Â∏¶Â•≥ÁöÑÂõûÂÆ∂Êù•‰∫ÜÔºåÈïøÂæóËõÆ•ΩÁúãÂíßÔºå‰∏çËøá‰∫∫ÂÆ∂Â∑≤Áªè´ʼn∫∫‰∫ÜÔºåËøôÂêéÈù¢Áöщ∫ã‰∏ç•ΩÂäûÂïä„ÄÇÊü≥ÂتÈ∏¢ÂΩìÊó∂Â∞±ÊÉ≥ÂäàºÄ•πÁöÑËÑëË¢ãÁúãÁúãÈá姥ÊòØÂì™ÈÉ®ÂàÜÂá∫ÊØõÁóÖ‰∫܂Ķ‚Ķ‰∏§‰∏™Â•≥ÁöÑÊòéÊòéÂ∫îËØ•ÊòØÂèãÊÉÖÔºåËøôÊÄé‰πà‰πüËÉΩÊÉ≥Ê≠™„ÄÇ
ËÄåÂùÝÁøéÂú®Âê¨ÂÆåÂÄöÂΩ±Âç´ÁöÑʱáÊ䕉πãÂêéÔºåÂè™ËØ¥‰∫܉∏â‰∏™Â≠óÔºö‚ÄúÂæàÈ∫ªÁɶ„ÄÇ‚Äù
ÂÄöÂΩ±Âç´ÂΩìÂç≥Ë∑™‰∏ãÔºåÊã±ÊâãÈÅìÔºö‚ÄúÊ≠§Ê¨°ÊòØÊàëÈ≤ÅËéΩÔºåÂΩìÁ´ãÂç≥Â∏¶Â•πÁ¶ªÂºÄÔºåÁªù‰∏çÁªôÂùÝÂÆ∂Â∏¶Êù•ÂçäÂàÜÈ∫ªÁɶ„ÄÇ‚Äù
‚ÄúÈÇ£ÂÄí‰∏çÁÄÇ‚ÄùÂùÝÁøéÁøªÁùĉªñÁöщπ¶Ôºå‚ÄúÊ≤°ÊúâÈ∫ªÁɶԺåÂùÝÂ∫úÂèà¶ljΩïËߣÊòØÈùû„ÄÇ‚Äù
‚ÄúÂ∞ëÁà∑‚Ķ‚Ķ‚ÄùÂÄöÂΩ±Âç´Âøɧ¥‰∏ÄÁÉ≠ÔºåÈáçÈáçÁªô‰ªñÁ£ï‰∫܉∏™Â§¥„ÄÇÂæó‰∫ÜÂùÝÁøéÁöÑÂÖÅËÆ∏Ôºå•πÊ≠§ÂàªËá≥Â∞ëÊòØÊúâ‰∫ÜÂÖ®‰∫¨ÂüéÊúÄÂÆâÂÖ®ÁöÑÂ∫áÊä§ÊâÄÔºå‰πãÂêéÁöщ∫ãÔºåÂÜçËØ¥ÂêßÔºå•π‰∏çÁõ∏‰ø°Â•π‰ºöÂΩìË°óÊùĉ∫∫Ôºå‰∏ÄÁÇπÈÉΩ‰∏çÁõ∏‰ø°„ÄÇ
‰πîÈòøÊôÆÁ¨¨‰∏Äʨ°ËßÅÂà∞Èôܧ´‰∫∫Êó∂ÔºåÂ∞±ÂØπËøô‰∏™Â®áÂ∞èÁé≤Áèë„ÄÅË∫≤Ë∫≤Èó™Èó™Âú∞Ë∑üÂú®ÂÄöÂΩ±Âç´Ë∫´ÂêéÁöÑ•≥Â≠êʵÅÈú≤Âá∫‰∫ÜÊûŧßÁöÑÂÖ¥Ë∂£ÔºåÂú®ÂÅ∑Âꨉ∫ÜÂÄöÂΩ±Âç´ÊèèËø∞ÁöÑ•π‰∏éÂÄöÂΩ±Âç´ÁöÑÊ∏äÊ∫ꉪ•Âèä•πÈÅ≠ÈÅáÁöѧßÁ•∏‰πãÂêéÔºå•πÈóÆÂùÝÁøé˶ÅÊÄé‰πà§ÑÁêÜËøô‰ª∂‰∫ã„ÄÇÂùÝÁøéËØ¥‰∏îÁúãÁúãÂÜçËØ¥ÔºåËØ¥ÁöÑÊòØÁä؉∫ÜÂΩìË°óÊùĉ∫∫ÁöѧßÁΩ™Ôºå‰ΩÜÂê¨ÂÄöÂΩ±Âç´Ë®Ä‰πãÂáøÂáøÂú∞Ëإ•π‰∏çÂèØËÉΩÂÅöËøôÊÝ∑Áöщ∫ãÔºåÊàñËÆ∏Èá姥ÁúüÁöÑÂè¶ÊúâÂà´ÊÉÖ„ÄljπîÈòøÊôÆÊíáÊíáÂò¥ÔºåËØ¥Âç≥‰æøÊúâÈöêÊÉÖÔºå‰ΩÜ•π‰ºóÁõÆÁùΩÁùΩÂΩìË°óÊùĉ∫∫Êò؉∏ç‰∫âÁöщ∫ãÂÆûÔºåÈöæ‰∏çÊàê‰Ω݉ª¨ÂùÝÂ∫úËøòËÉΩÂáåÈ©æ‰∫éÂæãÊ≥ï‰πã‰∏äÔºüÂùÝÁøéÊÉ≥‰∫ÜÂç䧩ÊâçËØ¥ÔºåÊòØÂæàÈ∫ªÁɶԺå‰ΩÜÂùÝÂ∫ú‰∏ìÂπ≤Ëøô‰∏™Ôºå‰ΩïÂܵÈÇ£ÊòØÂÄöÂΩ±Âç´Â∏¶Êù•Áöщ∫∫Ôºå‰∏çÁúãÂÉßÈù¢Áúã‰ΩõÈù¢Âïä„ÄÇ
Âê¨ÁΩ¢Ôºå‰πîÈòøÊôÆÂè™ÂòÄÂíï‰∫܉∏ÄÂè•ÔºåËøôʨ°ÁöÑÈ∫ªÁɶÂè™ÊÄï‰Ω݉ª¨Â∫ò‰∏ç‰∫Ü„ÄÇ
•ΩÊ≠πÊòØÂπ≥Âπ≥ÂÆâÂÆâÂêÉÂÆå‰∫ÜËøôÈ°øÈ•≠ÔºåÂùÝÁøéÂØπÂÄöÂΩ±Âç´ÈÅìÔºö‚ÄúÈôܧ´‰∫∫Â∞±‰∫§ÁΩÝÂÆâÈ°øÂêßÔºåÂ∫ú‰∏≠Á©∫ÊàøÈ¢á§öÔºåÁùÄÂá݉∏™Â∞èÂéÆÂéªÊî∂Êãæ‰∏ÄÈó¥ÔºåÂÜçÊâæ‰∏™‰∏´È¨ü‰º∫ÂÄô˵∑±քÄÇ‚Äù
“是。”倚影卫点头,“多谢少爷。”
‚Äú‰∏çÁî®Ëøô‰πàÈ∫ªÁɶ‰∫Ü„ÄÇ‚ÄùÈôܧ´‰∫∫ÂçÅÂà܉∏ç•ΩÊÑèÊÄùÔºåÂøôËØ¥Ôºå‚ÄúÊâìÊâ∞Â∫ú‰∏äÂ∑≤ÊòاߧßÁöщ∏çËØ•ÔºåÊÄéËøòËÉΩÂä≥Áɶ‰Ω݉ª¨ÈÅ£‰∫∫Êù•‰º∫ÂÄô„ÄÇ‚Äù
‚ÄúÈôܧ´‰∫∫Ë®ÄÈáçÔºåÊàëÂ∫úÈÇ∏Áîö§ßÔºå‰ΩÝÂàùÊù•‰πçÂà∞ÂøÖ‰∏çÁÜüÊÇâÔºåÊúâ‰∏™‰∏´È¨üÂú®ÊóÅÁÖßÈ°æÊòØÊúÄ•ΩÁöÑÔºåÂ∞±‰∏ç˶ÅÊé®Ëæû‰∫Ü„ÄÇ‚ÄùËØ¥ÁΩ¢Ôºå‰ªñËΩ¨Âêë‰πîÈòøÊôÆÔºå‚Äú‰πî‰∏´Â§¥ÔºåÈôܧ´‰∫∫Â∞±Âä≥‰ΩÝÁÖßÊñô‰∫Ü„ÄÇ‚Äù
乔阿普一翻白眼:“我还要饲药鼎呢!”
‚Äú‰ΩÝÊØ觩Êúâ§öÈó≤Áúü‰ª•‰∏∫Êàë‰∏çÁü•ÈÅìÔºü‚ÄùÂùÝÁøéÂàÄÔºå‚ÄúÈôܧ´‰∫∫‰∫§Áªô‰Ω݉∫ÜÔºåÊúâÂçäÁÇπÈó™Â§±ÔºåÂ∞èÂøɉΩÝÁöÑÂ∑•Èí±„ÄÇ‚Äù
软肋……对穷人来说这绝对是软肋……她一梗脖子:“去就去!”
“不不,真的不用了。”陆夫人连忙推辞,“姑娘既然有自己的事,就不要为我劳神,我实在担当不起。”
‚ÄúÊ≤°‰∫ãÊ≤°‰∫ãÔºåÊàëÊú¨Â∞±ÊòØÂùÝÂ∫úÁöÑÊùÇÂΩπÔºåÂ∞ëÁà∑ËØ¥‰ªÄ‰πàÊàëÂ∞±ÂæóÂꨉªÄ‰πà„ÄÇ‚Äù‰πîÈòøÊôÆÂøôÂØπ•πÈÅìÔºå‚ÄúÈôܧ´‰∫∫‰ΩÝË∫´ËæπÁ°ÆÂÆû˶ÅÊúâ‰∏™‰∫∫Ôºå‰∏çÁÑ∂‰Ω݉∏ÄÂÆö‰ºöÂú®ÂùÝÂ∫úÈáåËø∑Ë∑ØÁöÑ„ÄÇ‚Äù
‚ÄúÂ∞±‰∏ç˶ÅÊé®Ëæû‰∫Ü„ÄÇ‚ÄùÂÄöÂΩ±Âç´ÁúãÁùÄ•πÔºå‚Äú‰πî‰∏´Â§¥Âú®‰ΩÝË∫´ËæπÔºåÊàë‰πüÊîæÂøɉ∫õ„ÄÇ‚Äù
陆夫人看了看大家,犹豫片刻,终是点点头,又对乔阿普施礼道:“那就有劳姑娘了。”
“不劳不劳,陆夫人有啥要求尽管跟我说,千万不要憋屈了自己。”乔阿普说。
‰∫ãÊÉÖÂ∞±Ëøô‰πàÈ£éËΩª‰∫ëÊ∑°Âú∞ÂÆö‰∫܉∏ãÊù•„ÄÇÂÄöÂΩ±Âç´Â∏¶Âõû‰∫܉∏ĉ∏™Áä؉∏ãÊùĉ∫∫ÁΩ™ÁöÑËÄÅÊúãÂèãÔºåÂùÝÁøé‰∫åËØù‰∏çËØ¥ÂêåÊÑèÊî∂ÁïôÔºåÊĪ‰πãÂùÝÂ∫ú‰∏ä‰∏㉺º‰πéÂØπËøôÁßç‚ÄúÈ∫ªÁɶ‚ÄùÂ∑≤ÁªèËßÅÊÉ؉∏çÊęԺåÈô§‰∫܉πîÈòøÊôÆÊĪÊòØÊ虉ΩèÂêåÊÄßËøô‰∏ÄÁÇπÊääÂÄöÂΩ±Âç´ÈÉΩ˶ÅÈóÆÁɶ‰∫܉πã§ñÔºå§ßÂÆ∂ÈÉΩÁõ∏ÂΩìÂπ≥ÈùôԺ剪ø‰ΩõÂè™ÊòØÊù•‰∫܉∏™ÊôÆÈÄöÂÆæÂÆ¢ÁΩ¢‰∫Ü„ÄÇ
‰πîÈòøÊôÆÂØπ‰∫éÂùÝÁøéÂè¶ÂäÝÁªô•πÁöщªªÂä°ÔºåÈô§‰∫ÜÂòÄÂíïÂáÝÂ蕉πã§ñÔºåÂπ∂Ê≤°Êúâº∫ÁÉàÂèçÂØπÔºåÂèçËÄåÁâπÂà´È∫ªÂà©Âú∞ÂõûÂéªËá™Â∑±ÁöщΩè§ÑÔºåÊî∂Êãæ‰∫܉∫õÊó•Â∏∏Áî®Áöщ∏úË•øÔºå‰æøÂåÜÂåÜÂøôÂøôÂæÄÂÆ¢ÊàøÈÇ£ËæπÂ骉∫Ü„ÄÇ
(八千字奉上!本美女要发力了!)
相关推荐
 连载中
连载中
心魔剑道
 连载中
连载中
十八英雌
 ËøûËΩΩ‰∏≠
连载中
ºÄ±ÄÈì∏Â∞±Êó݉∏äÊÝπÂü∫ÔºåÊàëÈóÆȺ鉪ôË∑ØÔºÅ
 ËøûËΩΩ‰∏≠
连载中
ÊòéÂÝï‰πùÂπ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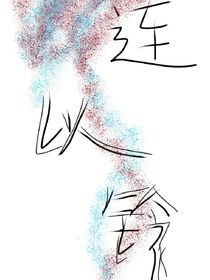 连载中
连载中
连以铃
 ËøûËΩΩ‰∏≠
连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