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з« пјҡзҺ„еӨңиӘ“е”ӨпјҢжқЁзҺүе…ұйқўеҜ№
еӨңйЈҺеҲ®иҝҮеұӢжӘҗпјҢйҷҲзҺ„еӨңз«ҷеңЁе··еҸЈжІЎеҠЁгҖӮжүӢиҝҳжҢүеңЁиғёеҸЈпјҢзҺүдҪ©зҡ„зғӯеәҰжІЎжңүйҖҖпјҢеғҸжҳҜиҙҙзқҖдёҖеқ—зғ§иҝҮзҡ„й“ҒзүҮгҖӮд»–дҪҺеӨҙзңӢдәҶзңјжҺҢеҝғпјҢд№ӢеүҚе’¬з ҙзҡ„ең°ж–№з»“дәҶз—ӮпјҢдҪҶжҢҮзјқйҮҢиҝҳжңүе№ІжҺүзҡ„иЎҖз—•гҖӮ
д»–еҫҖеүҚиө°пјҢи„ҡжӯҘжҜ”еҲҡжүҚзЁігҖӮжқЁе…„з»ҷзҡ„й“ңзүҢжҸЈеңЁжҖҖйҮҢпјҢжҜҸиө°еҮ жӯҘе°ұзў°дёҖдёӢиӮӢйӘЁпјҢзЎ®и®ӨиҝҳеңЁгҖӮе·ЎеӨңзҡ„жўҶеӯҗеЈ°д»ҺиҝңеӨ„дј жқҘпјҢдёүжӣҙеҲҡиҝҮпјҢиЎ—дёҠжІЎдәәпјҢеҸӘжңүеҮ еҸӘйҮҺзӢ—еңЁеўҷж №зҝ»йЈҹи…җиӮүгҖӮ
жңұйӣҖжҘјеңЁеҚ—иҫ№пјҢй«ҳиҝҮеҹҺеўҷдёҖеңҲпјҢй»‘еҪұз«ӢеңЁеӨ©иҫ№еғҸдёҖж №жҲіз ҙеӨңзҡ„жҹұеӯҗгҖӮд»–и®°еҫ—иҝҷең°ж–№пјҢд»ҘеүҚж··еёӮдә•ж—¶еҗ¬иҜҙпјҢзҷ»йЎ¶иғҪжңӣи§ҒеҚҠдёӘй•ҝе®үпјҢе°Өе…¶жҳҜеҚҺжё…жұ йӮЈиҫ№пјҢеӨңйҮҢжңүж°ҙе…үеҸҚзқҖжңҲиүІгҖӮ
д»–жІЎиө°жӯЈиЎ—пјҢиҙҙзқҖж°‘е®…еӨ–еўҷз»•иЎҢгҖӮдјӨи…ҝе·Із»ҸдёҚжӢ–ең°дәҶпјҢдҪҶиё©дёҠеҸ°йҳ¶ж—¶иҝҳжҳҜеҸ‘жІүгҖӮдёҖеҸЈж°”зҲ¬дёҠдёғеұӮпјҢжҺЁејҖжңЁй—ЁпјҢеҶ·йЈҺзӣҙжҺҘзҒҢиҝӣжқҘгҖӮд»–йқ еңЁж ҸжқҶдёҠе–ҳдәҶеҸЈж°”пјҢжҘјдёӢдёҖзүҮжјҶй»‘пјҢиҝһдёӘе®ҲеҚ’зҡ„зҒҜз¬јйғҪжІЎжңүгҖӮ
д»–зӣҳи…ҝеқҗдёӢпјҢжҠҠзҺүдҪ©ж”ҫеңЁиҶқзӣ–дёҠгҖӮе®ғиҮӘе·ұеңЁеҸ‘е…үпјҢж·Ўж·Ўзҡ„зҷҪпјҢеғҸжҳҜд»ҺеҶ…йғЁжё—еҮәжқҘзҡ„гҖӮд»–й—ӯзңјпјҢз…§е®ҲеўҹиҖҒдәәж•ҷзҡ„жі•еӯҗпјҢдёҖжҒҜдёҖеҗҗпјҢжҠҠдҪ“еҶ…д№ұзӘңзҡ„ж°”жҒҜеҫҖдёӢеҺӢгҖӮдё№з”°еӨ„еғҸжңүж №й’ҲжқҘеӣһжүҺпјҢдҪҶд»–жІЎеҒңгҖӮ
зқҒејҖзңјж—¶пјҢиҘҝеҚ—ж–№дёҖзӮ№еҫ®е…үжө®еҠЁгҖӮд»–зҹҘйҒ“йӮЈжҳҜеҚҺжё…жұ зҡ„ж–№еҗ‘гҖӮ
вҖңжҲ‘дёҚжҳҜд»Җд№Ҳе‘Ҫе®ҡд№ӢдәәгҖӮвҖқд»–ејҖеҸЈпјҢеЈ°йҹідёҚеӨ§пјҢдҪҶйЈҺжІЎжҠҠе®ғеҗ№ж•ЈпјҢвҖңжІЎеёҲзҲ¶пјҢжІЎйқ еұұпјҢиҝһеҠҹжі•йғҪжҳҜдёңжӢјиҘҝеҮ‘жқҘзҡ„гҖӮвҖқ
д»–йЎҝдәҶйЎҝпјҢдјёжүӢжҸЎдҪҸзҺүдҪ©гҖӮ
вҖңеҸҜжҲ‘зӯ”еә”иҝҮиҰҒжқҘгҖӮвҖқ
иҜқиҗҪпјҢжҢҮе°–з”ЁеҠӣпјҢеҲ’з ҙжҺҢеҝғгҖӮиЎҖйЎәзқҖзә№и·ҜжөҒдёӢпјҢж»ҙеңЁзҺүдҪ©иЎЁйқўгҖӮе®ғзҢӣең°дёҖйңҮпјҢе…үзһ¬й—ҙжү©ж•ЈпјҢеғҸдёҖеұӮи–„йӣҫзҪ©дҪҸдәҶж•ҙеә§жҘјйЎ¶гҖӮ
иҝңеӨ„дә‘еұӮејҖе§ӢеҠЁпјҢеҫҖиҝҷиҫ№иҒҡгҖӮзҡҮе®«ж–№еҗ‘дј жқҘдёҖеЈ°й—·е“ҚпјҢеғҸжҳҜй’ҹиў«ж•ІдәҶдёҖдёӢпјҢеҸҲдёҚеғҸгҖӮз©әж°”еҸҳеҫ—йҮҚпјҢе‘јеҗёйғҪиҙ№еҠІгҖӮ
д»–зҹҘйҒ“йӮЈжҳҜжӯҰеҲҷеӨ©з•ҷдёӢзҡ„дёңиҘҝеңЁеҸҚеә”вҖ”вҖ”йҫҷж°”й”ҒйӯӮйҳөгҖӮдёҚжҳҜжҙ»дәәиҜҘзў°зҡ„зҰҒеҲ¶пјҢдё“дёәеҺӢеҲ¶еғҸжқЁзҺүзҺҜйӮЈж ·зҡ„е‘Ҫж јиҖҢи®ҫгҖӮ
зҺүдҪ©зҡ„е…үејҖе§ӢжҠ–пјҢеғҸжҳҜиў«д»Җд№ҲдёңиҘҝеҺӢејҜдәҶи…°гҖӮ
他没收жүӢпјҢеҸҚиҖҢжҠҠзҺүдҪ©иҙҙеҲ°зңүеҝғгҖӮйўқеӨҙдёҖйҳөеҲәеҮүпјҢи„‘жө·йҮҢзӘҒ然жө®еҮәдёҖеҸҘиҜқпјҡеҘ№е–ңж¬ўжў…иҠұгҖӮ
д»–е°ұиҝҷд№Ҳи®°дҪҸдәҶгҖӮ
вҖңдҪ иҜҙеҶ·йҰҷиғҪи®©дәәеҝғйқҷгҖӮвҖқд»–дҪҺеЈ°иҜҙпјҢвҖңзҺ°еңЁеӨ–йқўжҳҜйЈҺйӣӘпјҢдҪҶжҲ‘жқҘдәҶгҖӮжҲ‘д№ҹеёҰжқҘдәҶејҖжҳҘзҡ„ж¶ҲжҒҜгҖӮвҖқ
иҝҷиҜқеғҸжҳҜдёҖжҠҠй’ҘеҢҷпјҢиҪ»иҪ»дёҖиҪ¬гҖӮ
еӣӣе‘Ёзҡ„еҺӢиҝ«ж„ҹиЈӮејҖдёҖйҒ“зјқгҖӮзҺүдҪ©зҡ„е…үдёҚеҶҚжҢЈжүҺпјҢиҖҢжҳҜзј“зј“й“әејҖпјҢйЎәзқҖйЈҺжөҒеҗ‘иҘҝеҚ—гҖӮ
д»–зҡ„ж„ҸиҜҶи·ҹзқҖйЈҳеҮәеҺ»гҖӮ
зңјеүҚеҸҳжҲҗдёҖзүҮ银зҷҪгҖӮж°ҙеә•ж·ұеӨ„пјҢдёҖдёӘдәәеҪұжӮ¬еңЁйӮЈйҮҢгҖӮзҷҪиЎЈпјҢй•ҝеҸ‘ж•ЈејҖпјҢеғҸзқЎзқҖдәҶдёҖж ·гҖӮе‘Ёеӣҙжңүз¬Ұж–ҮжөҒиҪ¬пјҢдёҖеңҲеңҲеӣҙзқҖеҘ№иҪ¬пјҢеғҸжҳҜй”Ғй“ҫпјҢеҸҲеғҸжҳҜдҝқжҠӨгҖӮ
еҘ№зқ«жҜӣеҠЁдәҶдёҖдёӢгҖӮ
然еҗҺпјҢдёҖдёӘеЈ°йҹізӣҙжҺҘеҮәзҺ°еңЁд»–и„‘еӯҗйҮҢпјҡ
вҖңдҪ жқҘдәҶгҖӮвҖқ
дёҚжҳҜз–‘й—®пјҢд№ҹдёҚжҳҜж„ҹеҸ№пјҢе°ұжҳҜдёҖеҸҘе№іе№іеёёеёёзҡ„иҜқпјҢеғҸзӯүдәҶи®ёд№…зҡ„дәәз»ҲдәҺзңӢи§ҒзҶҹдәәиҝӣй—ЁгҖӮ
йҷҲзҺ„еӨңеј дәҶеј еҳҙпјҢжғіеӣһиҜқпјҢеҚҙеҸ‘зҺ°иҜҙдёҚеҮәеЈ°гҖӮдҪҶд»–еҝғйҮҢжғізҡ„пјҢдјјд№ҺеҘ№йғҪзҹҘйҒ“гҖӮ
д»–жғіиө·жқЁе…„иҜҙзҡ„йӮЈеҸҘиҜқпјҡвҖңеҘ№иҜҙпјҢе“ҘпјҢжҲ‘дёҚз–јпјҢеҲ«е“ӯгҖӮвҖқ
еҸҜеҘ№жҳҺжҳҺз–јеҫ—жҢҮз”ІйғҪжҠ иҝӣдәҶжҺҢеҝғгҖӮ
д»–иғёеҸЈеҸ‘зҙ§гҖӮ
еҘ№еңЁйҮҢйқўиҝҮдәҶеӨҡд№…пјҹеҚҒе…ӯеІҒиҝӣе®«пјҢеҲ°зҺ°еңЁвҖҰвҖҰеӨҡе°‘е№ҙпјҹдёҖдёӘдәәиў«еҗҠеңЁж°ҙеә•пјҢйӯӮдёҚеҫ—и„ұпјҢиҝһз—ӣйғҪдёҚж•ўе–ҠеҮәжқҘгҖӮ
еҸҜеҘ№иҝҳеңЁзӯүгҖӮ
дёҚжҳҜзӯүж•‘иөҺпјҢжҳҜзӯүдёҖдёӘж„ҝж„Ҹиө°иҝӣеҘ№дё–з•Ңзҡ„дәәгҖӮ
д»–еҝҪ然жҳҺзҷҪпјҢиҝҷдёҚжҳҜи°ҒжӢҜж•‘и°Ғзҡ„дәӢгҖӮ
д»–дёҚжҳҜжқҘжҠҠеҘ№жӢүеҮәеҺ»зҡ„иӢұйӣ„гҖӮ
д»–жҳҜжқҘйҷӘеҘ№дёҖиө·йҶ’зҡ„гҖӮ
зҺүдҪ©зҡ„е…ү慢慢收еӣһпјҢд»–зқҒзңјпјҢи„ёдёҠдёҚзҹҘд»Җд№Ҳж—¶еҖҷж№ҝдәҶгҖӮд»–жІЎж“ҰпјҢеҸӘжҳҜжҠ¬иө·жүӢпјҢеңЁз©әдёӯз”ЁиЎҖз”»дәҶдёҖйҒ“гҖӮ
дёҚжҳҜз¬ҰпјҢдёҚжҳҜе’’пјҢ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еӯ—пјҡ**еҗҢ**гҖӮ
еҗҢдёҖе‘ҪиҝҗпјҢеҗҢдёҖйҖүжӢ©пјҢеҗҢдёҖжқЎи·ҜгҖӮ
д»–з«ҷиө·иә«пјҢи…ҝиҝҳжңүзӮ№йә»пјҢдҪҶз«ҷеҫ—зӣҙгҖӮжҘјеӨ–йЈҺжӣҙеӨ§дәҶпјҢз“ҰзүҮе’”е’”дҪңе“ҚпјҢжңүеҮ еқ—е·Із»ҸжқҫеҠЁгҖӮ
д»–зҹҘйҒ“дёҚиғҪеҶҚз•ҷгҖӮ
иҪ¬иә«ж—¶пјҢзҺүдҪ©еҝҪ然еҸҲйңҮдәҶдёҖдёӢгҖӮиҝҷж¬ЎдёҚжҳҜзғӯпјҢжҳҜеҶ·пјҢеғҸжҳҜеҶ°иҙҙеңЁзҡ®иӮүдёҠгҖӮд»–жӢҝеҮәжқҘдёҖзңӢпјҢиЎЁйқўжө®зҺ°еҮәдёҖж®өеҪұеғҸпјҡйӣӘеұұпјҢдә‘йӣҫпјҢдёҖйҒ“зҹій—ЁеҚҠеҹӢеңЁеІ©еЈҒйҮҢпјҢй—ЁдёҠеҲ»зқҖдёҚи®ӨиҜҶзҡ„еӯ—гҖӮ
д»–зӣҜзқҖзңӢдәҶеҮ з§’пјҢжҳҺзҷҪдәҶгҖӮ
жҳҶд»‘гҖӮ
еҺҹжқҘи·ҜдёҚеңЁй•ҝе®үпјҢд№ҹдёҚеңЁеҚҺжё…жұ гҖӮ
иҖҢеңЁжҳҶд»‘еўҹгҖӮ
д»–жҠҠзҺүдҪ©ж”¶еӣһжҖҖдёӯпјҢжңҖеҗҺзңӢдәҶдёҖзңјиҘҝеҚ—ж–№еҗ‘гҖӮйӮЈйҮҢдҫқж—§е®үйқҷпјҢж°ҙйқўж— жіўпјҢд»ҝдҪӣеҲҡжүҚзҡ„дёҖеҲҮйғҪжІЎеҸ‘з”ҹгҖӮ
еҸҜд»–зҹҘйҒ“пјҢеҘ№еҗ¬и§ҒдәҶгҖӮ
д»–иө°дёӢжҘјжўҜпјҢи„ҡжӯҘжҜ”дёҠжқҘж—¶еҝ«гҖӮжңЁжўҜеҗұе‘Җе“ҚпјҢиө°еҲ°з¬¬дёүеұӮж—¶пјҢеҗ¬и§ҒеҹҺеўҷдёҠжңүдәәиҜҙиҜқгҖӮ
вҖңеҲҡжүҚжңұйӣҖжҘјжҳҜдёҚжҳҜдә®дәҶдёҖдёӢпјҹвҖқ
вҖңдҪ зңӢй”ҷдәҶпјҢйЈҺеӨ§пјҢзҒҜз¬јжҷғзҡ„еҪұеӯҗгҖӮвҖқ
вҖңеҸҜжҲ‘жҖҺд№Ҳи§үеҫ—вҖҰвҖҰжңүзӮ№еҶ·пјҹвҖқ
йҷҲзҺ„еӨңиҙҙзқҖеўҷи§’и№ІдёӢпјҢзӯүдёӨдәәиө°иҝҮгҖӮ他们з©ҝзқҖеӨ©жһўйҷўзҡ„жҡ—иўҚпјҢи…°й—ҙжҢӮз¬ҰеҲҖпјҢиө°еҫ—дёҚжҖҘпјҢдҪҶе·ЎжҹҘеҫ—еҫҲз»ҶгҖӮ
зӯүи„ҡжӯҘиҝңдәҶпјҢд»–жүҚ继з»ӯеҫҖдёӢгҖӮ
еә•еұӮеҮәеҸЈиў«дёҖе ҶжқӮзү©е өзқҖпјҢд»–з”ЁжүӢжү’ејҖдёҖжқЎзјқпјҢй’»еҮәеҺ»пјҢйЎәжүӢжҠҠжҹҙе ҶжҺЁеӣһеҺҹдҪҚгҖӮ
еӨ–йқўе··еӯҗзӘ„пјҢдёӨиҫ№еўҷй«ҳпјҢжңҲе…үз…§дёҚиҝӣжқҘгҖӮд»–йқ зқҖеўҷиө°пјҢжүӢдёҖзӣҙжҢүеңЁеҢ•йҰ–жҹ„дёҠгҖӮиҷҪ然еҲҖиҝҳжІЎеҮәиҝҮйһҳпјҢдҪҶд»–зҹҘйҒ“пјҢжҺҘдёӢжқҘдёҚдјҡеҶҚжңүе®үзЁізҡ„еӨңгҖӮ
жӢҗеҮә第дёүжқЎеІ”йҒ“ж—¶пјҢд»–еҒңдёӢгҖӮ
еүҚж–№и·ҜеҸЈз«ҷзқҖдёҖдёӘдәәеҪұгҖӮ
иғҢеҜ№зқҖд»–пјҢжҠ«зқҖзҒ°еёғж–—зҜ·пјҢжүӢйҮҢжӢҺзқҖдёӘз«№зҜ®гҖӮ
йҷҲзҺ„еӨңжІЎеҠЁгҖӮ
йӮЈдәәд№ҹжІЎеӣһеӨҙгҖӮ
е°ұиҝҷд№ҲеғөдәҶеҮ жҒҜгҖӮ
然еҗҺпјҢеҜ№ж–№еҝҪ然еҫҖж—Ғиҫ№и®©дәҶдёҖжӯҘпјҢз©әеҮәйҖҡи·ҜгҖӮ
йҷҲзҺ„еӨңзңӢдәҶд»–дёҖзңјпјҢиҝҲжӯҘиө°иҝҮгҖӮ
дёӨдәәиӮ©иҶҖй”ҷејҖзҡ„зһ¬й—ҙпјҢйӮЈдәәдҪҺеЈ°иҜҙпјҡ
вҖңжў…иҠұејҖдәҶгҖӮвҖқ
йҷҲзҺ„еӨңи„ҡжӯҘдёҖйЎҝгҖӮ
жІЎеӣһеӨҙпјҢеҸӘеә”дәҶдёҖеЈ°пјҡвҖңе—ҜгҖӮвҖқ
然еҗҺ继з»ӯеҫҖеүҚгҖӮ
иә«еҗҺйӮЈдәәйқҷйқҷз«ҷзқҖпјҢзӣҙеҲ°д»–зҡ„иғҢеҪұж¶ҲеӨұеңЁе··е°ҫпјҢжүҚзј“зј“жҠ¬еӨҙгҖӮ
еӨ©дёҠж®ӢжңҲеҰӮй’©пјҢз…§еңЁд»–ж–—зҜ·иҫ№зјҳпјҢйңІеҮәдёҖи§’з»ЈзқҖжў…жһқзҡ„иЎЈйўҶгҖӮ
д»–жҸҗзқҖзҜ®еӯҗпјҢиҪ¬иә«иө°еҗ‘еҸҰдёҖжқЎиЎ—гҖӮ
зҜ®еӯҗйҮҢпјҢдёҖзӣҶзҷҪжў…жӯЈејҖзқҖ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ө¶е°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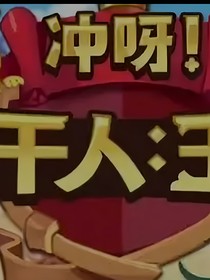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йҘје№ІдәӢи®°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еңЁејӮз•Ңзә№д№қйҫҷжӢүжЈә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Ҫ’е°ҳеҲӣдё–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家з”өи§ҶжңәиғҪз©ҝи¶ҠдёҮз•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