дә‘ж –жёЎпјҢзӢҗзҒ«з…§еҪ’дәә(з»ӯ)
дә‘ж –жёЎпјҢзӢҗзҒ«з…§еҪ’дәәпјҲз»ӯпјү
еұұеқізҡ„йӣҫжҳҜд»ҺзҷҪйңІйӮЈеӨ©еҗҺпјҢдёҖж—Ҙжө“иҝҮдёҖж—Ҙзҡ„гҖӮйҳҝжёЎи№ІеңЁжәӘиҫ№жҙ—иҚҜзҜ“ж—¶пјҢжҢҮе°–еҲҡзў°зқҖжөёзқҖеҮүж„Ҹзҡ„жәӘж°ҙпјҢж°ҙйқўе°ұжө®иө·з»ҶзўҺзҡ„еҶ°зўҙвҖ”вҖ”е…Ҙз§Ӣзҡ„жәӘж°ҙжё©йҷҚеҫ—еҝ«пјҢе”ҜжңүеҘ№иӮ©еӨҙйӮЈеӣўзӢҗзҒ«иҪ»иҪ»жҷғдәҶжҷғпјҢж©ҳзәўжҡ–е…үиЈ№дҪҸеҘ№зҡ„жүӢи…•пјҢеҶ°зўҙзһ¬й—ҙж¶ҲиһҚпјҢиҝһжәӘж°ҙйғҪжіӣиө·жө…жө…зҡ„жҡ–ж„ҸгҖӮиҝҷжҳҜеҘ№дҝ®дәҶзҷҫе№ҙзҡ„зҒөзҒ«пјҢйҖҡдҪ“жҫ„жҫҲпјҢйҷӨдәҶй©ұеҜ’пјҢжңҖиҰҒзҙ§зҡ„з”ЁеӨ„жҳҜвҖңи®Өи·ҜвҖқпјҢе“ӘжҖ•дјёжүӢдёҚи§Ғдә”жҢҮзҡ„жө“йӣҫпјҢд№ҹиғҪиў«е®ғзғ«еҮәжё…жҷ°зҡ„е…үи·ҜгҖӮ
иҚҜзҜ“йҮҢзҡ„еҮқйңІиҚүжІҫзқҖж°ҙжұҪпјҢжҳҜиҖҒж§җжёЎеұұж°‘жҚўзіҷзұізҡ„зү©д»¶гҖӮеҫҖеёёиҝҷдёӘж—¶иҫ°пјҢеұұи·ҜдёҠж—©иҜҘжңүжҢ‘жӢ…дәәзҡ„еҗҶе–қпјҢеҸҜд»Ҡж—ҘйӣҫйҮҢйқҷеҫ—еҸҚеёёпјҢиҝһйЈҺйғҪиЈ№зқҖж№ҝеҶ·зҡ„й»Ҹж„ҸгҖӮйҳҝжёЎеҲҡжӢҗиҝҮ第дёүдёӘеұұејҜпјҢзӢҗзҒ«еҝҪ然вҖңе—ЎвҖқең°з»·зҙ§е…үиҶңпјҢжҡ–е…үеҲәеҫ—йӣҫеұӮвҖңж»Ӣж»ӢвҖқжіӣзҷҪвҖ”вҖ”иҝҷжҳҜз”ҹдәәй—Ҝе…Ҙеұұеқізҡ„еҫҒе…ҶгҖӮ
еҘ№и№Іиә«и—Ҹиҝӣи•ЁиҚүеҗҺпјҢйӣҫйҮҢи·Ңж’һеҮәдёӘз©ҝзІ—еёғзҹӯжү“зҡ„е°‘е№ҙгҖӮеҚҒдёғе…«еІҒзҡ„е№ҙзәӘпјҢиғҢзқҖз ҙеёғеҢ…иўұпјҢиЈӨи„ҡеҚ·еҲ°иҶқзӣ–пјҢи…ҝиӮҡеӯҗеҲ’дәҶйҒ“иЎҖеҸЈеӯҗпјҢжӯЈдёҖзҳёдёҖжӢҗең°еҫҖжәӘиҫ№иө°гҖӮе°‘е№ҙжҢҮе°–еҲҡзў°зқҖж°ҙйқўзҡ„еҶ°зўҙпјҢе°ұз–јеҫ—еҳ¶дәҶеЈ°пјҢжҠ¬зңјж—¶пјҢз«ҹзӣҙеӢҫеӢҫзңӢеҗ‘йҳҝжёЎиӮ©еӨҙвҖ”вҖ”д»–зңјеә•и’ҷзқҖеұӮжө…зҒ°пјҢжҳҜеӨ©з”ҹзҡ„еҚҠзӣІпјҢеҚҙеҒҸиғҪеҫӘзқҖзӢҗзҒ«зҡ„жҡ–е…үиҫЁзү©гҖӮ
вҖңдҪ вҖҰвҖҰдҪ иҝҷе„ҝжңүвҖҳе…үвҖҷеҗ—пјҹвҖқе°‘е№ҙеЈ°йҹіеҸ‘йўӨпјҢвҖңжҲ‘д»ҺеұұеӨ–йҖғжқҘеҜ»йҳҝе§җпјҢйӣҫеӨӘеӨ§пјҢи…ҝвҖҰвҖҰвҖқд»–ж‘ёзҙўзқҖд»ҺеҢ…иўұйҮҢж‘ёеҮәеҚҠеқ—е№ІйҘјйҖ’иҝҮжқҘпјҢвҖңеҸӘжңүиҝҷдёӘпјҢиғҪжҚўдҪ иҝҷе…үпјҢз…§жҲ‘еҺ»иҖҒж§җжёЎеҗ—пјҹвҖқ
йҳҝжёЎзҡ„еЈ°йҹіеғҸеұұ涧еҶ°жіүпјҢжё…еҶ·еҶ·зҡ„пјҡвҖңиҖҒж§җжёЎд»Ҡж—ҘиәІйӣҫй¬јеҺ»дәҶгҖӮвҖқйӣҫй¬јжҳҜз§ӢйӣҫйҮҢзҡ„йӮӘзҘҹпјҢдё“зј иҝ·и·Ҝз”ҹдәәеҗёжҙ»дәәж°”пјҢе°‘е№ҙзҡ„и„ёвҖңе”°вҖқең°зҷҪдәҶпјҢж”Ҙзҙ§еҢ…иўұзҡ„жүӢйғҪеңЁжҠ–пјҡвҖңжҲ‘йҳҝе§җдёүе№ҙеүҚиҝӣеұұйҮҮиҸҮжІЎеӣһеҺ»пјҢеҢ…иўұйҮҢжңүеҘ№зҡ„银з°ӘвҖҰвҖҰвҖқ
йҳҝжёЎеһӮзңјпјҢзңӢи§ҒеҢ…иўұи§’йңІеҮәзҡ„银з°ӘвҖ”вҖ”з°ӘеӨҙеҲ»зқҖвҖңжёЎвҖқеӯ—пјҢжҳҜеҘ№еҺ»е№ҙеңЁжәӘеә•жҚЎзҡ„пјҢд№ҹжҳҜеҘ№з»ҷиҮӘе·ұеҸ–еҗҚеӯ—зҡ„з”ұжқҘгҖӮеҘ№жҢҮе°–зў°дәҶзў°зӢҗзҒ«пјҢжҡ–е…үеңЁйӣҫйҮҢзғ«еҮәжқЎз»Ҷе…үи·ҜпјҡвҖңи·ҹжҲ‘иө°пјҢдә‘ж –жёЎиғҪиәІйӣҫй¬јгҖӮвҖқ
дә‘ж –жёЎеңЁеұұеқіжңҖж·ұеӨ„пјҢжҳҜй—ҙйқ’зҹіжқҝз Ңзҡ„е°ҸеұӢпјҢеўҷж №е ҶзқҖеұұж°‘йҒ—иҗҪзҡ„ж—§зү©пјҢзҒ¶еҸ°дёҠж‘ҶзқҖеҚҠзҪҗзіҷзұігҖӮйҳҝжёЎжҠҠйҷ¶еЈ¶жһ¶еңЁзӢҗзҒ«дёҠзғ§зғӯж°ҙпјҢе°‘е№ҙеқҗеңЁй—Ёж§ӣдёҠпјҢиҜҙиҮӘе·ұеҸ«йҳҝж§җпјҢйҳҝе§җеҗҚе”ӨйҳҝжәӘпјҢдёүе№ҙеүҚдёәжҚўд»–зҡ„зңјиҚҜиҝӣеұұпјҢеҸӘз•ҷдёӢйӮЈж”Ҝ银з°ӘгҖӮйҳҝжёЎеҫҖй”…йҮҢж’’дәҶжҠҠеҮқйңІиҚүпјҢзғӯж°ҙжј«еҮәжё…иӢҰзҡ„йҰҷпјҡвҖңдҪ йҳҝе§җжҳҜж•‘жҲ‘ж—¶иў«йӣҫй¬јзј зҡ„гҖӮвҖқ
зҷҫе№ҙеүҚйҳҝжёЎеҲҡејҖзҒөжҷәпјҢиў«еұұеӨ–йҒ“еЈ«иҝҪжү“пјҢжҳҜйҳҝжәӘзҡ„йҳҝеЁҳи—ҸеҘ№еңЁдә‘ж –жёЎпјӣдёүе№ҙеүҚйҳҝжёЎеңЁйӣҫйҮҢиҝ·и·ҜпјҢжҳҜйҳҝжәӘеј•еҘ№еҫҖжәӘиҫ№иө°пјҢиҮӘе·ұеҚҙиў«йӣҫй¬јжӢ–иҝӣдәҶйӣҫеӣўгҖӮйҳҝж§җзҡ„зңјжіӘз ёеңЁиЈӨи…ҝдёҠпјҢд»–ж‘ёеҮә银з°ӘйҖ’иҝҮеҺ»пјҡвҖңйҳҝ渡姑еЁҳпјҢдҪ иғҪж•‘ж•‘йҳҝе§җеҗ—пјҹжҲ‘е°ұиҝҷдёҖдёӘдәІдәәдәҶгҖӮвҖқ
зӢҗзҒ«еҝҪ然йЈҳеҲ°й“¶з°ӘдёҠпјҢжҡ–е…үиЈ№зқҖз°Әиә«жіӣеҮәжө…зҷҪгҖӮйҳҝжёЎжҢҮе°–зў°дәҶзў°е…үиҶңпјҡвҖңйӣҫй¬јиЈ№зқҖеҘ№зҡ„ж®ӢйӯӮпјҢиҰҒеј•йӯӮеҫ—иҖ—зҷҫе№ҙзҒөеҠӣвҖ”вҖ”жҲ‘зҡ„зӢҗзҒ«дјҡж•ЈгҖӮвҖқйҳҝж§җзҢӣең°и·ӘдёӢжқҘпјҢиҶқзӣ–з ёеңЁзҹіжқҝдёҠй—·е“ҚпјҡвҖңжҲ‘з»ҷдҪ еҪ“зүӣеҒҡ马пјҢйҮҮиҚүиҚҜгҖҒеҠҲжҹҙпјҢд»Җд№ҲйғҪе№ІпјҒвҖқ
йҳҝжёЎеһӮзңјзӣҜзқҖд»–жіӣзәўзҡ„зңјзң¶пјҢйӮЈйҮҢйқўзҡ„е…үеғҸеұұеқійҮҢзҪ•и§Ғзҡ„ж—Ҙе…үгҖӮеҘ№зӮ№дәҶзӮ№еӨҙпјҡвҖңеӨңйҮҢйӣҫжңҖжө“ж—¶еј•йӯӮпјҢдҪ еҺ»йҮҮдёүж ӘзҒјеҝғиҚүпјҢй•ҝеңЁеҙ–иҫ№зҹізјқйҮҢпјҢиҢҺжҳҜзәўзҡ„гҖӮвҖқ
йҳҝж§җж‘ёй»‘еҫҖеҙ–иҫ№еҺ»ж—¶пјҢйӣҫе·Із»ҸжІүеҫ—иғҪж”ҘеҮәж°ҙгҖӮзӢҗзҒ«еҲҶдәҶзј•жҡ–е…үзј еңЁд»–жүӢи…•пјҢзғ«еҫ—йӣҫеұӮеҫҖдёӨиҫ№йҖҖгҖӮд»–еҲҡж‘ёеҲ°з¬¬дёҖж ӘзҒјеҝғиҚүпјҢеҝҪ然еҗ¬и§ҒйӣҫйҮҢдј жқҘвҖңе‘ңе‘ңвҖқзҡ„е“ӯи…”пјҢеғҸйҳҝе§җе°Ҹж—¶еҖҷе“„д»–зҡ„еЈ°йҹігҖӮйҳҝж§җж”Ҙзҙ§й“¶з°ӘеҫҖеүҚиө°пјҢйӣҫйҮҢжҷғеҮәеӣўзҒ°еҪұпјҢз©ҝзқҖйҳҝжәӘзҡ„зІ—еёғиЎ«пјҢеӨҙеҸ‘жҠ«ж•ЈзқҖпјҢзңјзӘқжҳҜз©әзҡ„й»‘зіҠзіҠйӣҫж°”гҖӮ
вҖңйҳҝе§җпјҒвҖқд»–еҫҖеүҚжү‘пјҢзҒ°еҪұеҚҙеј ејҖе°–зүҷеҫҖд»–иә«дёҠжү‘гҖӮзӢҗзҒ«зҡ„жҡ–е…үвҖңе—ЎвҖқең°зӮёејҖпјҢиЈ№жҲҗе…үзҗғж’һеңЁзҒ°еҪұиә«дёҠпјҢзҒ°еҪұе°–еҸ«зқҖзј©еӣһеҺ»пјҢи№ІеңЁе…үиҫ№е“ӯпјҢеЈ°йҹійҮҢе…ЁжҳҜ委еұҲгҖӮйҳҝж§җиҝҷжүҚзңӢжё…пјҢзҒ°еҪұзҡ„жүӢи…•дёҠжҲҙзқҖд»–ж”’й’ұжү“зҡ„银й•ҜпјҢеҲ»зқҖвҖңж§җвҖқеӯ—гҖӮ
д»–и№ІдёӢжқҘпјҢеЈ°йҹіеҸ‘йўӨпјҡвҖңйҳҝе§җпјҢжҲ‘жҳҜйҳҝж§җпјҢжқҘжҺҘдҪ еӣһ家дәҶгҖӮвҖқзҒ°еҪұйЎҝдәҶйЎҝпјҢж…ўж…ўеҫҖе…үйҮҢжҢӘпјҢжҡ–е…үиЈ№дҪҸе®ғж—¶пјҢзҒ°йӣҫж·ЎдәҶдәӣпјҢйңІеҮәйҳҝжәӘзҡ„еҚҠеј и„ёвҖ”вҖ”е’Ңд»–и®°еҝҶйҮҢдёҖж ·пјҢеҳҙи§’жңүйў—е°Ҹз—ЈгҖӮ
зӯүйҳҝж§җжҚ§зқҖдёүж ӘзҒјеҝғиҚүеӣһжқҘпјҢйҳҝжёЎе·Із»ҸеңЁзҒ¶еҸ°дёҠж‘ҶдәҶйҷ¶зў—пјҢзў—йҮҢзӣӣзқҖиһҚдәҶеҮқйңІиҚүзҡ„зғӯж°ҙгҖӮзӢҗзҒ«жӮ¬еңЁзў—дёҠж–№пјҢжҡ–е…үйЎәзқҖж°ҙйқўеҫҖдёӢжІүпјҢйҳҝжёЎжҠҠ银з°Әж”ҫиҝӣзў—йҮҢпјҢзҒјеҝғиҚүзҡ„зәўиҢҺеңЁж°ҙйҮҢж…ўж…ўеҢ–ејҖпјҢж°ҙиүІеҸҳжҲҗжө…зәўгҖӮ
вҖңеҘ№зҡ„ж®ӢйӯӮеӣ°еңЁйӣҫйҮҢдёүе№ҙпјҢжү§еҝөеӨӘйҮҚпјҢеҫ—з”ЁдҪ зҡ„иЎҖиһҚйӯӮгҖӮвҖқйҳҝжёЎйҖ’иҝҮзүҮзўҺз“·зүҮпјҢвҖңж»ҙдёүж»ҙеңЁзў—йҮҢгҖӮвҖқйҳҝж§җжІЎзҠ№иұ«пјҢеүІз ҙжҢҮе°–еҫҖзў—йҮҢж»ҙпјҢиЎҖзҸ иҗҪеңЁж°ҙйҮҢпјҢзһ¬й—ҙе’Ңжө…зәўиһҚеңЁдёҖиө·пјҢзў—йҮҢеҶ’еҮәзј•зҷҪж°”пјҢиЈ№зқҖйҳҝжәӘзҡ„еЈ°йҹіпјҡвҖңйҳҝж§җпјҢеҲ«йқ иҝ‘йӣҫвҖҰвҖҰвҖқ
зӢҗзҒ«зҢӣең°зӮёејҖжҡ–е…үпјҢиЈ№зқҖзҷҪж°”еҫҖйӣҫйҮҢеҺ»гҖӮйҳҝжёЎзҡ„и„ёзҷҪдәҶдәӣпјҢжҢҮе°–еңЁе…үиҶңдёҠеҲ’дәҶйҒ“еҚ°еӯҗвҖ”вҖ”зҷҫе№ҙзҒөеҠӣжӯЈйЎәзқҖе…үеҫҖж®ӢйӯӮйҮҢж·ҢгҖӮзҒ°еҪұеңЁе…үйҮҢж…ўж…ўеҸҳжё…жҷ°пјҢйҳҝжәӘзҡ„и„ёйңІеҮәжқҘпјҢеҘ№ж‘ёдәҶж‘ёйҳҝж§җзҡ„еӨҙпјҢжҢҮе°–жҳҜеҮүзҡ„пјҡвҖңйҳҝжёЎжҳҜеҘҪ姑еЁҳпјҢдҪ иҰҒеҘҪеҘҪеҫ…еҘ№гҖӮвҖқ
иҜқйҹіиҗҪж—¶пјҢзҒ°еҪұеҢ–дҪңйӣҫзө®ж•ЈдәҶпјҢеұұеқізҡ„йӣҫеҝҪ然еҫҖдёӨиҫ№йҖҖпјҢйңІеҮәеўЁи“қзҡ„еӨ©пјҢжҳҹжҳҹдә®еҫ—еғҸзўҺеңЁеӨ©дёҠзҡ„е…үгҖӮйҳҝжёЎзҡ„зӢҗзҒ«зј©жҲҗеӣўпјҢе…үиҶңжіӣзқҖжө…зҒ°вҖ”вҖ”зҷҫе№ҙзҒөеҠӣиҖ—еҫ—еҸӘеү©дёүжҲҗпјҢеҘ№еҫҖеҗҺиёүи·„дәҶжӯҘпјҢиў«йҳҝж§җжү¶дҪҸгҖӮ
вҖңдҪ жҖҺд№Ҳж ·пјҹвҖқйҳҝж§җзҡ„еЈ°йҹіеҸ‘зҙ§гҖӮйҳҝжёЎйқ еңЁд»–иӮ©дёҠпјҢзӢҗзҒ«и№ӯдәҶи№ӯеҘ№зҡ„и„ёйўҠпјҡвҖңжІЎдәӢпјҢзӢҗзҒ«дјҡж…ўж…ўе…»еӣһжқҘгҖӮвҖқ
еҫҖеҗҺзҡ„ж—ҘеӯҗпјҢйҳҝж§җжІЎиө°гҖӮд»–еңЁдә‘ж –жёЎж—ҒжҗӯдәҶй—ҙиҚүеұӢпјҢжҜҸж—ҘеӨ©дёҚдә®е°ұеҫҖеҙ–иҫ№еҺ»вҖ”вҖ”зҒјеҝғиҚүиғҪиЎҘзӢҗзҒ«зҡ„зҒөеҠӣпјҢеҙ–иҫ№зҡ„зҹізјқиў«д»–ж‘ёйҒҚдәҶпјҢжҢҮе°–зЈЁеҮәзҡ„иҢ§еӯҗдёҖеұӮеҸ дёҖеұӮгҖӮжңүж—¶йӣҫеӨӘеӨ§пјҢд»–е°ұеҫӘзқҖзӢҗзҒ«еҲҶжқҘзҡ„жҡ–е…үиө°пјҢиҚүеҸ¶еҲ’еңЁи„ёдёҠпјҢз–јеҫ—д»–йҫҮзүҷпјҢеҚҙиҝҳжҳҜж”ҘзқҖиҚҜзҜ“дёҚиӮҜеҒңгҖӮ
йҳҝжёЎзҡ„зӢҗзҒ«ж…ўж…ўжҒўеӨҚжҡ–е…үпјҢеҸӘжҳҜеҒ¶е°”дјҡеңЁеӨңйҮҢпјҢйЎәзқҖ银з°Әзғ«еҮәйҳҝжәӘзҡ„еҪұеӯҗгҖӮеҪұеӯҗеқҗеңЁй—Ёж§ӣдёҠпјҢеҳҙи§’зҡ„з—ЈеғҸйў—е°ҸжҳҹпјҢеҘ№зңӢзқҖйҳҝж§җз»ҷйҳҝжёЎеҠҲжҹҙпјҢзңӢзқҖйҳҝжёЎжҠҠжҡ–еҘҪзҡ„зіҷзұізІҘз«Ҝз»ҷйҳҝж§җпјҢиҪ»иҪ»з¬‘еҮәеЈ°пјҢеғҸе°Ҹж—¶еҖҷйӮЈж ·гҖӮ
е…Ҙз§ӢеҗҺзҡ„第дёғеңәйӣҫжқҘдёҙж—¶пјҢйҳҝж§җйҮҮеӣһдәҶдёҖеӨ§жҚҶзҒјеҝғиҚүгҖӮйҳҝжёЎжҠҠиҚүиҢҺжҷ’е№ІпјҢзЈЁжҲҗзІүж··еңЁеҮқйңІиҚүйҮҢпјҢзӢҗзҒ«зҡ„жҡ–е…үз»ҲдәҺжҒўеӨҚдәҶеҫҖж—Ҙзҡ„ж©ҳзәўпјҢиғҪзғ«ејҖеҚҠйҮҢең°зҡ„йӣҫгҖӮеұұ民们еҸҲејҖе§ӢеҫҖдә‘ж –жёЎжқҘпјҢжңүдәәжҚўиҚүиҚҜпјҢйҳҝж§җе°ұеё®зқҖз§°ж–ӨдёӨпјӣжңүдәәиҝ·и·ҜпјҢзӢҗзҒ«е°ұеҲҶзј•жҡ–е…ү引他们еҮәеҺ»гҖӮиҖҒж§җжёЎзҡ„зіҷзұіе ҶеңЁзҒ¶еҸ°дёӢпјҢзҪҗеӯҗйҮҢзҡ„еҮқйңІиҚүжҖ»ж»ЎзқҖпјҢиҚүеҸ¶дёҠзҡ„йңІзҸ еӯҗпјҢжҖ»жІҫзқҖзӢҗзҒ«зҡ„жҡ–е…үгҖӮ
жңүж¬Ўеұұж°‘еёҰжқҘеқ—зі–пјҢйҳҝж§җеҒ·еҒ·и—Ҹиө·жқҘпјҢеӨңйҮҢеүҘдәҶзі–зәёеЎһз»ҷйҳҝжёЎгҖӮзі–еқ—еңЁеҘ№иҲҢе°–еҢ–ејҖпјҢз”ңеҫ—еҘ№зңјзқӣејҜиө·жқҘпјҢзӢҗзҒ«жҷғдәҶжҷғпјҢжҡ–е…үиЈ№дҪҸдёӨдёӘдәәзҡ„еҪұеӯҗпјҢжҠ•еңЁеўҷдёҠеғҸеӣўиҪҜд№Һд№Һзҡ„дә‘гҖӮйҳҝж§җж‘ёзқҖеҘ№зҡ„еҸ‘йЎ¶пјҢеЈ°йҹіеҫҲиҪ»пјҡвҖңйҳҝжёЎпјҢд»ҘеҗҺжҲ‘з»ҷдҪ йҮҮдёҖиҫҲеӯҗзҒјеҝғиҚүгҖӮвҖқ
йҳҝжёЎзҡ„жҢҮе°–зў°дәҶзў°д»–зҡ„зңјзқӣпјҢйӮЈйҮҢзҡ„жө…зҒ°йҮҢзӣӣзқҖжҡ–е…үпјҡвҖңжҳҺе№ҙжҳҘеӨ©пјҢзӢҗзҒ«иғҪи®Өи·ҜеҺ»еұұеӨ–пјҢеёҰдҪ жІ»зңјзқӣгҖӮвҖқ
йҳҝж§җ笑зқҖж‘ҮеӨҙпјҢжҠҠеҘ№зҡ„жүӢжҢүеңЁиҮӘе·ұеҝғеҸЈпјҡвҖңдёҚз”ЁжІ»пјҢжңүдҪ е’ҢзӢҗзҒ«пјҢжҲ‘еңЁе“Әе„ҝйғҪиғҪзңӢи§Ғи·ҜгҖӮвҖқ
зӘ—еӨ–зҡ„йӣҫеҸҲжІүдёӢжқҘпјҢзӢҗзҒ«зҡ„жҡ–е…үйЎәзқҖзӘ—жЈӮж·ҢеҮәеҺ»пјҢзғ«ејҖжқЎз»Ҷе…үи·ҜпјҢи·Ҝзҡ„е°ҪеӨҙжҳҜеўЁи“қзҡ„еӨ©пјҢжҳҹжҳҹдә®еҫ—жё©жҹ”гҖӮдә‘ж –жёЎзҡ„еұӢйҮҢпјҢзіҷзұізІҘзҡ„йҰҷиЈ№зқҖзі–е‘іпјҢзҒ¶иҶӣйҮҢзҡ„жҡ–е…үиЈ№зқҖдёӨдёӘдәәзҡ„е‘јеҗёпјҢеғҸеұұеқійҮҢзҡ„еІҒжңҲпјҢе®үе®үзЁізЁізҡ„пјҢиҝһйӣҫйғҪеҸҳеҫ—иҪҜе’Ңиө·жқҘгҖӮ
еҗҺжқҘеұұ民们иҜҙпјҢдә‘ж –жёЎзҡ„жҡ–е…үж°ёиҝңдёҚдјҡж•ЈвҖ”вҖ”йӮЈе…үйҮҢжңүзҒөзӢҗзҡ„зҷҫе№ҙжё©жҹ”пјҢжңүе°‘е№ҙзҡ„дёҖз”ҹжүҝиҜәпјҢиҝҳжңүйӣҫйҮҢеҪ’жқҘзҡ„жү§еҝөпјҢйғҪиЈ№еңЁж©ҳзәўзҡ„жҡ–йҮҢпјҢз…§зқҖеұұеқізҡ„и·ҜпјҢд№ҹз…§зқҖеҪ’дәәзҡ„家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ҝғйӯ”еү‘й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ҚҒе…«иӢұйӣ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јҖеұҖй“ёе°ұж— дёҠж №еҹәпјҢжҲ‘й—®йјҺд»ҷи·Ҝпј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Һе •д№қе№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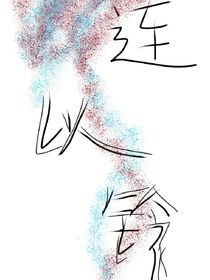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д»Ҙй“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