дә‘ж –жёЎпјҢзӢҗзҒ«з…§еҪ’дәә
дә‘ж –жёЎпјҢзӢҗзҒ«з…§еҪ’дәә
еұұеқійҮҢзҡ„йӣҫжҳҜд»ҺзҷҪйңІйӮЈеӨ©ејҖе§Ӣжө“зҡ„пјҢеғҸжҸүзўҺзҡ„жЈүзө®жөёдәҶеҮүж°ҙпјҢжІүз”ёз”ёең°еҺӢеңЁй»ӣиүІзҡ„еұұи„ҠдёҠгҖӮйҳҝжёЎи№ІеңЁжәӘиҫ№жҙ—иҚҜзҜ“ж—¶пјҢжҢҮе°–еҲҡзў°еҲ°жөёзқҖеҮүж„Ҹзҡ„жәӘж°ҙпјҢж°ҙйқўе°ұжө®иө·дёҖеұӮз»ҶзўҺзҡ„еҶ°зўҙвҖ”вҖ”е…Ҙз§Ӣзҡ„жәӘж°ҙжё©йҷҚеҫ—еҝ«пјҢе”ҜжңүеҘ№иӮ©еӨҙйӮЈеӣўзӢҗзҒ«иҪ»иҪ»жҷғдәҶжҷғпјҢж©ҳзәўиүІзҡ„жҡ–е…үиЈ№дҪҸеҘ№зҡ„жүӢи…•пјҢеҶ°зўҙзһ¬й—ҙж¶ҲиһҚпјҢиҝһеёҰзқҖжәӘж°ҙйғҪжіӣиө·жө…жө…зҡ„жҡ–ж„ҸгҖӮиҝҷжҳҜеҘ№дҝ®дәҶзҷҫе№ҙзҡ„зҒөзҒ«пјҢйҖҡдҪ“жҫ„жҫҲж— жқӮиүІпјҢйҷӨдәҶй©ұеҜ’пјҢжңҖиҰҒзҙ§зҡ„з”ЁеӨ„жҳҜвҖңи®Өи·ҜвҖқпјҢе“ӘжҖ•жҳҜдјёжүӢдёҚи§Ғдә”жҢҮзҡ„жө“йӣҫпјҢд№ҹиғҪиў«е®ғзғ«еҮәдёҖйҒ“жё…жҷ°зҡ„е…үи·ҜгҖӮ
дёүе№ҙеүҚеқ еҙ–зҡ„йӮЈдёӘй»„жҳҸпјҢеҘ№жҳҜеңЁеҙ–йЎ¶зҡ„жЎғж ‘дёӢйҶ’иҝҮжқҘзҡ„гҖӮиә«дёҠзҡ„ж“ҰдјӨиў«з”Ёе№ІеҮҖзҡ„йә»еёғиЈ№еҫ—ж•ҙйҪҗпјҢдјӨеҸЈж•·зқҖжё…еҮүзҡ„иҚүиҚҜпјҢжһ•иҫ№еҺӢзқҖдёҖжһҡзј жһқиҺІжҡ–зҺүпјҢзҺүиә«йӣ•е·Ҙз»Ҷи…»пјҢзј жһқиҺІзҡ„зә№и·ҜйҮҢиҝҳж®Ӣз•ҷзқҖж·Ўж·Ўзҡ„жӘҖйҰҷгҖӮж—Ғиҫ№еҸ зқҖдёҖеј зҙ з¬әпјҢз¬әзәёиҫ№зјҳжІҫзқҖеҚҠзүҮе«Јзәўзҡ„жЎғиҠұз“ЈпјҢдёҠйқўжҳҜдёҖиЎҢжё…йҡҪзҡ„еӯ—иҝ№пјҡвҖңеҫ…дҪ зӢҗзҒ«иғҪиһҚеҶ¬жәӘеҶ°пјҢжқҘдә‘ж –жёЎеҜ»жҲ‘гҖӮвҖқ
йҳҝжёЎжҠҠжҡ–зҺүжҸЈиҝӣж–ңиҘҹзҡ„еёғе…ңйҮҢпјҢзҺүиә«иҙҙзқҖеҝғеҸЈпјҢжё©еҮүзҡ„и§Ұж„ҹзҶЁеё–зқҖиғёи…”йҮҢзҡ„иәҒеҠЁгҖӮеҘ№еҜ№зқҖжәӘж°ҙйҮҢзҡ„еҪұеӯҗзҗҶдәҶзҗҶ鬓иҫ№зҡ„зўҺеҸ‘пјҢ鬓角еҲ«зқҖдёҖжңөйЈҺе№Ізҡ„е°ҸйӣҸиҸҠпјҢжҳҜеҘ№д»Ҡж—©йҮҮиҚүиҚҜж—¶йЎәжүӢж‘ҳзҡ„гҖӮиҖҒиү„е…¬зҡ„з«№иҲ№е°ұжіҠеңЁдёӢжёёзҡ„ж»©ж¶Ӯиҫ№пјҢиҲ№иә«жҳҜж·ұиӨҗиүІзҡ„иҖҒжқүжңЁпјҢеёҰзқҖз»Ҹе№ҙзҙҜжңҲзҡ„ж°ҙжұҪе‘іпјҢиҲ№зҜ·дёҠжҢӮзқҖдёІе№ІиүҫиҚүпјҢеҸ¶зүҮе·Із»Ҹжҷ’еҫ—еҸ‘и„ҶпјҢйЈҺдёҖеҗ№пјҢзўҺе“ҚиЈ№зқҖиҚүжңЁйҰҷжј«иҝҮжқҘпјҢй©ұж•ЈдәҶйӣҫйҮҢзҡ„ж№ҝй—·гҖӮ
вҖң姑еЁҳжҳҜиҰҒеҫҖдә‘ж –жёЎеҺ»пјҹвҖқиҖҒиү„е…¬еҸјзқҖж—ұзғҹжқҶпјҢзғҹй”…йҮҢзҡ„зҒ«жҳҹжҳҺзҒӯпјҢзңји§’зҡ„зҡұзә№жҢӨжҲҗдәҶз»ҶеҜҶзҡ„жІҹеЈ‘пјҢеғҸжҳҜиў«еІҒжңҲеҲ»ж»ЎдәҶж•…дәӢгҖӮд»–еҫҖиҲ№иҫ№зҡ„ж°ҙйҮҢеҗҗдәҶеҸЈзғҹжёЈпјҢж°ҙйқўжіӣиө·дёҖеңҲж¶ҹжјӘпјҢвҖңйӮЈең°ж–№еҒҸеҫ—зҙ§пјҢдёүйқўзҺҜеұұпјҢдёҖйқўйқ ж°ҙпјҢйӣҫиЈ№дёүжңҲжүҚејҖдёҖж—ҘжҷҙпјҢи·ҜеҸҲйҡҫиө°пјҢ姑еЁҳеӯӨиә«дёҖдәәпјҢеҺ»еҒҡд»Җд№ҲпјҹвҖқ
вҖңеҜ»дёӘдәәгҖӮвҖқйҳҝжёЎиёҸдёҠиҲ№жқҝпјҢи„ҡжӯҘиҪ»зј“пјҢиҲ№жқҝеҸӘеҸ‘еҮәиҪ»еҫ®зҡ„вҖңеҗұе‘ҖвҖқеЈ°гҖӮзӢҗзҒ«зҡ„е…үиҗҪеңЁиҲ№иҲ·зҡ„йқ’иӢ”дёҠпјҢйқ’з»ҝиүІзҡ„иӢ”и—“иў«жҡ–е…үжҳ еҫ—еҸ‘дә®пјҢж№ҝж„Ҹж…ўж…ўи’ёеҸ‘пјҢз•ҷдёӢжө…жө…зҡ„зҷҪз—•пјҢвҖңд»–иҜҙеңЁйӮЈйҮҢзӯүжҲ‘гҖӮвҖқ
иҖҒиү„е…¬еҸ№еҸЈж°”пјҢз«№зҜҷеҫҖжіҘйҮҢдёҖж’‘пјҢеёҰзқҖйқ’иӢ”зҡ„з«№зҜҷжә…иө·еҮ ж»ҙжіҘж°ҙпјҢиҲ№е°ұйЎәзқҖж°ҙжөҒеҫҖйӣҫйҮҢжјӮгҖӮвҖңдә‘ж –жёЎзҡ„规зҹ©пјҢжҙ»дәәеҺ»еҫ—еёҰвҖҳеҝөжғізү©вҖҷгҖӮвҖқд»–зҡ„еЈ°йҹіиЈ№еңЁйӣҫйҮҢпјҢеғҸжөёдәҶж°ҙзҡ„жЈүзәҝпјҢй—·й—·зҡ„пјҢвҖңдҪ иҝҷзӢҗзҒ«жҳҜзҷҫе№ҙзҒөзү©пјҢз®—дёҖ件пјҢеү©дёӢзҡ„пјҢеҫ—з”Ёиҙҙиә«зҡ„дёңиҘҝжҠөпјҢдёҚ然йӣҫйҮҢзҡ„еј•и·Ҝй¬јдёҚи®ӨгҖӮвҖқ
йҳҝжёЎжІЎзҠ№иұ«пјҢжҠҠжҡ–зҺүд»Һеёғе…ңйҮҢжҺҸеҮәжқҘпјҢиҪ»иҪ»ж”ҫеңЁиҲ№жқҝзҡ„з«№еһ«дёҠгҖӮз«№еһ«жҳҜз”Ёж–°еҠҲзҡ„з«№зҜҫзј–зҡ„пјҢиҝҳеёҰзқҖж·Ўж·Ўзҡ„з«№йҰҷпјҢжҡ–зҺүж”ҫеңЁдёҠйқўпјҢжҠҳе°„еҮәз»ҶзўҺзҡ„е…үгҖӮиҲ№еҲҡе…ҘйӣҫпјҢйЈҺе°ұеҚ·зқҖж°ҙжұҪжү‘иҝҮжқҘпјҢеёҰзқҖеұұжһ—йҮҢи…җеҸ¶зҡ„ж°”жҒҜпјҢйҳҝжёЎиЈ№дәҶиЈ№иә«дёҠзҡ„зҙ иүІеёғиЎЈпјҢзӢҗзҒ«еҸҲдә®дәҶдәӣпјҢжҠҠеҘ№е‘Ёиә«зҡ„йӣҫйғҪйҖјйҖҖдәҶеҚҠе°әгҖӮвҖңйӮЈжёЎйҮҢзҡ„дәәпјҢйғҪжҳҜзӯүзқҖвҖҳи®ӨдәәвҖҷзҡ„гҖӮвҖқиҖҒиү„е…¬зҡ„зғҹжқҶеңЁиҲ№иҲ·дёҠзЈ•дәҶзЈ•пјҢзғҹзҒ°иҗҪеңЁж°ҙйҮҢпјҢзһ¬й—ҙж•ЈејҖпјҢвҖңжңүдәәзӯүдёүдә”е№ҙпјҢжңүдәәзӯүдёүдә”еҚҒе№ҙпјҢиҝҳжңүдәәзӯүдәҶдёҖиҫҲеӯҗпјҢеҲ°жңҖеҗҺйғҪжІЎзӯүжқҘгҖӮ姑еЁҳдҪ вҖҰвҖҰвҖқ
вҖңжҲ‘зӯүдәҶдёүе№ҙпјҢдҝ®дәҶзҷҫе№ҙпјҢеӨҹдәҶгҖӮвҖқйҳҝжёЎжҢҮе°–зў°дәҶзў°иӮ©еӨҙзҡ„зӢҗзҒ«пјҢжҡ–е…үйЎәзқҖжҢҮзјқжј«ејҖпјҢжҠҠйӣҫзғ«еҮәдәҶдёҖйҒ“жө…з—•пјҢз—•иҫ№зҡ„йӣҫзҸ еғҸзўҺй’»дёҖж ·пјҢжіӣзқҖжҷ¶иҺ№зҡ„е…үпјҢвҖңд»–иҜҙдјҡзӯүжҲ‘пјҢе°ұдёҖе®ҡеңЁгҖӮвҖқ
иҲ№иЎҢзәҰиҺ«еҚҠдёӘж—¶иҫ°пјҢйӣҫеҝҪ然иЈӮдәҶйҒ“зјқпјҢеғҸжҳҜиў«и°Ғз”ЁеүӘеҲҖеүӘејҖдәҶдёҖеқ—幕еёғгҖӮеүҚж–№зҡ„жёЎеҸЈжө®еңЁиҪҜз»өзҡ„е…үйҮҢпјҢй»‘зҹіз•Ңзў‘зҹ—з«ӢеңЁж°ҙиҫ№пјҢзў‘иә«зІ—зіҷпјҢеёҰзқҖеӨ©з„¶зҡ„зә№и·ҜпјҢвҖңдә‘ж –жёЎвҖқдёүдёӘеӯ—жҳҜз”ЁжқҫзғҹеҶҷзҡ„пјҢеўЁиүІж·ұжІүпјҢеӯ—зјқйҮҢй•ҝзқҖз»Ҷејұзҡ„е…°иҚүпјҢеҸ¶зүҮе«©з»ҝпјҢжІҫзқҖйӣҫзҸ пјҢеғҸжҳҜеҲҡиў«йӣЁж°ҙжҙ—иҝҮгҖӮзў‘дёӢзҡ„зҹійҳ¶й“әеҲ°ж°ҙиҫ№пјҢйқ’зҒ°иүІзҡ„зҹіеӨҙиў«еІҒжңҲе’ҢиЎҢдәәиё©зЈЁеҫ—жіӣзқҖжҹ”е…үпјҢзҹійҳ¶зјқйҡҷйҮҢй•ҝзқҖдәӣз»ҶзўҺзҡ„йқ’иӢ”пјҢж№ҝжјүжјүзҡ„пјҢйҖҸзқҖз”ҹжңәгҖӮ
вҖңеҲ°дәҶгҖӮвҖқиҖҒиү„е…¬жҠҠжҡ–зҺүйҖ’еӣһжқҘпјҢзғҹжқҶеҸҲеңЁиҲ№иҲ·дёҠзЈ•дәҶзЈ•пјҢвҖңиҝҮдәҶз•Ңзў‘еҲ«д№ұжҗӯиҜқпјҢжёЎйҮҢзҡ„дәәдёҚзҲұеҗ¬й—ІиЁҖпјҢеҸӘи®ӨвҖҳиҰҒзӯүзҡ„дәәвҖҷгҖӮж—ҘеӨҙиҗҪеұұеүҚеҫ—зҰ»жёЎпјҢдёҚ然йӣҫдјҡжҠҠи·Ҝе°Ғжӯ»гҖӮвҖқ
йҳҝжёЎиё©зқҖзҹійҳ¶дёҠеІёж—¶пјҢзӢҗзҒ«еҝҪ然дә®еҫ—жҷғзңјпјҢж©ҳзәўиүІзҡ„е…үжҳ еңЁй»‘зҹіз•Ңзў‘дёҠпјҢжҠҠе…°иҚүзҡ„еҪұеӯҗжӢүеҫ—еҫҲй•ҝгҖӮз•Ңзў‘еҗҺзҡ„е··еј„й“әзқҖйқ’зҹіжқҝпјҢзҹіжқҝиў«йӣЁж°ҙеҶІеҲ·еҫ—е№ІеҮҖпјҢзјқйҡҷйҮҢеҒ¶е°”иғҪзңӢи§ҒдёҖдёӨж ӘеҶ’еӨҙзҡ„йҮҺиҚүгҖӮдёӨдҫ§жҳҜзҹ®еўҷй»ӣз“Ұзҡ„йҷўеӯҗпјҢеўҷеӨҙдёҚй«ҳпјҢзҲ¬зқҖжҳҹжҳҹзӮ№зӮ№зҡ„зҙ«зүөзүӣпјҢиҠұз“ЈеёҰзқҖжҷЁйңІзҡ„ж№ҝж„ҸпјҢйЈҺдёҖеҗ№пјҢиҠұз“ЈиҗҪеңЁеҘ№зҡ„еҸ‘жўўдёҠпјҢеёҰзқҖж·Ўж·Ўзҡ„иҠұйҰҷгҖӮе··еӯҗйҮҢеҫҲйқҷпјҢеҸӘжңүйЈҺз©ҝиҝҮеұӢжӘҗзҡ„вҖңе‘ңе‘ңвҖқеЈ°пјҢиҝҳжңүеҒ¶е°”дј жқҘзҡ„еҮ еЈ°йёҹйёЈпјҢжё…и„ҶжӮҰиҖіпјҢжү“з ҙдәҶеҜӮйқҷгҖӮ
е··еҸЈзҡ„зҹіеў©дёҠеқҗзқҖдёӘз©ҝйқ’иЎ«зҡ„е°‘е№ҙпјҢйқ’иЎ«жҙ—еҫ—жңүдәӣеҸ‘зҷҪпјҢиў–еҸЈеҚ·зқҖпјҢйңІеҮәз»ҶзҳҰзҡ„жүӢи…•гҖӮд»–жӯЈз”ЁиҚүиҢҺйҖ—зқҖеҸӘзҷҪиқ¶пјҢзҷҪиқ¶зҝ…иҶҖдёҠзҡ„иҠұзә№еғҸз»ЈдёҠеҺ»зҡ„пјҢеңЁе…үйҮҢжіӣзқҖеҪ©е…үгҖӮеҗ¬и§Ғи„ҡжӯҘеЈ°пјҢд»–жҠ¬зңјзңӢеҗ‘йҳҝжёЎиӮ©еӨҙзҡ„зӢҗзҒ«пјҢжҢ‘дәҶжҢ‘зңүпјҢзңјйҮҢеёҰзқҖеҮ еҲҶеҘҪеҘҮпјҡвҖңзҷҫе№ҙзҒөзҒ«пјҢзәҜеәҰиҝҷд№Ҳй«ҳпјҢдҪ жҳҜ第дёҖдёӘеёҰзқҖиҝҷдёңиҘҝжқҘзҡ„жҙ»дәәгҖӮвҖқ
вҖңжҲ‘жүҫдёҖдёӘзҷҪиЎЈе…¬еӯҗгҖӮвҖқйҳҝжёЎжҠҠжҡ–зҺүж”ҘеңЁжҺҢеҝғпјҢжҢҮиҠӮеҫ®еҫ®жіӣзҷҪпјҢжҡ–зҺүзҡ„жё©еҮүи®©еҘ№зЁҚеҫ®е®ҡдәҶе®ҡзҘһпјҢвҖңдёүе№ҙеүҚпјҢд»–иҜҙеңЁиҝҷйҮҢзӯүжҲ‘гҖӮвҖқ
е°‘е№ҙжҠҠиҚүиҢҺжү”еңЁең°дёҠпјҢзҷҪиқ¶жҢҜзқҖзҝ…иҶҖеҫҖйӣҫйҮҢйЈһиҝңдәҶпјҢзҝ…иҶҖжүҮеҠЁзҡ„еЈ°йҹіеҫҲиҪ»гҖӮвҖңи·ҹжҲ‘жқҘгҖӮвҖқд»–з«ҷиө·иә«пјҢдёӘеӯҗдёҚз®—й«ҳпјҢиә«еҪўеҚ•и–„пјҢвҖңиҝҷжёЎйҮҢзҡ„йҷўеӯҗйғҪеҸ«вҖҳеҫ…еҪ’йҷўвҖҷпјҢжҜҸдёӘзӯүзҡ„дәәйғҪжңүдёҖй—ҙпјҢжҢүжқҘзҡ„е…ҲеҗҺйЎәеәҸжҺ’пјҢдҪ иҜҙзҡ„е…¬еӯҗпјҢиҜҘжҳҜиҘҝ巷第дёүй—ҙгҖӮвҖқ
иҘҝе··зҡ„йӣҫж·Ўеҫ—еғҸзәұпјҢйҳіе…үйҖҸиҝҮйӣҫеұӮжҙ’дёӢжқҘпјҢеҪўжҲҗж·Ўж·Ўзҡ„е…үжҹұпјҢз…§еңЁйқ’зҹіжқҝдёҠпјҢжіӣзқҖжҹ”е’Ңзҡ„е…үгҖӮ第дёүй—ҙйҷўеӯҗзҡ„й—ЁжҳҜз«№зј–зҡ„пјҢж·Ўй»„иүІзҡ„з«№зҜҫзј–еҫ—з»ҶеҜҶпјҢдёҠйқўиҝҳз•ҷзқҖз«№иҠӮзҡ„зә№и·ҜгҖӮжҺЁејҖж—¶вҖңеҗұе‘ҖвҖқдёҖеЈ°пјҢжғҠиө·дәҶйҷўи§’жўЁж ‘дёҠзҡ„еҮ еҸӘйә»йӣҖпјҢйә»йӣҖжү‘жЈұзқҖзҝ…иҶҖйЈһиө°пјҢиҗҪдёӢеҮ зүҮеҲҡжҠҪиҠҪзҡ„жўЁж ‘еҸ¶пјҢе«©з»ҝиүІзҡ„пјҢеёҰзқҖжё…ж–°зҡ„иҚүжңЁйҰҷгҖӮйҷўеӯҗйҮҢж‘ҶзқҖеј зҹіжЎҢпјҢзҹіжЎҢиЎЁйқўе…үж»‘пјҢеёҰзқҖиҮӘ然зҡ„зә№зҗҶпјҢжЎҢдёҠзҡ„йқ’з“·еЈ¶иҝҳжё©зқҖпјҢеЈ¶иә«жіӣзқҖж·Ўйқ’иүІзҡ„е…үпјҢж—Ғиҫ№ж”ҫзқҖеҚҠзӣҸжІЎе–қе®Ңзҡ„иҢ¶пјҢиҢ¶зӣҸиҫ№еҺӢзқҖзүҮеҲҡиҗҪзҡ„жўЁиҠұз“ЈпјҢйӣӘзҷҪзҡ„пјҢеёҰзқҖжө…жө…зҡ„зә№и·ҜгҖӮ
вҖңд»–еҲҡиө°жІЎеӨҡд№…гҖӮвҖқе°‘е№ҙжҢҮзқҖзҹіеҮідёҠзҡ„её•еӯҗпјҢйӮЈеё•еӯҗжҳҜж·ЎзІүиүІзҡ„пјҢз»ЈзқҖеҚҠжңөеұұиҢ¶пјҢй’Ҳи„ҡз»ҶеҜҶпјҢжҳҜйҳҝжёЎжңҖзҶҹзҡ„ж ·ејҸпјҢвҖңиҝҷжҳҜдҪ зҡ„пјҹд»–дёҖзӣҙж”ҫеңЁзҹіжЎҢдёҠпјҢиҜҙзӯүдҪ жқҘдәҶпјҢи®©дҪ зңӢзңӢгҖӮвҖқ
йҳҝжёЎж„ЈдәҶж„ЈпјҢдјёжүӢжҠҠеё•еӯҗ收иҝӣиў–йҮҢвҖ”вҖ”иҝҷжҳҜеҘ№еқ еҙ–ж—¶жҢӮеңЁд№ұжһқдёҠзҡ„пјҢеҪ“ж—¶её•еӯҗиў«еӢҫз ҙдәҶдёӘе°Ҹи§’пјҢжІЎжғіеҲ°дјҡ被他收зқҖпјҢиҝҳзјқиЎҘеҘҪдәҶпјҢз ҙи§’зҡ„ең°ж–№еӨҡдәҶдёҖеңҲе°Ҹе°Ҹзҡ„и•ҫдёқиҠұиҫ№гҖӮеҘ№жҢҮе°–еҲҡзў°еҲ°з“·еЈ¶зҡ„жё©ж„ҸпјҢйҷўй—ЁеҸЈзҡ„йЈҺеҝҪ然еҚ·зқҖжўЁиҠұз“Јеҗ№иҝӣжқҘпјҢдёҖдёӘз©ҝзҷҪиЎЈзҡ„е…¬еӯҗз«ҷеңЁе…үеҪұйҮҢпјҢзҷҪиЎЈиғңйӣӘпјҢиЎЈиўӮйЈҳйЈҳпјҢиў–еҸЈз»ЈзқҖдёҖжңөе°Ҹе°Ҹзҡ„зј жһқиҺІпјҢе’Ңжҡ–зҺүдёҠзҡ„иҠұзә№дёҖжЁЎдёҖж ·гҖӮд»–зҡ„зңүзӣ®е’Ңдёүе№ҙеүҚзҡ„и®°еҝҶеҲҶжҜ«дёҚе·®пјҢеҸӘжҳҜзңјеә•еӨҡдәҶдәӣеғҸйӣҫдёҖж ·зҡ„еҖҰж„ҸпјҢеҸ‘дёқиў«йЈҺеҗ№еҫ—еҫ®еҫ®йЈҳеҠЁпјҢжІҫзқҖдёҖзүҮе°Ҹе°Ҹзҡ„жўЁиҠұз“ЈгҖӮ
вҖңдҪ жқҘдәҶгҖӮвҖқд»–ејҖеҸЈж—¶пјҢеЈ°йҹіеғҸжөёдәҶжё©иҢ¶зҡ„иҪҜжЈүпјҢжё©е’ҢеҠЁеҗ¬пјҢвҖңжҲ‘з®—зқҖдҪ иҝҷеҮ ж—ҘиҜҘеҲ°дәҶпјҢжҜҸеӨ©йғҪжқҘйҷўеӯҗйҮҢзӯүгҖӮвҖқ
йҳҝжёЎж”ҘзқҖеё•еӯҗзҡ„жүӢзҙ§дәҶзҙ§пјҢжҢҮе°–зҡ„жҡ–зҺүзғ«еҫ—жүӢеҝғеҸ‘ж…ҢпјҡвҖңдҪ зӯүдәҶжҲ‘дёүе№ҙпјҹвҖқ
вҖңеҜ№жҲ‘жқҘиҜҙпјҢжҳҜдёүзҷҫдёӘжўЁиҠұејҖзҡ„жё…жҷЁгҖӮвҖқд»–иө°еҲ°зҹіжЎҢж—ҒпјҢз»ҷйҳҝжёЎеҖ’дәҶжқҜиҢ¶пјҢиҢ¶йӣҫиЈ№зқҖжө…ж·Ўзҡ„жЎӮйҰҷжј«ејҖжқҘпјҢжІҒдәәеҝғи„ҫпјҢвҖңжҲ‘жң¬жҳҜиҝҷжёЎйҮҢзҡ„жҠӨжёЎдәәпјҢзҷҫе№ҙеүҚйҒӯдәҶеұұйӣЁпјҢеұұдҪ“ж»‘еқЎпјҢжҲ‘иў«еӣ°еңЁжҹҙжҲҝйҮҢпјҢжҳҜдёӘз»ЈеұұиҢ¶её•еӯҗзҡ„姑еЁҳжҠҠжҲ‘ж•‘дәҶеҮәжқҘпјҢиҝҳз»ҷжҲ‘йҖҒдәҶдјӨиҚҜе’Ңеҗғзҡ„гҖӮеҘ№иҜҙпјҢиӢҘжңүжқҘз”ҹиғҪеҶҚйҒҮи§ҒпјҢиҰҒжҲ‘еңЁдә‘ж –жёЎзӯүеҘ№вҖ”вҖ”дҪ еқ еҙ–ж—¶пјҢжҲ‘еҲҡеҘҪи·ҜиҝҮпјҢзңӢи§ҒдҪ иў–йҮҢзҡ„её•еӯҗпјҢе°ұзҹҘйҒ“жҳҜдҪ дәҶгҖӮвҖқ
йҳҝжёЎжҚ§зқҖиҢ¶жқҜзҡ„жҢҮе°–жҡ–иө·жқҘпјҢзӢҗзҒ«зҡ„е…үиЈ№дҪҸдәҶзҹіжЎҢпјҢжҠҠжўЁиҠұз“ЈйғҪжҹ“жҲҗдәҶжҡ–й»„иүІпјҢиҝһиҢ¶йӣҫйғҪеҸҳеҫ—жё©жҹ”гҖӮвҖңйӮЈжҠӨжёЎдәәвҖҰвҖҰиғҪзҰ»ејҖиҝҷйҮҢеҗ—пјҹвҖқеҘ№жҠ¬еӨҙзңӢзқҖд»–пјҢзңјйҮҢеёҰзқҖеҮ еҲҶжңҹзӣјгҖӮ
вҖңиғҪгҖӮвҖқд»–жҢҮе°–зў°дәҶзў°еҘ№иӮ©еӨҙзҡ„зӢҗзҒ«пјҢйӮЈеӣўзҒөзҒ«еҝҪ然дә®иө·жқҘпјҢиЈ№дҪҸдёӨдәәзҡ„жүӢи…•пјҢжҡ–жөҒдј йҒҚе…Ёиә«пјҢвҖңжҠӨжёЎдәәзҡ„规зҹ©пјҢзӯүзҡ„дәәеёҰзқҖвҖҳеҝөжғізү©вҖҷжқҘи®ӨпјҢи§ЈдәҶжү§еҝөпјҢе°ұиғҪеҚёдәҶжёЎйҮҢзҡ„е·®дәӢпјҢжҒўеӨҚиҮӘз”ұиә«гҖӮвҖқ
иҝҷж—¶йқ’иЎ«е°‘е№ҙжү’зқҖйҷўй—ЁеҸЈзҡ„з«№зҜұжҺўиҝӣеӨҙпјҢжүӢйҮҢжҷғзқҖдёӘиҚүзј–зҡ„е°ҸзӯҗпјҢзӯҗйҮҢиЈ…зқҖдәӣеұұжһЈпјҢзәўйҖҡйҖҡзҡ„пјҢзңӢзқҖе°ұз”ңпјҡвҖңйҳҝ渡姑еЁҳпјҢдҪ иҝҷзӢҗзҒ«иғҪжҡ–жһңеӯҗеҗ—пјҹиҝҷжёЎйҮҢзҡ„еұұжһЈжҖ»еҮүеҫ—зЎҢзүҷпјҢжҲ‘жғіе°қе°қжҡ–зҡ„гҖӮвҖқ
йҳҝ渡笑зқҖзӮ№еӨҙпјҢзӢҗзҒ«зҡ„е…үиЈ№дҪҸе°‘е№ҙзӯҗйҮҢзҡ„еұұжһЈпјҢеҮүзЎ¬зҡ„жһңеӯҗзһ¬й—ҙжҡ–еҫ—иҪҜе’ҢпјҢиҝҳж•ЈеҸ‘еҮәж·Ўж·Ўзҡ„жһңйҰҷгҖӮе°‘е№ҙжҠұзқҖзӯҗи·‘иҝңж—¶пјҢеЈ°йҹіиЈ№еңЁйЈҺйҮҢпјҡвҖңдёӢж¬ЎжқҘеёҰзӮ№зі–пјҒиҝҷжёЎйҮҢзҡ„иҢ¶жІЎз”ңе‘іпјҢеұұжһЈжҡ–дәҶд№ҹдёҚеӨҹз”ңпјҒвҖқ
иө°еҮәйҷўеӯҗж—¶пјҢйҳҝжёЎеӣһеӨҙзңӢдәҶзңјвҖңеҫ…еҪ’йҷўвҖқзҡ„з«№й—ЁпјҢз«№й—ЁеңЁйЈҺйҮҢиҪ»иҪ»жҷғеҠЁпјҢеҸ‘еҮәиҪ»еҫ®зҡ„еЈ°е“ҚгҖӮйӣҫжӯЈж…ўж…ўж•ЈжҲҗжө…зҷҪзҡ„е…үпјҢиҝңеӨ„зҡ„еұұеқійҮҢйҖҸеҮәдәҶж—ҘеӨҙзҡ„жҡ–й»„пјҢжҠҠдә‘еұӮжҹ“жҲҗдәҶж·Ўж·Ўзҡ„йҮ‘иүІгҖӮеҘ№ж”Ҙзҙ§жҡ–зҺүпјҢи·ҹзқҖзҷҪиЎЈе…¬еӯҗеҫҖз•Ңзў‘иө°пјҢиҖҒиү„е…¬зҡ„иҲ№иҝҳжіҠеңЁж»©ж¶Ӯиҫ№пјҢиүҫиҚүдёІеңЁйЈҺйҮҢжҷғзқҖз»ҶзўҺзҡ„е“ҚпјҢж»©ж¶Ӯиҫ№зҡ„ж°ҙиҚүйҡҸйЈҺж‘ҶеҠЁпјҢеёҰзқҖж№ҝж„ҸгҖӮ
вҖңд»ҘеҗҺиҝҳиғҪжқҘеҗ—пјҹвҖқйҳҝжёЎй—®пјҢзӣ®е…үиҗҪеңЁз•Ңзў‘дёҠзҡ„е…°иҚүдёҠпјҢе…°иҚүеңЁе…үйҮҢжҳҫеҫ—ж„ҲеҸ‘йІңе«©гҖӮ
зҷҪиЎЈе…¬еӯҗзүөиө·еҘ№зҡ„жүӢпјҢжҢҮе°–зҡ„жё©еәҰиЈ№зқҖжҡ–зҺүзҡ„жё©еҮүпјҢеҫҲжҳҜиҲ’жңҚпјҡвҖңеҪ“然пјҢзӯүжҳҺе№ҙжўЁиҠұеҶҚејҖпјҢжҲ‘们жқҘз»ҷе°‘е№ҙйҖҒзі–пјҢеҶҚзңӢзңӢиҝҷдә‘ж –жёЎзҡ„йӣҫгҖӮвҖқ
дёӨдәәжІҝзқҖжәӘеІёеҫҖеұұеӨ–иө°ж—¶пјҢж—ҘеӨҙе·Із»ҸеҚҮеҲ°дәҶеҚҠз©әпјҢйҳіе…үйҖҸиҝҮж ‘еҸ¶зҡ„зјқйҡҷжҙ’дёӢжқҘпјҢеҪўжҲҗж–‘й©ізҡ„е…үеҪұпјҢиҗҪеңЁжәӘж°ҙйҮҢпјҢи·ҹзқҖж°ҙжөҒжҷғеҠЁгҖӮжәӘж°ҙйҮҢзҡ„дә‘еҪұзўҺжҲҗ银йіһпјҢй—ӘзқҖжіўе…үпјҢеҒ¶е°”жңүеҮ жқЎе°ҸйұјжёёиҝҮпјҢж‘ҶзқҖе°ҫе·ҙпјҢжҝҖиө·е°Ҹе°Ҹзҡ„ж¶ҹжјӘгҖӮйҳҝжёЎиё©зқҖжө…иҚүеҫҖеүҚиө°пјҢиҚүеҸ¶дёҠиҝҳжІҫзқҖжҷЁйңІпјҢжү“ж№ҝдәҶеҘ№зҡ„иЈҷж‘ҶпјҢеҮүдёқдёқзҡ„гҖӮеҝҪ然зңӢи§ҒеІёиҫ№и№ІзқҖдёӘз©ҝи“қеёғиЎ«зҡ„е©Ҷе©ҶпјҢи“қеёғиЎ«жҳҜзІ—еёғеҒҡзҡ„пјҢеёҰзқҖиҙЁжңҙзҡ„зә№и·ҜпјҢеҘ№жӯЈжҠҠеҲҡж‘ҳзҡ„йҮҺиҸҠж”ҫиҝӣз«№зҜ®йҮҢпјҢз«№зҜ®зҡ„жІҝдёҠзј зқҖеҚҠе°әзәўз»іпјҢзәўз»іжңүдәӣиӨӘиүІпјҢеҚҙеҫҲе№ІеҮҖгҖӮйҮҺиҸҠејҖеҫ—жӯЈзӣӣпјҢй»„иүІзҡ„иҠұз“ЈеёҰзқҖжё…ж–°зҡ„йҰҷж°”пјҢе Ҷж»ЎдәҶе°ҸеҚҠдёӘз«№зҜ®гҖӮ
вҖңе©Ҷе©ҶиҝҷиҸҠжҳҜиҰҒеҒҡд»Җд№ҲпјҹвҖқйҳҝжёЎи№ІдёӢжқҘпјҢеё®зқҖжҚЎиҗҪеңЁиҚүйҮҢзҡ„йҮҺиҸҠпјҢжҢҮе°–зў°еҲ°иҠұз“ЈпјҢиҪҜд№Һд№Һзҡ„гҖӮ
е©Ҷе©ҶжҠ¬иө·еӨҙпјҢи„ёдёҠзҡ„зҡұзә№йҮҢиЈ№зқҖ笑ж„ҸпјҢеғҸејҖдәҶиҠұдёҖж ·пјҡвҖңеҒҡиҸҠзі•е‘ҖпјҢжҲ‘家е°ҸеӯҗзҲұеҗғз”ңзҡ„пјҢжҜҸжңҲеҚҒдә”йғҪеӣһжқҘпјҢжҲ‘жҸҗеүҚеӨҮеҘҪзӯүзқҖе°ұиЎҢгҖӮиҝҷйҮҺиҸҠжё…зғӯпјҢеҒҡзі•д№ҹйҰҷгҖӮвҖқ
зңӢзқҖе©Ҷе©Ҷзҡ„иғҢеҪұжӢҗиҝӣз”°еҹӮпјҢз”°еҹӮдёӨж—ҒжҳҜз»ҝжІ№жІ№зҡ„еә„зЁјпјҢй•ҝеҠҝе–ңдәәпјҢе©Ҷе©Ҷзҡ„иә«еҪұж…ўж…ўж¶ҲеӨұеңЁеә„зЁјең°йҮҢгҖӮйҳҝжёЎеҝҪ然笑дәҶпјҡвҖңеҺҹжқҘвҖҳзӯүвҖҷдёҚжҳҜеҸӘжңүдә‘ж –жёЎжүҚжңүгҖӮвҖқ
вҖңжҳҜе‘ҖгҖӮвҖқзҷҪиЎЈе…¬еӯҗеё®еҘ№жӢҚжҺүиЈҷи§’зҡ„иҚүеұ‘пјҢиҚүеұ‘иҗҪеңЁең°дёҠпјҢиў«йЈҺеҚ·иө°пјҢвҖңжңүдәәзӯүеңЁжёЎйҮҢпјҢжңүдәәзӯүеңЁйҷўйҮҢпјҢжңүдәәзӯүеңЁз”°еҹӮиҫ№пјҢйғҪжҳҜжҠҠж—ҘеӯҗзҶ¬жҲҗжҡ–зҡ„гҖӮвҖқ
иө°еҲ°еұұеқіеҸЈж—¶пјҢйҳҝжёЎзңӢи§Ғи·Ҝиҫ№зҡ„жЎғж ‘дёӢж‘ҶзқҖдёӘз«№зӯҗпјҢзӯҗйҮҢжҳҜеҲҡж‘ҳзҡ„еұұжҘӮпјҢзәўеҪӨеҪӨзҡ„пјҢеғҸе°ҸзҒҜз¬јдёҖж ·гҖӮзӯҗиҫ№еқҗзқҖдёӘжүҺзҫҠи§’иҫ«зҡ„е°Ҹ姑еЁҳпјҢиҫ«еӯҗдёҠзі»зқҖзІүиүІзҡ„дёқеёҰпјҢжӯЈиё®зқҖи„ҡеӨҹжһқеӨҙдёҠзҡ„зәўжһңпјҢйһӢе°–жІҫзқҖжө…иҚүзҡ„з»ҝпјҢиЈӨи…ҝеҚ·зқҖпјҢйңІеҮәз»ҶзҳҰзҡ„е°Ҹи…ҝгҖӮжЎғж ‘зҡ„жһқе№ІдёҚз®—зІ—пјҢжһқеӨҙдёҠжҢӮж»ЎдәҶеұұжҘӮпјҢеҺӢеҫ—жһқжқЎеҫ®еҫ®ејҜжӣІгҖӮ
вҖңжҲ‘её®дҪ ж‘ҳгҖӮвҖқйҳҝжёЎиө°иҝҮеҺ»пјҢзӢҗзҒ«зҡ„е…үиЈ№дҪҸжһқеӨҙзҡ„еұұжҘӮпјҢзҶҹйҖҸзҡ„зәўжһңвҖңе“—е•Ұе•ҰвҖқиҗҪиҝӣзӯҗйҮҢпјҢз ёеҮәз»ҶзўҺзҡ„е“ҚпјҢеёҰзқҖжһңе®һзҡ„йҘұж»ЎгҖӮ
е°Ҹ姑еЁҳжҠұзқҖзӯҗ笑еҮәдәҶжўЁж¶ЎпјҢзҫҠи§’иҫ«жҷғеҫ—иҪ»еҝ«пјҡвҖңи°ўи°ўе§җе§җпјҒжҲ‘ж‘ҳеұұжҘӮз»ҷеҘ¶еҘ¶з…®зі–ж°ҙпјҢеҘ¶еҘ¶еңЁе®¶зӯүжҲ‘е‘ўпјҒеҘ¶еҘ¶зүҷдёҚеҘҪпјҢз…®иҪҜдәҶеҘ№жүҚеҗғеҫ—еҠЁгҖӮвҖқ
зңӢзқҖе°Ҹ姑еЁҳи·‘иҝңзҡ„иғҢеҪұпјҢеҘ№зҡ„е°Ҹзҹӯи…ҝиҝҲеҫ—йЈһеҝ«пјҢз«№зӯҗеңЁиҮӮејҜйҮҢжҷғжӮ пјҢеұұжҘӮзҡ„йҰҷж°”дёҖи·ҜйЈҳж•ЈгҖӮйҳҝжёЎж‘ёдәҶж‘ёиӮ©еӨҙзҡ„зӢҗзҒ«вҖ”вҖ”иҝҷеӣўзҒ«еҺҹжқҘдёҚжӯўиғҪи®Өи·ҜпјҢиҝҳиғҪжҡ–дёҖжҡ–ж—Ғдәәзҡ„вҖңзӯүвҖқпјҢи®©иҝҷд»ҪжңҹзӣјеӨҡдәҶеҮ еҲҶжё©еәҰгҖӮ
ж—ҘеӨҙеҒҸиҘҝж—¶пјҢдёӨдәәиө°еҲ°дәҶй•ҮеҸЈзҡ„зҹіжЎҘдёҠгҖӮзҹіжЎҘжҳҜйқ’зҹіжқҝй“әзҡ„пјҢжЎҘж ҸдёҠйӣ•еҲ»зқҖз®ҖеҚ•зҡ„иҠұзә№пјҢжңүдәӣең°ж–№е·Із»ҸзЈЁжҚҹпјҢеҚҙжӣҙжҳҫеҸӨжңҙгҖӮжЎҘиҫ№зҡ„иҖҒж§җж ‘й•ҝеҫ—жһқз№ҒеҸ¶иҢӮпјҢжө“еҜҶзҡ„жһқеҸ¶йҒ®еҮәеӨ§зүҮйҳҙеҮүпјҢж ‘дёӢж‘ҶзқҖдёӘзі–з”»ж‘ҠеӯҗпјҢж‘Ҡдё»жҳҜдёӘз©ҝзҒ°еёғиЎ«зҡ„иҖҒзҲ·еӯҗпјҢзҒ°еёғиЎ«жҙ—еҫ—е№ІеҮҖпјҢиў–еҸЈзјқзқҖиЎҘдёҒгҖӮд»–жӯЈз”Ёзі–зЁҖз”»зқҖе…”еӯҗпјҢй“ңеӢәйҮҢзҡ„зі–зЁҖжіӣзқҖзҗҘзҸҖиүІзҡ„е…үпјҢйЎәзқҖеӢәеӯҗиҫ№зјҳзј“зј“жөҒдёӢпјҢеңЁзҹіжқҝдёҠеӢҫеӢ’еҮәе…”еӯҗзҡ„иҪ®е»“пјҢзі–йҰҷиЈ№зқҖжҡ–ж„ҸеңЁйЈҺйҮҢжј«ејҖпјҢз”ңеҫ—иҜұдәәгҖӮ
вҖңжқҘдёӨдёІзі–з”»пјҹвҖқзҷҪиЎЈе…¬еӯҗжҢҮзқҖж‘ҠеӯҗдёҠзҡ„зі–е…”пјҢзі–е…”е·Із»Ҹз”»еҘҪпјҢжҸ’еңЁж—Ғиҫ№зҡ„иҚүжҠҠдёҠпјҢжҷ¶иҺ№еү”йҖҸпјҢвҖңдҪ е°Ҹж—¶еҖҷпјҢжҳҜдёҚжҳҜд№ҹзҲұеҗғиҝҷдёӘпјҹвҖқ
йҳҝжёЎзӮ№еӨҙж—¶пјҢиҖҒзҲ·еӯҗе·Із»ҸжҠҠзі–е…”йҖ’дәҶиҝҮжқҘпјҢз«№зӯҫдёҠзҡ„зі–е…”жІҫзқҖз»ҶзўҺзҡ„иҠқйә»пјҢйҰҷж°”жӣҙжө“дәҶгҖӮвҖңе°Ҹдјҷеӯҗзңје…үеҘҪпјҢиҝҷ姑еЁҳзңӢзқҖйқўе–„пјҢжҳҜеҲҡд»ҺеӨ–еӨҙеӣһжқҘпјҹвҖқиҖҒзҲ·еӯҗ笑зқҖиҜҙпјҢзңји§’зҡ„зҡұзә№жҢӨеңЁдёҖиө·пјҢеҫҲжҳҜж…ҲзҘҘгҖӮ
вҖңжҳҜе‘ҖпјҢеҲҡеҜ»зқҖдәәпјҢиҝҷе°ұеӣһ家дәҶгҖӮвҖқзҷҪиЎЈе…¬еӯҗд»ҳдәҶй’ұпјҢжҠҠзі–е…”еЎһиҝӣйҳҝжёЎжүӢйҮҢпјҢжҢҮе°–зў°зқҖеҘ№зҡ„жҺҢеҝғпјҢжҡ–еҫ—еғҸжҷ’йҖҸзҡ„жЈүзө®пјҢеёҰзқҖе®үеҝғзҡ„жё©еәҰгҖӮ
йҳҝжёЎе’¬дәҶеҸЈзі–е…”пјҢз”ңж„Ҹжј«ејҖж—¶пјҢйЎәзқҖе–үе’ҷеҫҖдёӢж·ҢпјҢжҡ–дәҶж•ҙдёӘиғёи…”гҖӮеҘ№зңӢи§ҒжЎҘйӮЈеӨҙиө°жқҘдёӘз©ҝйқ’еёғиЎ«зҡ„йқ’е№ҙпјҢжүӢйҮҢжҸҗзқҖдёӘеёғеҢ…пјҢеёғеҢ…дёҠз»ЈзқҖеҚҠжңөеұұиҢ¶пјҢе’ҢеҘ№её•еӯҗдёҠзҡ„иҠұзә№еҫҲеғҸгҖӮиҖҢй•ҮеҸЈзҡ„зҹійҳ¶дёҠпјҢз«ҷзқҖдёӘз©ҝзўҺиҠұиЎ«зҡ„姑еЁҳпјҢзўҺиҠұиЎ«йўңиүІйІңиүіпјҢиЈҷж‘Ҷж‘ҶеҠЁж—¶еғҸејҖдәҶдёҖжңөиҠұгҖӮзңӢи§Ғйқ’е№ҙж—¶пјҢеҘ№з¬‘зқҖжҢҘдәҶжҢҘжүӢпјҢеҸ‘жўўзҡ„иқҙиқ¶з»“жҷғеҫ—жё©жҹ”пјҢзңјйҮҢж»ЎжҳҜж¬ўе–ңгҖӮ
вҖңйӮЈжҳҜеңЁзӯүд»–е‘ўгҖӮвҖқйҳҝжёЎжҢҮзқҖ姑еЁҳзҡ„ж–№еҗ‘пјҢзі–йҰҷиЈ№зқҖеҘ№зҡ„еЈ°йҹіпјҢиҪҜиҪҜзҡ„гҖӮ
зҷҪиЎЈе…¬еӯҗзүөзҙ§еҘ№зҡ„жүӢпјҢжҢҮе°–жүЈзқҖеҘ№зҡ„жҢҮзјқпјҢеҠӣйҒ“йҖӮдёӯпјҡвҖңжҲ‘们д№ҹиҜҘвҖҳеҲ°е®¶вҖҷдәҶгҖӮвҖқ
д»–иҜҙзҡ„вҖң家вҖқпјҢжҳҜй•ҮдёңеӨҙзҡ„дёҖй—ҙе°ҸйҷўпјҢйҷўй—ЁеҸЈз§ҚзқҖжЈөеҲҡжҠҪжһқзҡ„е°ҸжўЁж ‘пјҢж ‘жһқдёҠеҶ’еҮәе«©з»ҝзҡ„ж–°иҠҪпјҢе……ж»Ўз”ҹжңәгҖӮзӘ—жЈӮдёҠжҢӮзқҖдёІж–°жҷ’зҡ„иүҫиҚүпјҢиүҫиҚүзҡ„йўңиүІжҳҜж·ұз»ҝиүІзҡ„пјҢйҰҷиЈ№зқҖйҳіе…үзҡ„жҡ–пјҢжё…ж–°еҘҪй—»гҖӮжҺЁејҖй—Ёж—¶пјҢйҷўеӯҗйҮҢзҡ„зҹіжЎҢдёҠж‘ҶзқҖеҲҡжё©еҘҪзҡ„иҢ¶пјҢиҢ¶еЈ¶жҳҜзІ—йҷ¶еҒҡзҡ„пјҢеёҰзқҖиҙЁжңҙзҡ„иҙЁж„ҹпјҢж—Ғиҫ№ж”ҫзқҖеҚҠзўҹзӮ’еҫ—йҰҷй…Ҙзҡ„иҠұз”ҹпјҢиҠұз”ҹеЈійҮҢиЈ№зқҖжө…зәўзҡ„д»ҒпјҢйҰҷж°”жү‘йј»гҖӮйҷўеӯҗи§’иҗҪйҮҢз§ҚзқҖеҮ ж ӘжЎӮиҠұпјҢжһқеӨҙе·Із»ҸеҶ’еҮәдәҶе°Ҹе°Ҹзҡ„иҠұиӢһпјҢеёҰзқҖж·Ўж·Ўзҡ„з”ңйҰҷгҖӮ
вҖңиҝҷжҳҜвҖҰвҖҰвҖқйҳҝжёЎжңүдәӣж„ЈпјҢжҢҮе°–зў°зқҖзҹіжЎҢзҡ„жё©ж„ҸпјҢеҝғйҮҢж¶ҢдёҠдёҖиӮЎжҡ–жөҒгҖӮ
вҖңжҲ‘жҜҸжңҲйғҪжқҘжү“жү«пјҢжғізқҖдҪ жқҘдәҶе°ұиғҪдҪҸгҖӮвҖқзҷҪиЎЈе…¬еӯҗз»ҷеҘ№еҖ’дәҶжқҜиҢ¶пјҢиҢ¶йӣҫйҮҢиЈ№зқҖжЎӮиҠұйҰҷпјҢвҖңйҷўеӯҗдёҚеӨ§пјҢдҪҶж ·ж ·йғҪйҪҗгҖӮд»ҘеҗҺиҝҷйҮҢе°ұжҳҜ家дәҶпјҢдёҚз”ЁеҶҚеӣӣеӨ„еҘ”жіўгҖӮвҖқ
йҳҝжёЎжҚ§зқҖиҢ¶жқҜеқҗеңЁзҹіеҮідёҠпјҢжўЁж ‘еҸ¶зҡ„еҪұеӯҗиҗҪеңЁеҘ№жүӢиғҢдёҠпјҢеғҸз»ҶзўҺзҡ„е…үж–‘пјҢйҡҸзқҖйЈҺиҪ»иҪ»жҷғеҠЁгҖӮиӮ©еӨҙзҡ„зӢҗзҒ«иҪ»иҪ»жҷғзқҖпјҢж©ҳзәўиүІзҡ„жҡ–е…үиЈ№дҪҸдәҶж•ҙй—ҙйҷўеӯҗпјҢиҝһйЈҺйҮҢзҡ„жЎӮйҰҷйғҪеҸҳеҫ—иҪҜе’ҢгҖӮеҘ№еҝҪ然жғіиө·дә‘ж –жёЎзҡ„йӣҫпјҢжғіиө·еҫ…еҪ’йҷўзҡ„иҢ¶пјҢжғіиө·иҖҒиү„е…¬зҡ„иҲ№пјҢжғіиө·е··еҸЈзҡ„зҙ«зүөзүӣпјҢжғіиө·зҹіжЎҢдёҠзҡ„жўЁиҠұз“ЈвҖ”вҖ”еҺҹжқҘжүҖжңүзҡ„вҖңзӯүвҖқпјҢеҲ°жңҖеҗҺйғҪдјҡеҸҳжҲҗвҖңеңЁиҝҷе„ҝе‘ўвҖқзҡ„е®үзЁіпјҢеғҸиҝҷжқҜжё©иҢ¶пјҢдёҚзғ«дёҚеҮүпјҢеҲҡеҘҪжҡ–дәәеҝғгҖӮ
еӮҚжҷҡзҡ„йЈҺиЈ№зқҖжЎӮиҠұйҰҷеҗ№иҝӣйҷўеӯҗж—¶пјҢйҳҝжёЎйқ еңЁзҷҪиЎЈе…¬еӯҗзҡ„иӮ©еӨҙпјҢзңӢи§ҒеӨ©дёҠзҡ„дә‘ж…ўж…ўй“әжҲҗдәҶжҡ–й»„иүІпјҢеғҸиў«еӨ•йҳіжҹ“йҖҸ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ҝғйӯ”еү‘й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ҚҒе…«иӢұйӣ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јҖеұҖй“ёе°ұж— дёҠж №еҹәпјҢжҲ‘й—®йјҺд»ҷи·Ҝпј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Һе •д№қе№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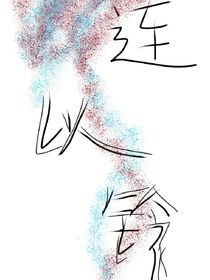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д»Ҙй“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