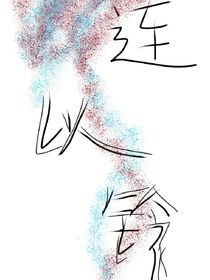《云栖渡,狐火焚三世,断尾换长生》
云栖渡:狐火焚三世,断尾换长生
忘川河的水,凉得能冻碎魂魄。
阿渡撑着乌木船,在泛着墨色涟漪的河面上漂了三百年。她肩头悬着簇橘红狐火,是这死寂忘川里唯一的暖光——能照见亡魂的前世因果,能焚尽缠人的怨念,却烧不热她自己早已冰封的心。船桨划过水面时,会带起细碎的魂屑,像三百年前青丘的落雪,落在她只剩八根的狐尾上,凉得刺骨。
“渡我。”
冷不丁的声音撞进耳里,阿渡的船桨“咚”地砸进水里。
船头站着个男人,月白仙袍沾着未干的血,侧脸的轮廓是她刻在骨血里的模样:九重天的战神墨渊,她等了三百年的人。
阿渡指尖蜷紧,狐火颤了颤。三百年前,她还是青丘最娇纵的小狐狸,偷溜到九重天看战神祭剑,却撞上失控的焚天剑——那剑被觊觎青丘狐心的魔修动了手脚,裹着能蚀魂的魔息,目标本是她这只“心头血能养魔器”的九尾狐。是墨渊扑过来替她挡了那道仙力,仙骨被魔息啃噬,战神位险些被夺。
没人知道,她为了救他,在青丘的聚灵阵里断了自己的狐尾。九尾狐断尾,是剜心的痛,每断一根,灵力就散一分。她断了最灵的那根尾,换九重天的圣物“渡生莲”融在他仙脉里,自己却因私动圣物被青丘驱逐,困在忘川渡魂三百年。
“我渡了你三百年。”阿渡的声音裹着忘川的凉,“墨渊,我们两清了。”
男人抬眼,眼底是她看不懂的猩红。他突然笑了,仙袍下的手扣住她的腕子,力道狠得像要捏碎她的骨头:“两清?你偷了我的渡生莲,忘了?”
阿渡猛地抬头。三百年前她断尾后灵力溃散,是墨渊把渡生莲塞给她,说“渡你,也渡我”,怎么成了她偷的?
“那是你给我的。”
“是你偷的。”墨渊的眼彻底红了,掌心的仙力混着未散的魔息刺进她的狐脉,“我仙骨再损,只有渡生莲能救。阿渡,把莲交出来,或者——”
他的指尖擦过她的狐尾根(八根尾羽晃得他眼疼),语气是淬了冰的疯魔:“用你的狐心,换。”
忘川的水骤然翻涌,阿渡肩头的狐火爆成橘红的焰,烧得墨渊的仙袍嗤嗤作响。她挣开他的手,船桨拍在船舷上:“你被执念逼疯了。”
三百年前的真相,她没说出口:墨渊替她挡剑,是知道魔修会盯紧她,故意用“被夺仙骨”的理由,把她逼去忘川避祸。他说“忘川的水遮得住狐族气息”,却没说自己要留在九重天,替她挡那些明枪暗箭。可现在的他,眼底只剩魔息和对“生”的执念。
“疯的是你。”墨渊的仙力裹着忘川水砸向她,浪头卷着碎魂的冷,“不交莲,我就毁了这忘川,让你永世困在碎魂水里。”
阿渡的狐火骤然暗下去。她摸向心口——当年怕渡生莲被魔修夺走,她把莲融在了自己狐心里。取出来,她就死了。
可她看着墨渊眼底的魔息,突然笑了。狐尾轻轻扫过他的手背,是三百年前她撒娇时的动作:“墨渊,你要渡生莲,我给你。”
狐心被剜出的那一刻,阿渡的狐火彻底灭了。她倒在船板上,八根尾羽一寸寸化作飞灰,只有指尖还碰着他的仙袍。
“墨渊,”她的声音轻得像忘川的雾,“渡生莲能救你,却救不了你的执念。下一世,别再找我了。”
墨渊接住那颗裹着渡生莲的狐心,掌心的血烫得他发抖。忘川的风里,突然飘来三百年前的声音——小狐狸叼着他的袖角,眼尾翘得像月牙:“战神大人,我偷了你的莲,也偷了你的心,你要不要娶我呀?”
他猛地低头,船板上只剩一捧狐灰,和一根断了的、泛着血光的狐尾。
忘川的水,突然暖了。那是阿渡三百年的泪,终于烧干了。
墨渊服下渡生莲,仙骨上的魔息瞬间消散,可心口的位置却空得发疼。他在忘川河畔守了七日,疯了似的打捞阿渡的狐灰,却只捡到那根断尾。直到第八日,九重天的仙官来报,说当年暗算焚天剑的魔修卷土重来,已攻破南天门。
墨渊握紧断尾,眼底的猩红褪去,只剩冰冷的杀意。他提着焚天剑重返九重天,那一战打了三天三夜,魔修的血染红了南天门的台阶,而他的仙袍上,也沾满了魔息与血污。战后,他跪在天帝面前,请求辞去战神之位,入凡间轮回——他要找她,哪怕耗尽生生世世。
天帝叹了口气,准了。只是渡生莲的仙力太强,他的仙骨未散,轮回时会带着记忆,却也会被三百年前的执念缠绕,时而清醒,时而疯魔。
“墨渊,这是对你的惩罚,也是对你的成全。”天帝说,“若能解开心结,尚可重返仙班;若执念不消,便永世困在轮回里,尝尽她当年的苦。”
墨渊没有回头,抱着那根断尾,纵身跃入了轮回道。
凡间的雨,缠了临安城三个月。
说书先生拍着醒木,唾沫星子溅在茶客的瓜子盘里:“话说这沈渊沈公子,三个月前从忘川支流捡回个姑娘,那姑娘长得跟画里的狐狸精似的,偏生沈公子宠得紧,连沈家祖传的玉坠都给她挂脖子上咯——”
茶楼上,沈渊捏着茶杯的手紧了紧。他桌对面的姑娘穿鹅黄衫子,正啃着桂花糕,眼尾翘得像月牙,脖子上的玉坠(刻着“墨”字)晃得他眼晕。
“阿渡,”沈渊的声音发涩,“你到底是谁?”
姑娘抬眼,嘴角沾着糕屑,笑起来有两个梨涡:“我是阿渡啊,你捡回来的小可怜。”
沈渊是临安城的书生,三个月前在忘川渡口(凡间的支流)捡到她时,她浑身是伤,蜷在破船板上,说自己叫阿渡,什么都不记得了。可他总觉得,她看他的眼神太熟,像等了三百年的人——比如他熬夜温书时,她会偷偷把狐火悬在灯盏旁;比如他被同窗欺负时,她的尾羽会悄悄缠上对方的脚踝,让那人摔个狗啃泥;比如他咳嗽时,她会翻遍全城的药铺,捧着一碗热姜汤蹲在他床边,眼睛红红的像兔子。
更奇怪的是,她怕火,却总在夜里摸出那簇橘红狐火,对着玉坠掉眼泪。沈渊问过她怎么回事,她只说觉得玉坠眼熟,狐火是天生就有的,能暖身子。
其实阿渡没说实话。她不是不记得,是不敢记得。忘川的痛太刻骨,狐心被剜的滋味,尾羽化作飞灰的绝望,她一想起来就浑身发抖。可看到沈渊的脸,她又忍不住靠近——他的眉眼,他的笑,都和三百年前的墨渊一模一样,让她又爱又怕。
“沈公子!”楼下突然传来嘈杂声,衙役踹开茶馆的门,刀鞘撞在木柱上,震得茶碗叮当响,“有人举报你私藏妖物!”
阿渡的狐火瞬间收进袖中,指尖的糕屑抖落在桌上。沈渊把她护在身后:“她是我远亲,不是妖物。”
衙役的刀架在他脖子上,另一只手掏出张画像——纸上的姑娘和阿渡长得一模一样,旁边写着“青丘逃狐,取其心者,可得长生”。
阿渡的脸色白了。她想起零碎的记忆:那个要抢她狐心的魔修,竟然也跟着她转世了。
“我不是妖。”她攥紧沈渊的衣角,狐尾在衫子里颤了颤(她的尾羽长回来了,却只有八根)。
衙役的刀突然刺向她,沈渊想都没想,扑过去替她挡了——刀刃扎进他的后背,血溅在阿渡的鹅黄衫子上,像极了三百年前墨渊仙袍上的红。
阿渡的狐火爆开,橘红的焰裹着衙役的刀,烧得刀身嗤嗤融化。她抱着沈渊,狐尾卷住他的伤口,心口的渡生莲(竟跟着她转世了)散出微光,替他止住了血。
“阿渡,”沈渊的手摸着她的尾羽,指尖沾着血,却笑了,“原来你真的是狐狸。”
他的笑和三百年前的墨渊一模一样:“没关系,我不怕你。”
阿渡的眼泪砸在他的伤口上。她想起三百年前,墨渊也是这样,替她挡了焚天剑的仙力,笑着说“小狐狸,我不怕你,我护你”。可这一世,她不想再让他为自己受伤了。
可远处的巷口,一道黑影裹着雨雾站着,掌心的魔器泛着冷光——那是墨渊的另一个“影子”,是被三百年前未散的魔息控制的部分,也是那个魔修的眼线。他看着阿渡的狐尾,眼底是疯魔的执念:“阿渡,你的狐心,我要定了。”
雨又下起来,阿渡抱着沈渊,狐火裹着他的身体,像三百年前,她裹着墨渊的仙骨。
这一世,她不想再断尾了。她想护着他,哪怕代价是,魂飞魄散。
沈渊的伤养了半月才好,可临安城的“捉妖令”却越来越紧。阿渡不敢再用狐火,连尾羽都收得紧紧的,只敢在夜里趁沈渊睡熟,偷偷用灵力替他温着药。她知道魔修在找她,也知道沈渊的身份不简单——他脖子上的玉坠,是九重天的仙玉,寻常凡人不可能有。
这天夜里,她正蹲在灶前添柴,突然听见院外传来风声——不是寻常的雨风,是裹着魔息的冷。
阿渡的狐尾瞬间竖起来。她刚要叫醒沈渊,院门锁“咔哒”一声碎了,黑影裹着雨雾闯进来,掌心的魔器直指她的心口。
“阿渡,把狐心交出来。”黑影的声音是墨渊的,却裹着淬冰的魔息。
沈渊被惊醒,抄起桌上的砚台砸过去:“你是谁?”
黑影挥袖打飞砚台,魔器的光扫向沈渊,阿渡扑过去挡在他身前——魔器的光擦过她的狐尾,八根尾羽瞬间焦了三根。
“别碰他。”阿渡的狐火裹着身体,像只炸毛的小兽。
黑影笑了,魔息卷着她的狐火:“三百年前你断尾救我,三百年后你还要护着我的转世?阿渡,你怎么这么蠢。”
他的话像惊雷,劈得阿渡愣在原地——他是墨渊?是那个在忘川剜了她狐心,又入轮回找她的墨渊?
“你是……墨渊?”阿渡的声音发抖。
黑影没有回答,魔器刺向沈渊的喉咙,阿渡终于反应过来,狐尾缠上魔器的刃,另一只手推着沈渊往门外跑:“走!别回来!”
可沈渊没走。他看着阿渡焦黑的尾羽,突然抓住魔器的刃,掌心的血顺着刃身往下流:“你要的是她,别伤她。”
黑影的眼彻底红了——魔息和神智在他体内撕扯,他看着沈渊掌心的血,想起三百年前忘川的那捧狐灰,想起自己辞去战神位的决心,突然嘶吼着甩开魔器:“滚!”
阿渡趁机拽着沈渊往外跑,可没跑两步,黑影的魔息就卷住了她的脚踝。他把她按在院墙上,魔器抵着她的狐心,声音是哭腔的疯魔:“为什么不认我?阿渡,我是墨渊啊,我来找你了。”
沈渊扑过来,却被魔息掀飞,撞在院门上,昏了过去。
阿渡看着他额角的血,突然笑了。她的狐尾缠上魔器的刃,一点点收紧——九尾狐的尾羽能缚魔,代价是断尾。三百年前她断尾救他,三百年后,她还是想护着他,不管他是战神墨渊,还是书生沈渊。
“墨渊,”她的尾羽寸寸断裂,血溅在他的仙袍上,“这是我最后一次断尾了。”
第八根尾羽断开的瞬间,狐火裹着魔息爆开,黑影的魔器碎了,魔息从他体内散出来,他终于清醒,看着阿渡断了的尾羽,愣在原地。
“阿渡……”
阿渡倒在他怀里,狐心的渡生莲散出最后一点光,裹住了沈渊的身体:“墨渊,这一世,我护他,也护你。”
她的狐火彻底灭了,身体化作细碎的光,飘在临安的雨里。那些光落在沈渊身上,他醒了过来,眼神清明,带着墨渊三百年的记忆。
“阿渡!”他伸手去抓,却只抓到一把冰冷的雨。
墨渊抱着那八根断尾,跪在雨里,像三百年前忘川的那只乌木船,再也等不到撑船的人。雨水中,他感受到了阿渡最后的心意——渡生莲的光不仅护住了沈渊的身体,还净化了他体内最后的魔息,解了他三百年的执念。
他终于明白了。阿渡从来不是偷他渡生莲的贼,而是用自己的性命护了他两世的人。他的执念,是对生的渴望,也是对失去的恐惧,可他却因为这份执念,伤了最想护的人。
远处,魔修的身影出现,看着漫天飘散的光点,冷笑一声:“没了狐心,看你还怎么护着她。”
墨渊猛地抬头,眼底是滔天的恨意。他捡起地上的断尾,指尖凝起仙力——没有了焚天剑,没有了战神位,可他还有三百年的仙骨,还有对阿渡的愧疚与爱意。
“我要你,为她偿命。”
那一战,临安城的雨停了。魔修被墨渊彻底斩杀,可阿渡却再也回不来了。墨渊抱着断尾,走遍了凡间的山川河流,他想找到阿渡的残魂,却一无所获。
后来,他回到了忘川河畔,做了个撑船的渡夫。他的船是乌木的,和三百年前阿渡的那只一样,船舷上挂着八根断尾,风吹过时,会发出细碎的响。他穿着粗布衣衫,不再是九重天的战神,只是一个等待的渡夫。
忘川的水还是凉的,却总能漂来桂花糕的香——那是阿渡在凡间最爱的味道。他撑着船,渡了无数亡魂,每一个亡魂路过,他都会问一句:“你见过一只叫阿渡的小狐狸吗?八根尾羽,肩头有橘红狐火。”
亡魂们总是摇头,说忘川里没有这样一只狐狸。
就这样,又过了三百年。
这天,他撑船渡魂时,看见船头站着个穿鹅黄衫子的姑娘,眼尾翘得像月牙,正蹲在船板上捡魂屑,肩头悬着簇橘红狐火。
姑娘抬起头,看见他,眼睛亮了:“你是谁呀?你的船真好看,这断尾……好眼熟。”
墨渊的船桨“咚”地砸进水里。
姑娘叫阿渡,说自己是青丘的小狐狸,偷溜出来玩,迷了路,在忘川里漂了三百年,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觉得这忘川的水很亲切,觉得他很亲切。
“你等谁?”阿渡把捡起来的魂屑放在手心,吹了口气,魂屑化作细碎的光,“他们说,忘川的渡夫都在等一个人。”
墨渊看着她肩头的狐火,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