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з« пјҡзңјзәҝеӨҚеҪ’жқҘпјҢж¬ІжҜҒеңЈеғҸи®Ў
иҚҜзў—иҝҳеңЁжЎҢдёҠеҶ’зқҖзғӯж°”пјҢзҺӢе®Ҳд»Ғе·Із»ҸеҮәдәҶй—ЁгҖӮ
д»–иө°еҫ—дёҚеҝ«пјҢдҪҶжҜҸдёҖжӯҘйғҪзЁігҖӮиөөеҜЎеҰҮйӮЈдёҖеЈ°вҖңеҖ’дәҶдёңиҘҝвҖқпјҢи®©д»–еҝғйҮҢзҡ„ејҰз«ӢеҲ»з»·дәҶиө·жқҘгҖӮз”ҹзҘ еҲҡз«Ӣиө·жқҘпјҢзҷҫ姓еҝғйҮҢеҲҡжңүзӮ№жҢҮжңӣпјҢиҝҷж—¶еҖҷеҮәдәӢпјҢдёҚжҳҜе°ҸдәӢгҖӮ
йЈҺд»Һз”°еҹӮйӮЈиҫ№еҗ№иҝҮжқҘпјҢеёҰзқҖдёҖиӮЎеӯҗдёҚеҜ№еҠІзҡ„е‘ійҒ“гҖӮиҜҙдёҚжё…жҳҜи…ҘиҝҳжҳҜиҮӯпјҢеғҸжҳҜзғӮиҸңеҸ¶еӯҗжіЎеңЁж°ҙйҮҢеӨӘд№…пјҢеҸҲж··дәҶзӮ№й“Ғй”ҲгҖӮд»–жІЎеҒңжӯҘпјҢжүӢжҢҮиҪ»иҪ»зў°дәҶдёӢи…°й—ҙзҡ„жЎғжңЁеү‘гҖӮеү‘иә«еҫ®йңҮпјҢдёҚжҳҜж•Ңж„ҸпјҢжҳҜиӯҰи§үгҖӮ
жқ‘еҸЈжІЎдәәгҖӮж—©дёҠзҡ„зғӯй—№ж•ЈдәҶпјҢеӯ©еӯҗеҺ»ең°еӨҙжҚЎиұҶи§’пјҢиҖҒдәәеӣһеұӢжү“зӣ№гҖӮеҸӘжңүз”ҹзҘ еүҚйӮЈзүҮз©әең°иҝҳж•һзқҖпјҢжңЁеғҸйқҷйқҷз«ӢзқҖпјҢжҠ«зқҖйӮЈд»¶жҙ—еҫ—еҸ‘зҷҪзҡ„йқӣи“қзӣҙиЈ°пјҢи„ёдёҠжҳҜжқ‘ж°‘з…§зқҖи®°еҝҶйӣ•еҮәжқҘзҡ„жЁЎж ·вҖ”вҖ”зңүйӘЁй«ҳдәӣпјҢеҳҙи§’еҺӢзқҖпјҢеғҸжҖ»еңЁжғідәӢжғ…гҖӮ
йҰҷзӮүж‘ҶеңЁеғҸеүҚпјҢй“ңзҡ®еҢ…и§’пјҢжҳҜиөөеҜЎеҰҮжӢҝиҮӘ家е«ҒеҰҶй”…ж”№зҡ„гҖӮзӮүеҸЈй»‘зҒ°жңӘеҶ·пјҢеҸҜиҫ№дёҠжңүдёҖеңҲж№ҝз—•пјҢйўңиүІеҸ‘жҡ—пјҢеғҸжҳҜжіјдәҶй…’пјҢеҸҲдёҚеғҸгҖӮ
зҺӢе®Ҳд»Ғиө°иҝ‘дёӨжӯҘпјҢи№ІдёӢгҖӮ
д»–дјёжүӢжҠ№дәҶзӮ№йӮЈж№ҝз—•пјҢжҢҮе°–дёҖеҮүпјҢйҡҸеҚіжіӣиө·йә»ж„ҸгҖӮиҝҷдёҚжҳҜж°ҙпјҢд№ҹдёҚжҳҜй…’гҖӮд»–жҚ»дәҶжҚ»пјҢйӮЈдёңиҘҝй»ҸзіҠзіҠзҡ„пјҢй—»зқҖи…ҘдёӯеёҰиӢҰпјҢеғҸжӯ»йұјиӮҡеӯҗйҮҢзҡ„дёңиҘҝгҖӮ
вҖңеҰ–иЎҖгҖӮвҖқд»–дҪҺеЈ°иҜҙгҖӮ
иҜқйҹіжңӘиҗҪпјҢзңји§’жү«еҲ°дәәеҪұдёҖй—ӘгҖӮ
жҳҜдёӘиҙ§йғҺпјҢжҢ‘зқҖжӢ…еӯҗд»Һдёңиҫ№з»•иҝҮжқҘпјҢз«№зӯҗйҮҢж‘ҶзқҖй’ҲзәҝгҖҒзҒ«зҹігҖҒзІ—зӣҗпјҢзңӢзқҖеҜ»еёёгҖӮдҪҶд»–и„ҡжӯҘиҷҡжө®пјҢиӮ©дёҠжүҒжӢ…жҷғеҫ—дёҚиҮӘ然пјҢеғҸжҳҜж•…ж„Ҹиө°ж…ўгҖӮ
зҺӢе®Ҳд»ҒжІЎеҠЁпјҢеҸӘзӣҜзқҖд»–гҖӮ
иҙ§йғҺдҪҺеӨҙзңӢйһӢпјҢз»•ејҖйҰҷзӮүеҫҖжңЁеғҸиғҢеҗҺиө°гҖӮжүӢдјёиҝӣиў–еӯҗпјҢжҺҸеҮәдёӘе°Ҹ瓷瓶пјҢ瓶еҸЈжІҫзқҖй»‘жёЈгҖӮд»–и№ІдёӢпјҢеҫҖеә•еә§иғҢйқўеҖ’дәҶдёҖзӮ№ж¶ІдҪ“пјҢеҠЁдҪңйЈһеҝ«пјҢиҝҳжғіз”Ёиў–еӯҗж“ҰгҖӮ
вҖңдҪҸжүӢпјҒвҖқдёҖеЈ°еҗјзӮёеңЁз©әең°дёҠгҖӮ
иөөеҜЎеҰҮд»ҺжӢҗи§’еҶІеҮәжқҘпјҢжүӢйҮҢжӢҺзқҖиҸңеҲҖгҖӮеҘ№д»ҠеӨ©жІЎзі»еӣҙиЈҷпјҢз©ҝзқҖжҙ—ж—§зҡ„йқ’еёғиЎ«пјҢеӨҙеҸ‘д№ұзіҹзіҹжүҺзқҖпјҢзңјзқӣзһӘеҫ—еғҸиҰҒиЈӮејҖгҖӮ
иҙ§йғҺзҢӣең°еӣһеӨҙпјҢи„ёиүІеҸҳдәҶгҖӮ
вҖңжҲ‘ж—©зңӢзқҖдҪ пјҒвҖқиөөеҜЎеҰҮдёҖи„ҡиё№зҝ»жӢ…еӯҗпјҢй’ҲзәҝзҒ«зҹіж’’дәҶдёҖең°пјҢвҖңжҳЁе„ҝдёӘйӣЁеҒңдҪ е°ұеңЁиҝҷиҪ¬жӮ пјҢд»Ҡе„ҝеҸҲжқҘпјҹеҪ“иҖҒеЁҳзһҺпјҹвҖқ
еҘ№дёҫеҲҖе°ұз ҚгҖӮ
иҙ§йғҺжҠ¬иҮӮж јжҢЎпјҢиў–еӯҗиў«еҲ’ејҖдёҖйҒ“еҸЈеӯҗпјҢйңІеҮәйҮҢйқўдёҖеұӮй»‘еёғгҖӮйӮЈй»‘еёғдёҠз»ЈзқҖжүӯжӣІзҡ„з¬Ұж–ҮпјҢдёҖй—ӘеҚізҒӯгҖӮ
еҲҖй”Ӣж“ҰзқҖд»–иғіиҶҠиҝҮеҺ»пјҢжӯЈе·§еҲ®еҲ°з“·з“¶гҖӮ瓶еӯҗиҗҪең°пјҢзўҺдәҶпјҢжөҒеҮәзҡ„иЎҖеҪ“еңәеҶ’иө·з»ҝзҒ«пјҢйЎәзқҖеә•еә§еҫҖдёҠзҲ¬гҖӮ
зҺӢе®Ҳд»ҒжҠ¬жүӢпјҢжҺҢеҝғеҗ‘еүҚгҖӮ
дёҖдёӘвҖңжӯЈвҖқеӯ—еҮӯз©әжө®зҺ°пјҢеҚҠеҜёй«ҳпјҢйҮ‘е…үеҮқжҲҗпјҢдёҚе“Қд№ҹдёҚзӮёпјҢе°ұиҝҷд№ҲеҺӢдёӢеҺ»гҖӮз»ҝзҒ«вҖңе—ӨвҖқең°дёҖеЈ°зҶ„дәҶпјҢеғҸиў«ж°ҙжөҮйҖҸзҡ„зӮӯгҖӮ
иҙ§йғҺжғіи·‘гҖӮ
зҺӢе®Ҳд»ҒжІЎиҝҪпјҢеҸӘзӣҜзқҖжңЁеғҸгҖӮ
йӮЈз»ҝзҒ«иҷҪзҒӯпјҢеҸҜеә•еә§дёҠзҡ„иЎҖе·Із»Ҹжё—иҝӣеҺ»еҮ еҲҶпјҢжңЁзә№йҮҢжө®еҮәз»Ҷе°Ҹй»‘зәҝпјҢеғҸиҷ«еӯҗеңЁзҲ¬гҖӮжӣҙжҖӘзҡ„жҳҜпјҢжңЁеғҸзҡ„зңјзқӣдҪҚзҪ®пјҢеҺҹжң¬жҳҜеҲ»еҮәжқҘзҡ„еҮ№з—•пјҢжӯӨеҲ»з«ҹеҫ®еҫ®жіӣеҮәдёҖзӮ№е№Ҫе…үгҖӮ
вҖңе®ғиҰҒеҠЁгҖӮвҖқиөөеҜЎеҰҮдҪҺеЈ°йҒ“гҖӮ
вҖңдёҚжҳҜе®ғиҰҒеҠЁгҖӮвҖқзҺӢе®Ҳд»Ғз«ҷзӣҙпјҢвҖңжҳҜжңүдәәжғіи®©е®ғеҸҳгҖӮвҖқ
д»–иө°еҲ°жңЁеғҸеүҚпјҢеҸіжүӢжҢүеңЁеә•еә§иғҢйқўгҖӮйӮЈйҮҢиҝҳи—ҸзқҖвҖңж–ҮеңЈвҖқдёӨдёӘеӯ—пјҢиў«жіҘе·ҙзӣ–зқҖпјҢжІЎдәәжҸҗпјҢд№ҹжІЎдәәж“ҰгҖӮ
д»–жҺҢеҝғеҸ‘зғӯпјҢй»ҳеҝөгҖҠж–Үе®«зҜҮгҖӢйҮҢзҡ„еҸҘеӯҗпјҢдёҚжҳҜжҲҳжі•пјҢжҳҜеј•жі•гҖӮеј•зҡ„жҳҜдәәеҝғйҮҢзҡ„еҝөпјҢдёҚжҳҜеӨ©ең°йҮҢзҡ„ж°”гҖӮ
вҖңдҪ иҰҒжҳҜзңҹжүҝдәҶж„ҝеҠӣпјҢе°ұиҮӘе·ұжё…дәҶи„ҸдёңиҘҝгҖӮвҖқ
иҜқиҗҪдёҚеҲ°дёүжҒҜпјҢејӮеҸҳзӘҒз”ҹгҖӮ
жңЁеғҸеҸҢзӣ®дҪҚзҪ®йҮ‘е…үжҡҙж¶ЁпјҢдёҚжҳҜзҒ«з„°пјҢд№ҹдёҚжҳҜдә®е…үпјҢе°ұжҳҜзәҜзІ№зҡ„йҮ‘гҖӮйӮЈе…үдёҖеҮәпјҢеә•еә§дёҠзҡ„й»‘зәҝвҖңеҗұвҖқең°еҸ«дәҶдёҖеЈ°пјҢеғҸзғ«зҶҹзҡ„иҡҜиҡ“пјҢзј©еӣһиЎҖиҝ№йҮҢгҖӮз»ҝзҒ«ж®ӢдҪҷд№ҹиў«еҗёиҝҮеҺ»пјҢиҪ¬зңјеҢ–дҪңзј•зј•зҷҪж°”пјҢеҚҮеҲ°еҚҠз©әпјҢеҮқжҲҗдёӨдёӘеӯ—пјҡвҖңзҹҘиЎҢвҖқгҖӮ
еӯ—дёҖзҺ°пјҢз«ӢеҲ»ж•ЈдәҶгҖӮ
иҙ§йғҺзҳ«еңЁең°дёҠпјҢжҠ–еҫ—еғҸзӯӣзі гҖӮ
иөөеҜЎеҰҮжҸҗеҲҖдёҠеүҚпјҢдёҖи„ҡиё©дҪҸд»–жүӢи…•пјҢвҖңиҜҙпјҒи°ҒжҙҫдҪ жқҘзҡ„пјҹеҖ’зҡ„д»Җд№ҲпјҹвҖқ
иҙ§йғҺе’¬зүҷдёҚиҜӯгҖӮ
зҺӢе®Ҳд»ҒеҚҙ笑дәҶдёӢпјҢвҖңд»–дёҚдјҡиҜҙпјҢд№ҹдёҚж•ўиҜҙгҖӮвҖқ
д»–д»ҺжҖҖйҮҢеҸ–еҮәеўЁзҺүзүҢпјҢжҢӮеңЁиҙ§йғҺи„–еӯҗдёҠгҖӮвҖңзҹҘиЎҢвҖқдәҢеӯ—иҙҙзқҖеҜ№ж–№зҡ®иӮӨпјҢеҫ®е…үзј“зј“жё—е…ҘгҖӮиҙ§йғҺиә«дҪ“дёҖеғөпјҢе–үе’ҷйҮҢеҸ‘еҮәвҖңе’Ҝе’ҜвҖқеЈ°пјҢеғҸжҳҜжңүд»Җд№ҲдёңиҘҝеңЁдҪ“еҶ…иў«еҺӢдҪҸдәҶгҖӮ
вҖңжңүиӣҠгҖӮвҖқзҺӢе®Ҳд»Ғ收еӣһзүҢеӯҗпјҢвҖңи—ҸеңЁиҲҢж №дёӢйқўпјҢдёҖе’¬е°ұжҜ’еҸ‘гҖӮвҖқ
иөөеҜЎеҰҮеҶ·з¬‘пјҢвҖңйӮЈжҲ‘зҺ°еңЁе°ұжҺ°ејҖд»–еҳҙпјҢжҠҠжҜ’зүҷжҠ еҮәжқҘгҖӮвҖқ
вҖңдёҚз”ЁгҖӮвҖқзҺӢе®Ҳд»Ғж‘ҮеӨҙпјҢвҖңд»–дјҡйҶ’гҖӮзӯүд»–иҮӘе·ұејҖеҸЈгҖӮвҖқ
д»–иҜҙе®ҢпјҢзӣҳиҶқеқҗдёӢпјҢиғҢйқ жңЁеғҸеә•еә§гҖӮеӨңйЈҺиө·дәҶпјҢеҗ№еҫ—йҰҷзӮүиҫ№зҡ„йҮҺиҠұиҪ»иҪ»жҷғгҖӮйӮЈиҠұжҳҜе°Ҹеӯ©ж—©дёҠж”ҫзҡ„пјҢи”«дәҶд№ҹжІЎдәә收гҖӮ
иөөеҜЎеҰҮз«ҷеңЁд»–ж—Ғиҫ№пјҢиҸңеҲҖжЁӘеңЁиҶқдёҠпјҢеҲҖйқўжҳ зқҖжңҲе…үгҖӮ
дёӨдәәи°ҒйғҪжІЎиҜҙиҜқгҖӮ
иҝҮдәҶдёҚзҹҘеӨҡд№…пјҢиҙ§йғҺжҠҪжҗҗдәҶдёҖдёӢпјҢзқҒзңјгҖӮ
д»–зңјзҘһж¶Јж•ЈпјҢеҳҙе”Үе“Ҷе—ҰпјҢ第дёҖеҸҘиҜқеҚҙжҳҜпјҡвҖңжҲ‘дёҚжҳҜиҙ§йғҺвҖҰвҖҰжҲ‘жҳҜеҺҝиЎҷзҡ„е·®еҪ№пјҢдёғж—ҘеүҚиў«и°ғжқҘйҖҒзІ®гҖӮвҖқ
зҺӢе®Ҳд»ҒзӮ№еӨҙпјҢвҖң继з»ӯгҖӮвҖқ
вҖңеҺҝд»ӨеӨ§дәәиҜҙпјҢйҫҷеңәй©ҝйӮӘж°”йҮҚпјҢз”ҹзҘ дёҚиғҪз«ӢгҖӮи®©жҲ‘еҒ·еҒ·жҜҒдәҶжңЁеғҸпјҢеҶҚж”ҫжҠҠзҒ«пјҢиҜҙжҳҜйӣ·еҠҲзҡ„вҖҰвҖҰвҖқд»–еЈ°йҹіеҸ‘йўӨпјҢвҖңеҸҜжҲ‘жҳЁжҷҡжўҰи§ҒдёҖзҫӨеӯ©еӯҗи·ӘеңЁз”°йҮҢе“ӯпјҢиҜҙжІЎжңүе…Ҳз”ҹ他们全еҫ—йҘҝжӯ»вҖҰвҖҰжҲ‘дёҚж•ўеҠЁжүӢпјҢеҸҜд»ҠеӨ©вҖҰвҖҰжңүдәәеңЁжҲ‘ж°ҙйҮҢдёӢдәҶиҚҜпјҢжҲ‘дёҖйҶ’жқҘе°ұеңЁи·ҜдёҠдәҶвҖҰвҖҰвҖқ
вҖңи°Ғз»ҷзҡ„иҚҜпјҹвҖқиөөеҜЎеҰҮйҖјй—®гҖӮ
вҖңдёҚзҹҘйҒ“вҖҰвҖҰз©ҝй»‘иўҚпјҢи„ёи’ҷзқҖвҖҰвҖҰд»–з»ҷдәҶжҲ‘иҝҷ瓶иЎҖпјҢиҜҙж¶ӮдёҠеҺ»пјҢжңЁеғҸе°ұдјҡиЈӮејҖеҶ’й»‘зғҹпјҢзҷҫ姓еҗ“и·‘дәҶпјҢиҮӘ然жӢҶеәҷгҖӮвҖқ
зҺӢе®Ҳд»ҒзӣҜзқҖд»–пјҢвҖңдҪ дҝЎеҗ—пјҹвҖқ
иҙ§йғҺж‘ҮеӨҙпјҢвҖңжҲ‘дёҚдҝЎгҖӮеҸҜжҲ‘жҺ§еҲ¶дёҚдәҶиҮӘе·ұгҖӮе°ұеғҸвҖҰвҖҰжңүдәәеңЁжҲ‘и„‘еӯҗйҮҢиҜҙиҜқгҖӮвҖқ
зҺӢе®Ҳд»ҒжІүй»ҳзүҮеҲ»пјҢеҝҪ然问пјҡвҖңдҪ жўҰи§Ғзҡ„еӯ©еӯҗпјҢй•ҝд»Җд№Ҳж ·пјҹвҖқ
вҖңдёҖдёӘе°Ҹз”·еӯ©пјҢз©ҝиЎҘдёҒиЈӨпјҢе·Ұи„ҡе°‘дёӘйһӢеёҰвҖҰвҖҰд»–жҠ¬еӨҙзңӢжҲ‘пјҢиҜҙвҖҳдҪ д№ҹжҳҜзҲ№еЁҳе…»зҡ„пјҢеҮӯд»Җд№Ҳе®іеҘҪдәәвҖҷгҖӮвҖқ
зҺӢе®Ҳд»Ғй—ӯдәҶдёӢзңјгҖӮ
д»–зҹҘйҒ“жҳҜи°Ғжүҳзҡ„жўҰгҖӮдёҚжҳҜй¬јпјҢд№ҹдёҚжҳҜзҘһпјҢжҳҜиҝҷзүҮең°йҮҢеҲҡй•ҝеҮәжқҘзҡ„еҝөгҖӮ
вҖңдҪ жІЎеҒҡй”ҷгҖӮвҖқд»–зқҒејҖзңјпјҢвҖңзҺ°еңЁеӣһеҺ»пјҢе‘ҠиҜүеҺҝд»ӨпјҢз”ҹзҘ дёҚжӢҶпјҢжңЁеғҸдёҚжҜҒгҖӮиӢҘд»–еҶҚжҙҫдәәжқҘпјҢдёӢж¬Ўе°ұдёҚеҸӘжҳҜеҰ–иЎҖеҸҚеҷ¬дәҶгҖӮвҖқ
иҙ§йғҺж„ЈдҪҸпјҢвҖңжӮЁвҖҰвҖҰдёҚжқҖжҲ‘пјҹвҖқ
вҖңдҪ жҳҜдәәпјҢдёҚжҳҜеҰ–гҖӮвҖқзҺӢе®Ҳд»Ғз«ҷиө·иә«пјҢвҖңеӣһеҺ»еҘҪеҘҪжҙ»зқҖпјҢеҲ«еҝҳдәҶжўҰйҮҢйӮЈеҸҘиҜқгҖӮвҖқ
иөөеҜЎеҰҮзҡұзңүпјҢвҖңе°ұиҝҷд№Ҳж”ҫд»–иө°пјҹвҖқ
вҖңз•ҷзқҖд»–пјҢжҜ”жқҖдәҶжңүз”ЁгҖӮвҖқзҺӢе®Ҳд»ҒзңӢзқҖиҝңеӨ„еҺҝиЎҷж–№еҗ‘пјҢвҖң他们жҖ»дјҡеҶҚжқҘгҖӮзӯүдёӢж¬ЎпјҢжҲ‘们е°ұиғҪйЎәи—Өж‘ёз“ңгҖӮвҖқ
иөөеҜЎеҰҮе“јдәҶеЈ°пјҢжҠҠиҸңеҲҖжҸ’еӣһи…°й—ҙгҖӮ
иҙ§йғҺзҲ¬иө·жқҘпјҢи…ҝиҪҜеҫ—иө°дёҚеҠЁпјҢжү¶зқҖж ‘е№ІдёҖжӯҘжӯҘжҢӘеҗ‘жқ‘еҸЈгҖӮиө°еҲ°дёҖеҚҠпјҢзӘҒ然еӣһеӨҙгҖӮ
вҖңе…Ҳз”ҹпјҒвҖқд»–е–ҠдәҶдёҖеЈ°гҖӮ
зҺӢе®Ҳд»ҒжІЎеӣһеӨҙгҖӮ
вҖңйӮЈз“¶иЎҖвҖҰвҖҰжҳҜд»ҺеҢ—иҫ№жқҘзҡ„гҖӮйҖҒиЎҖзҡ„дәәпјҢе·ҰжүӢзјәдәҶж №жүӢжҢҮпјҢиў–еҸЈз»ЈзқҖзӢјеӨҙгҖӮвҖқ
иҜқйҹіиҗҪдёӢпјҢдәәе·Іж¶ҲеӨұеңЁеӨңиүІйҮҢгҖӮ
зҺӢе®Ҳд»Ғз«ҷзқҖжІЎеҠЁгҖӮ
иөөеҜЎеҰҮиө°иҝҮжқҘпјҢвҖңеҢ—иҫ№вҖҰвҖҰжҳҜиӢҚйӘЁзҡ„ең°зӣҳпјҹвҖқ
вҖңдёҚжӯўгҖӮвҖқзҺӢе®Ҳд»ҒдҪҺеӨҙзңӢжүӢпјҢвҖңеҰ–еҗҺзҡ„дәәпјҢд№ҹе–ңж¬ўз”Ёиҝҷз§ҚиЎҖгҖӮвҖқ
д»–жҠ¬иө·жүӢжҺҢпјҢжҢҮе°–жңүдёҖйҒ“зәўз—•пјҢжҳҜеҲҡжүҚзў°еҰ–иЎҖж—¶з•ҷдёӢзҡ„гҖӮзәўз—•иҫ№зјҳеҫ®еҫ®еҸ‘зҙ«пјҢеғҸжҳҜиҰҒжү©ж•ЈгҖӮ
иөөеҜЎеҰҮзңӢи§ҒдәҶпјҢдјёжүӢеҺ»жҺҸиҚҜзҪҗпјҢвҖңжҲ‘з»ҷдҪ дёҠзӮ№иҚҜгҖӮвҖқ
вҖңдёҚз”ЁгҖӮвҖқд»–жҠҠжүӢ收иҝӣиў–еӯҗпјҢвҖңиҝҷзӮ№дёңиҘҝпјҢиҝҳдјӨдёҚдәҶдәәгҖӮвҖқ
еҸҜд»–зҹҘйҒ“пјҢиҝҷдёҚжҳҜз»“жқҹгҖӮ
жҳҜејҖе§ӢгҖӮ
з”ҹзҘ йқҷз«ӢпјҢжңЁеғҸи„ёдёҠзҡ„е…үеҪұеҝҪжҳҺеҝҪжҡ—гҖӮйҰҷзӮүйҮҢйӮЈзӮ№зҒ°иў«йЈҺеҗ№ж•ЈпјҢеҮ зІ’зҒ«жҳҹйЈҳиө·жқҘпјҢиҗҪеңЁеә•еә§иғҢйқўпјҢжӯЈеҘҪзӣ–дҪҸвҖңж–ҮеңЈвҖқдәҢеӯ—гҖӮ
зҺӢе®Ҳд»ҒеқҗеңЁеҺҹең°пјҢжІЎеҶҚиҜҙиҜқгҖӮ
иөөеҜЎеҰҮе®ҲеңЁдёҖж—ҒпјҢжүӢдёҖзӣҙжҗӯеңЁеҲҖжҹ„дёҠгҖӮ
еӨңжӣҙж·ұдәҶпјҢжқ‘еӨ–е°Ҹи·ҜдёҠпјҢдёҖеҸӘд№ҢйёҰжү‘жЈұжЈұйЈһиө·пјҢзҝ…иҶҖжӢҚеҮәжІүй—·еЈ°е“Қ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ө¶е°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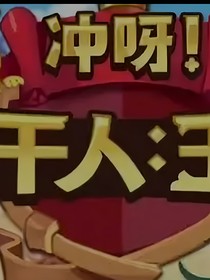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йҘје№ІдәӢи®°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еңЁејӮз•Ңзә№д№қйҫҷжӢүжЈә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Ҫ’е°ҳеҲӣдё–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家з”өи§ҶжңәиғҪз©ҝи¶ҠдёҮз•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