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з« пјҡзңјзәҝз»ҲеҖ’жҲҲпјҢж–ҮдјҡеҠҝеҠӣжү©
еӨ©еҲҡдә®пјҢжҹҙжҲҝзҡ„й—Ёиў«жҺЁејҖгҖӮ
зҺӢе®Ҳд»Ғиө°дәҶиҝӣеҺ»пјҢиў–дёӯиҚҜзҪҗиҪ»иҪ»жҷғдәҶдёҖдёӢгҖӮзңјзәҝиҝҳеқҗеңЁең°дёҠпјҢеҸҢжүӢжҠұзқҖиҶқзӣ–пјҢи„ёиүІеҸ‘йқ’пјҢеҳҙе”Үе№ІиЈӮгҖӮд»–жҠ¬еӨҙзңӢдәҶдёҖзңјпјҢеҸҲиҝ…йҖҹдҪҺдёӢеӨҙгҖӮ
вҖңдҪ иҜҙиҝҮпјҢеҸӘиҰҒжҲ‘иҜҙзңҹиҜқпјҢе°ұз»ҷжҲ‘дёүеӨ©е‘ҪгҖӮвҖқд»–еЈ°йҹіжІҷе“‘пјҢвҖңжҲ‘зҺ°еңЁиҜҙгҖӮвҖқ
зҺӢе®Ҳд»ҒжІЎиҜҙиҜқпјҢжҠҠиҚҜзҪҗж”ҫеңЁж—Ғиҫ№зҡ„жңЁжЎҢдёҠпјҢд»ҺжҖҖйҮҢеҸ–еҮәйӮЈеҚҠеқ—зӢјйҰ–д»ӨзүҢпјҢж”ҫеңЁжЎҲдёҠгҖӮд»ӨзүҢдёҠзҡ„иЈӮз—•еңЁжҷЁе…үдёӢжҳҫеҫ—ж јеӨ–жё…жҷ°гҖӮ
вҖңдҪ зҹҘйҒ“иҝҷжҳҜд»Җд№ҲгҖӮвҖқд»–иҜҙгҖӮ
зңјзәҝе–үз»“еҠЁдәҶеҠЁпјҢвҖңжҳҜиӢҚйӘЁзҡ„и°ғе…өд»ӨвҖҰвҖҰзўҺдәҶдёҖеҚҠпјҢеҸҰдёҖеҚҠеңЁеҺҝд»ӨжүӢйҮҢгҖӮвҖқ
вҖң继з»ӯгҖӮвҖқ
вҖңжҲ‘еҘүе‘ҪеңЁдёғдёӘжқ‘еӯҗеҹӢдәҶдёңиҘҝгҖӮвҖқд»–й—ӯдёҠзңјпјҢвҖңдә•еә•гҖҒзҘ е ӮгҖҒзІ®д»“вҖҰвҖҰйғҪеҹӢдәҶеҰ–еҚөгҖӮжҜҸжңҲеҚҒдә”пјҢиЎҖжңҲеҚҮз©әпјҢе®ғ们е°ұдјҡз ҙеЈіпјҢй’»еҮәжҜ’иҷ«пјҢдё“е’¬иҜ»д№Ұдәәзҡ„еӨҙйў…гҖӮвҖқ
зҺӢе®Ҳд»ҒжүӢжҢҮиҪ»зӮ№жЎҢйқўпјҢвҖңи°Ғи®©дҪ еҹӢзҡ„пјҹвҖқ
вҖңеҺҝд»Өе’ҢдёҖдёӘй»‘иўҚдәәгҖӮвҖқзңјзәҝе–ҳдәҶеҸЈж°”пјҢвҖң他们иҰҒеңЁж–ҮдјҡејҖи®ІйӮЈеӨ©еҠЁжүӢпјҢдёүзҷҫеҚөеҗҢж—¶зҲҶејҖпјҢж–Үж°”йҖҶеҶІпјҢеӯ©еӯҗ们иҜ»зқҖд№Ұе°ұдјҡз–ҜжҺүпјҢеҸҳжҲҗиЎҢе°ёиө°иӮүгҖӮвҖқ
зҺӢе®Ҳд»Ғз«ҷиө·иә«пјҢиө°еҲ°д»–йқўеүҚпјҢвҖңдҪ жҳЁеӨңжўҰйҮҢеҗ¬еҲ°зҡ„йӮЈеҸҘиҜқвҖ”вҖ”вҖҳзҒ«иҰҒд»Һж №зғ§вҖҷпјҢиҝҳи®°еҫ—еҗ—пјҹвҖқ
зңјзәҝзӮ№еӨҙпјҢвҖңи®°еҫ—гҖӮвҖқ
вҖңйӮЈдҪ зҺ°еңЁеҺ»дј иҝҷеҸҘиҜқгҖӮвҖқ
вҖңеҸҜ他们иҰҒжҳҜдёҚдҝЎе‘ўпјҹвҖқ
вҖң他们дјҡдҝЎгҖӮвҖқзҺӢе®Ҳд»ҒзӣҜзқҖд»–пјҢвҖңеӣ дёәдҪ е·Із»Ҹжӯ»дәҶгҖӮжӯ»еңЁжҳЁеӨңзҡ„жҙ»зҘӯйҳөйҮҢгҖӮжІЎдәәзҹҘйҒ“дҪ иҝҳжҙ»зқҖпјҢд№ҹжІЎдәәзҹҘйҒ“дҪ и§ҒиҝҮжҲ‘гҖӮвҖқ
зңјзәҝжІүй»ҳдәҶдёҖдјҡе„ҝпјҢеҝҪ然笑дәҶпјҢвҖңе…Ҳз”ҹвҖҰвҖҰжӮЁдёҚжҖ•жҲ‘еӣһеӨҙеҶҚйӘ—жӮЁпјҹвҖқ
вҖңжҖ•гҖӮвҖқзҺӢе®Ҳд»ҒиҜҙпјҢвҖңжүҖд»ҘжҲ‘еҺӢдҪҸдәҶдҪ дҪ“еҶ…зҡ„иӣҠгҖӮдҪ иӢҘиҜҙи°ҺпјҢе®ғдјҡе…Ҳе’¬з©ҝдҪ зҡ„еҝғи„ҸгҖӮвҖқ
зңјзәҝи„ёдёҠзҡ„笑еғөдҪҸдәҶгҖӮ
зҺӢе®Ҳд»ҒиҪ¬иә«еҫҖеӨ–иө°пјҢвҖңеҺ»еҗ§гҖӮеӨ©дә®еүҚпјҢжҠҠиҜҘиҜҙзҡ„иҜқиҜҙе®ҢгҖӮеӨ©дә®еҗҺпјҢжҲ‘иҰҒзңӢи§Ғдёғжқ‘зҡ„дәәжқҘгҖӮвҖқ
й—Ёе…ідёҠпјҢеҸӘеү©зңјзәҝдёҖдёӘдәәеқҗеңЁеұӢйҮҢгҖӮд»–дҪҺеӨҙзңӢзқҖиҮӘе·ұзҡ„жүӢпјҢжүӢжҢҮеҫ®еҫ®еҸ‘жҠ–гҖӮиҝҮдәҶеҫҲд№…пјҢд»–ж…ўж…ўз«ҷиө·жқҘпјҢиө°еҗ‘й—ЁеҸЈгҖӮ
еӨ–йқўйҳіе…үз…§иҝӣжқҘпјҢеҲәеҫ—д»–зқҒдёҚејҖзңјгҖӮ
---
дёҚеҲ°дёӨдёӘж—¶иҫ°пјҢжқ‘еҸЈжқҘдәҶдәәгҖӮ
е…ҲжҳҜдёүдёӘй•ҝиҖҒжӢ„зқҖжӢҗжқ–иө°жқҘпјҢиә«еҗҺи·ҹзқҖеҚҒеҮ дёӘйқ’е№ҙпјҢжүӢйҮҢжӢҝзқҖй”„еӨҙгҖҒжүҒжӢ…гҖӮжҺҘзқҖеҸҲжңүеӣӣжӢЁдәәд»ҺдёҚеҗҢж–№еҗ‘иө¶жқҘпјҢиЎЈиЎ«з ҙж—§пјҢи„ҡдёҠжІҫжіҘпјҢдҪҶзңјзҘһйғҪдёҖж ·еқҡе®ҡгҖӮ
зҺӢе®Ҳд»Ғз«ҷеңЁд№Ұйҷўй—ЁеүҚпјҢзңӢзқҖ他们иө°иҝ‘гҖӮ
жңҖиҖҒзҡ„йӮЈдёӘй•ҝиҖҒи·ӘдәҶдёӢжқҘпјҢйўқеӨҙиҙҙең°пјҢвҖңе…Ҳз”ҹж•‘жҲ‘们пјҒжқ‘йҮҢжңҖиҝ‘еӨңйҮҢжҖ»жңүжҖӘеЈ°пјҢеӯ©еӯҗеҒҡеҷ©жўҰпјҢиҖҒдәәеҗҗй»‘иЎҖпјҢжҳҜдёҚжҳҜвҖҰвҖҰзңҹжҳҜеҰ–еҚөдҪңзҘҹпјҹвҖқ
зҺӢе®Ҳд»ҒжІЎзӯ”иҜқпјҢиҪ¬иә«еҜ№иә«иҫ№дәәиҜҙпјҡвҖңжҠ¬зў‘гҖӮвҖқ
дёӨеқ—й•ҮйӮӘзў‘зҡ„зўҺзүҮиў«жҗ¬дәҶеҮәжқҘпјҢдёҠйқўиҝҳжІҫзқҖй»‘иүІй»Ҹж¶ІгҖӮзҺӢе®Ҳд»ҒжҠҪеҮәжЎғжңЁеү‘пјҢеңЁз©әдёӯеҲ’дәҶеҮ йҒ“пјҢзўҺзүҮзӘҒ然йңҮеҠЁпјҢеҮ зүҮжјҶй»‘зҡ„еЈід»ҺиЈӮзјқдёӯжҺүиҗҪпјҢиҗҪең°еҚізҮғпјҢеҶ’еҮәи…ҘиҮӯй»‘зғҹгҖӮ
вҖңиҝҷе°ұжҳҜеҰ–еҚөгҖӮвҖқд»–иҜҙпјҢвҖңдҪ 们еёҰеӣһеҺ»пјҢеҹӢеңЁжқ‘еҸЈгҖӮиӢҘжңүејӮеҠЁпјҢзҹідёҠж–Үеӯ—дјҡдә®гҖӮвҖқ
й•ҝиҖҒ们дёҖдёӘдёӘдёҠеүҚеҸ©йҰ–гҖӮ
зҺӢе®Ҳд»Ғжү¶иө·жңҖиҖҒзҡ„йӮЈдёӘпјҢвҖңжҲ‘дёҚ收еҫ’пјҢд№ҹдёҚз«Ӣе®—гҖӮдҪ 们иҰҒзҡ„дёҚжҳҜеёҲзҲ¶пјҢжҳҜиғҪжҠӨдҪҸ家дәәзҡ„жң¬дәӢгҖӮвҖқ
вҖңйӮЈжҲ‘们жҖҺд№ҲеҠһпјҹвҖқжңүдәәй—®гҖӮ
вҖңиҜҶеӯ—гҖӮвҖқзҺӢе®Ҳд»ҒиҜҙпјҢвҖңиҜ»д№ҰгҖӮеҶҷж–Үз« гҖӮ用笔жқҶеӯҗеҪ“еҲҖжһӘгҖӮвҖқ
д»–иҪ¬иә«иө°иҝӣйҷўеҶ…пјҢзүҮеҲ»еҗҺжҚ§еҮәдёғеқ—йқ’зҹіжқҝпјҢжҜҸеқ—дёҠйғҪеҲ»зқҖдёүзҜҮж–Үз« гҖӮ
вҖңиҝҷжҳҜжҲ‘еҶҷзҡ„гҖҠй©ұйӮӘдёүзҜҮгҖӢгҖӮдёҖзҜҮи®ІеҰӮдҪ•иҫЁеҰ–ж–ҮпјҢдёҖзҜҮж•ҷжҖҺд№Ҳз”Ёж–Үж°”жҠӨеҝғпјҢ第дёүзҜҮжҳҜз»ҷеӯ©еӯҗзҡ„еҗҜи’ҷе’’гҖӮжӢҝеӣһеҺ»пјҢдёҖе®¶дј дёҖ家пјҢдёҖдәәж•ҷдёҖдәәгҖӮвҖқ
йқ’е№ҙ们жҺҘиҝҮзҹіжқҝпјҢеғҸжҺҘеңЈзү©дёҖж ·жҠұеңЁжҖҖйҮҢгҖӮ
вҖңд»Һд»ҠеӨ©иө·пјҢжҜҸдёӘжқ‘и®ҫдёҖдёӘж–Үи§’гҖӮвҖқзҺӢе®Ҳд»ҒиҜҙпјҢвҖңжҜҸеӨ©жҷҡдёҠпјҢз”ұиҜҶеӯ—зҡ„дәәйўҶиҜ»дёҖзҜҮгҖӮиҜ»е®ҢиҰҒзӮ№дёҖзӣҸжІ№зҒҜпјҢзҒҜдёҚзҒӯпјҢж–Үж°”е°ұдёҚж•ЈгҖӮвҖқ
вҖңжҲ‘们еҗ¬жӮЁзҡ„пјҒвҖқдёҖдёӘе№ҙиҪ»дәәе–ҠгҖӮ
вҖңжҲ‘дёҚжҳҜдҪ 们зҡ„дё»гҖӮвҖқзҺӢе®Ҳд»Ғж‘ҮеӨҙпјҢвҖңж–ҮйҒ“жүҚжҳҜгҖӮдҪ 们жӢңзҡ„дёҚжҳҜжҲ‘пјҢжҳҜиҮӘе·ұдёҚиӮҜдҪҺеӨҙзҡ„и„ҠжўҒгҖӮвҖқ
дәәзҫӨйқҷдәҶзүҮеҲ»пјҢеҝҪ然йҪҗеЈ°й«ҳе‘јпјҡвҖңж„ҝйҡҸе…Ҳз”ҹпјҢе®Ҳж–ҮжҠӨж°‘пјҒвҖқ
еЈ°йҹійңҮеҫ—еұӢжӘҗиҗҪзҒ°гҖӮ
зҺӢе®Ҳд»Ғз«ҷеңЁеҸ°йҳ¶дёҠпјҢзңӢзқҖзңјеүҚиҝҷдәӣдәәпјҢжІЎжңү笑пјҢд№ҹжІЎжңүеҠЁгҖӮ
д»–зҹҘйҒ“пјҢиҝҷдёҚеҸӘжҳҜдёғдёӘжқ‘еӯҗзҡ„йҖүжӢ©пјҢжҳҜж–ҮзҒ«з»ҲдәҺзғ§еҲ°дәҶж°‘й—ҙгҖӮ
---
еӨңж·ұдәҶгҖӮ
жҹҙжҲҝйҮҢзӮ№дәҶзӣҸе°ҸжІ№зҒҜпјҢзңјзәҝеқҗеңЁжІҷзӣҳеүҚпјҢжүӢйҮҢжҸЎзқҖзӮӯ笔гҖӮжІҷзӣҳдёҠз”»зқҖдёғжқ‘ең°еҪўпјҢд»–дёҖ笔дёҖ笔жҸҸзқҖпјҢжүӢдёҖзӣҙеңЁжҠ–гҖӮ
д»–зҹҘйҒ“пјҢеҸӘиҰҒжҠҠиҝҷдәӣдҪҚзҪ®з”»еҮәжқҘпјҢд»–е°ұзңҹзҡ„еӣһдёҚдәҶеӨҙдәҶгҖӮ
笔尖еҒңеңЁз¬¬дёүдёӘжқ‘еӯҗзҡ„дә•еҸЈдҪҚзҪ®пјҢд»–еҝҪ然еҒңдёӢпјҢжҠ¬еӨҙзңӢеҗ‘зӘ—еӨ–гҖӮ
зҺӢе®Ҳд»Ғз«ҷеңЁжӘҗдёӢпјҢиғҢзқҖжүӢпјҢиҚҜзҪҗжҢӮеңЁи…°дҫ§пјҢеҪұеӯҗжӢүеҫ—еҫҲй•ҝгҖӮ
зңјзәҝе’¬дәҶе’¬зүҷпјҢ继з»ӯз”»гҖӮ
жңҖеҗҺдёҖеӨ„зІ®д»“ж Үи®°е®ҢпјҢд»–ж”ҫдёӢ笔пјҢж•ҙдёӘдәәзҳ«еңЁең°дёҠгҖӮ
е°ұеңЁиҝҷж—¶пјҢжІҷзІ’еҝҪ然еҠЁдәҶгҖӮ
еҺҹжң¬ж•Јд№ұзҡ„з»ҶжІҷиҮӘеҠЁиҒҡжӢўпјҢеңЁжІҷзӣҳдёӯеӨ®жӢјеҮәдёҖдёӘеӯ—вҖ”вҖ”и°ўгҖӮ
зңјзәҝж„ЈдҪҸпјҢдјёжүӢжғіеҺ»зў°пјҢжІҷзІ’еҚҙзә№дёқдёҚеҠЁгҖӮ
д»–жҠ¬еӨҙжңӣеҗ‘зӘ—еӨ–пјҢзҺӢе®Ҳд»Ғе·Із»ҸдёҚеңЁдәҶгҖӮ
дҪҶд»–зҹҘйҒ“пјҢйӮЈдёӘдәәдёҖе®ҡзңӢеҲ°дәҶгҖӮ
---
第дәҢеӨ©жё…жҷЁпјҢдёғдёӘжқ‘еӯҗеҗҢж—¶иЎҢеҠЁгҖӮ
жңүзҡ„жҢ–еҮәдә•еә•зҡ„й»‘еҚөпјҢз”ЁзҹізҒ°е°Ғеӯҳпјӣжңүзҡ„жӢҶдәҶзҘ е Ӯең°жқҝпјҢеҸ‘зҺ°еўҷеӨ№еұӮйҮҢи—ҸзқҖиӣҮзҡ®еҢ…иЈ№зҡ„йӮӘз¬ҰпјӣжңҖеҢ—иҫ№зҡ„жқ‘еӯҗз”ҡиҮіеңЁзІ®д»“ең°зӘ–жҢ–еҮәдёҖеҸЈйқ’й“ңжЈәпјҢйҮҢйқўе…ЁжҳҜжіЎеңЁиЎҖж°ҙйҮҢзҡ„е№јиҷ«гҖӮ
ж¶ҲжҒҜдј еӣһйҫҷеңәй©ҝпјҢзҺӢе®Ҳд»ҒжӯЈеңЁж•ҷеҮ дёӘеӯ©еӯҗеҶҷеӯ—гҖӮ
д»–еҗ¬е®ҢжұҮжҠҘпјҢеҸӘиҜҙдәҶдёҖеҸҘпјҡвҖңжҠҠгҖҠй©ұйӮӘдёүзҜҮгҖӢеҶҚжҠ„еҚҒд»ҪпјҢйҖҒеҲ°жӣҙиҝңзҡ„жқ‘гҖӮвҖқ
еј е®ҲжӢҷжҙҫжқҘзҡ„дәәй—®пјҡвҖңиҰҒдёҚиҰҒжҙҫдәәзӣҜзқҖзңјзәҝпјҹвҖқ
зҺӢе®Ҳд»Ғж‘ҮеӨҙпјҢвҖңдёҚз”ЁгҖӮд»–е·Із»ҸдёҚжҳҜзңјзәҝдәҶгҖӮвҖқ
вҖңйӮЈжҳҜд»Җд№ҲпјҹвҖқ
вҖңжҳҜ第дёҖдёӘйҶ’иҝҮжқҘзҡ„дәәгҖӮвҖқ
---
еӨңйҮҢпјҢзҺӢе®Ҳд»ҒзӢ¬иҮӘеқҗеңЁд№ҰжҲҝгҖӮ
жЎҢдёҠж‘ҶзқҖдёғеқ—зҹіжқҝзҡ„жӢ“жң¬пјҢеўҷдёҠжҢӮзқҖдёҖеј жүӢз»ҳең°еӣҫпјҢдёҠйқўж ҮзқҖеҚҒдёүдёӘзәўзӮ№гҖӮд»–зҹҘйҒ“пјҢиҝҷеҸӘжҳҜејҖе§ӢгҖӮ
еҰ–еҚөдёҚжӯўдёғдёӘпјҢжқ‘д№ҹдёҚжӯўдёғеә§гҖӮ
д»–жӢҝиө·иҚҜзҪҗе–қдәҶдёҖеҸЈпјҢж”ҫдёӢж—¶пјҢзҪҗеә•еҸ‘еҮәиҪ»еҫ®е“ҚеЈ°гҖӮ
иҝҷж—¶пјҢй—ЁеӨ–дј жқҘи„ҡжӯҘеЈ°гҖӮ
дёҖдёӘйқ’е№ҙи·‘иҝӣжқҘпјҢж»Ўи„ёз„ҰжҖҘпјҢвҖңе…Ҳз”ҹпјҒиҘҝеІӯжқ‘зҡ„дәәжқҘдәҶпјҢиҜҙ他们жқ‘еӯҰе ӮжҳЁжҷҡйҒӯдәҶиҙјпјҢи®Ід№үе…Ёиў«жҚўдәҶеҶ…е®№пјҒжңүдәәиҜ»дәҶд№ӢеҗҺпјҢеҪ“еңәжҠҪжҗҗпјҢеҸЈеҗҗзҷҪжІ«пјҒвҖқ
зҺӢе®Ҳд»Ғз«ҷиө·иә«пјҢжЎғжңЁеү‘жҠ“еңЁжүӢйҮҢгҖӮ
вҖңеёҰи·ҜгҖӮвҖқ
д»–иө°еҮәй—ЁпјҢеӨңйЈҺиҝҺйқўеҗ№жқҘпјҢиҚҜзҪҗеңЁи…°й—ҙиҪ»иҪ»жҷғдәҶдёҖдёӢгҖӮ
иЎ—и§’зҡ„жІ№зҒҜеҝҪжҳҺеҝҪжҡ—пјҢз…§зқҖд»–еүҚиЎҢзҡ„иә«еҪұ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ө¶е°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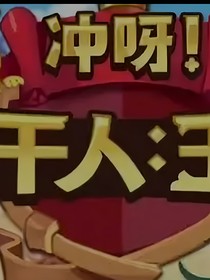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йҘје№ІдәӢи®°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еңЁејӮз•Ңзә№д№қйҫҷжӢүжЈә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Ҫ’е°ҳеҲӣдё–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家з”өи§ҶжңәиғҪз©ҝи¶ҠдёҮз•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