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з« пјҡж–ҮйӣЁж¶Ұж—ұз”°пјҢзҷҫ姓е»әз”ҹзҘ
иҚҜзҪҗд»Һиў–еҸЈж»‘иҗҪпјҢз ёеңЁжіҘйҮҢеҸ‘еҮәй—·е“ҚгҖӮ
зҺӢе®Ҳд»ҒдҪҺеӨҙзңӢдәҶзңјзўҺиЈӮзҡ„з“·зүҮпјҢжІЎеҺ»жҚЎгҖӮд»–еқҗеңЁй•ҮйӮӘзў‘еүҚпјҢжүӢж’‘зқҖиҶқзӣ–пјҢе‘јеҗёжҜ”е№іж—¶ж…ўдәҶдёҖжӢҚгҖӮжҳЁеӨңйӮЈеңәеҜ№еіҷиҖ—еҫ—еҺүе®іпјҢжҢҮе°–иҝҳж®Ӣз•ҷзқҖеҶҷиЎҖеӯ—ж—¶зҡ„涩ж„ҹгҖӮеҸҜең°еә•еҠЁйқҷжІЎеҒңпјҢж–Үи„үеғҸжқЎиӢҸйҶ’зҡ„иӣҮпјҢеңЁеңҹеұӮдёӢзј“зј“жёёиө°гҖӮ
д»–дјёжүӢж‘ёдәҶж‘ёжЎғжңЁеү‘зҡ„иЈӮз—•гҖӮ
еү‘иә«жё©зғӯпјҢдёҚжҳҜжқҖж°”пјҢжҳҜжҙ»ж°”гҖӮ
вҖңиҝҳиғҪеҶҚж’‘дёҖеӣһгҖӮвҖқд»–еҜ№иҮӘе·ұиҜҙгҖӮ
з«ҷиө·жқҘзҡ„ж—¶еҖҷи…ҝжңүзӮ№иҪҜпјҢдҪҶд»–жІЎжү¶дёңиҘҝгҖӮиө°еҲ°з”°иҫ№и№ІдёӢпјҢжҠ“дәҶжҠҠеңҹгҖӮеңҹжҳҜзҒ°зҷҪиүІзҡ„пјҢдёҖжҗ“е°ұж•ЈпјҢиҝһиҚүж №йғҪз„ҰдәҶгҖӮиҝңеӨ„еҮ жҲ·дәә家жӯЈжҠ¬ж°ҙжөҮең°пјҢдёҖи¶ҹжҺҘдёҖи¶ҹпјҢжЎ¶еә•жү“ж№ҝзҡ„йқўз§ҜиҝҳжІЎи„ҡеҚ°еӨ§гҖӮ
зҺӢе®Ҳд»ҒжҠҠжЎғжңЁеү‘жҸ’иҝӣең°зјқгҖӮ
йҮ‘е…үйЎәзқҖеү‘иә«еҫҖдёӢжё—пјҢдёҚеғҸжҳЁеӨңйӮЈж ·зӮёејҖпјҢиҖҢжҳҜж…ўж…ўй“әеұ•пјҢеғҸдәәжҸүејҖж”Ҙзҙ§зҡ„жӢіеӨҙгҖӮд»–й—ӯзңјпјҢй»ҳеҝөгҖҠж–Үе®«зҜҮгҖӢйҮҢйӮЈж®өвҖңеӨ©ең°д»ҒеҝғвҖқгҖӮиҝҷдёҚжҳҜжҲҳжі•пјҢжҳҜе…»жңҜгҖӮж–ҮзҒ«еӨӘзғҲдјҡдјӨдәәпјҢеҫ—и°ғжҲҗжё©жұӨпјҢжүҚиғҪж¶Ұзү©гҖӮ
еӨҙйЎ¶дә‘еұӮејҖе§ӢиҒҡгҖӮ
дёҚжҳҜй»‘дә‘пјҢжҳҜйқ’зҷҪиүІпјҢжө®еңЁеҚҠз©әеғҸдёҖеұӮи–„зәұгҖӮжқ‘йҮҢдәәжҠ¬еӨҙзңӢеӨ©пјҢжІЎдәәиҜҙиҜқгҖӮеүҚдёӨеӨ©еҲҡдёӢдәҶеңәйӣЁпјҢиҗҪең°е°ұе№ІпјҢиҝһдёӘж°ҙеҚ°йғҪжІЎз•ҷгҖӮиҝҷж¬Ўдә‘дёҚеҠЁпјҢд№ҹдёҚжү“йӣ·гҖӮ
зҺӢе®Ҳд»Ғе’¬з ҙжүӢжҢҮгҖӮ
д»–еңЁз©әдёӯеҲ’дәҶдёӨиЎҢеӯ—пјҡвҖңйЎәеӨ©д№Ӣж—¶пјҢеӣ ең°д№ӢеҲ©гҖӮвҖқеӯ—дёҖжҲҗпјҢз«ӢеҲ»еҢ–дҪңз»Ҷе°ҸйҮ‘зә№пјҢй’»иҝӣдә‘еә•гҖӮдёӢдёҖеҲ»пјҢйӣЁзӮ№иҗҪдёӢжқҘгҖӮ
дёҚжҳҜе“—е•Ұе•ҰйӮЈз§ҚпјҢжҳҜдёҖж»ҙдёҖж»ҙпјҢж…ўеҫ—еҫҲеҢҖгҖӮеҘҮжҖӘзҡ„жҳҜпјҢжҜҸйў—йӣЁзҸ йҮҢйғҪиЈ№зқҖеӯ—пјҢзұізІ’еӨ§е°ҸпјҢзңӢеҫ—жё…жё…жҘҡжҘҡвҖ”вҖ”жӯЈжҳҜгҖҠйҪҗж°‘иҰҒжңҜгҖӢйҮҢзҡ„ж®өиҗҪгҖӮ
иҖҒжқҺ第дёҖдёӘеҸҚеә”иҝҮжқҘгҖӮ
д»–жү”дәҶжүҒжӢ…пјҢи·ӘеңЁз”°йҮҢдјёжүӢжҺҘйӣЁгҖӮдёҖж»ҙиҗҪеңЁжҺҢеҝғпјҢеӯ—иҝ№дёҖй—ӘпјҢеҢ–жҲҗдёҖиӮЎжҡ–жөҒй’»иҝӣзҡ®иӮүгҖӮд»–зҢӣең°жҠ¬еӨҙпјҢзңӢи§ҒиҮӘ家йӮЈзүҮжһҜй»„зҡ„зЁ»иҢ¬жӯЈеңЁжҠҪз»ҝпјҢе«©иҠҪйЎ¶з ҙз„ҰеңҹпјҢдёҖеҜёдёҖеҜёеҫҖдёҠи№ҝгҖӮ
вҖңжҙ»дәҶпјҒвҖқд»–еҗјдәҶдёҖеЈ°гҖӮ
ж—Ғиҫ№еҮ дёӘеӯ©еӯҗж„ЈдҪҸпјҢжҺҘзқҖж’’и…ҝеҫҖ家跑гҖӮдёҖ家жҺҘдёҖ家ејҖй—ЁпјҢз”·еҘіиҖҒе°‘е…Ёж¶ҢеҲ°ең°еӨҙгҖӮжңүдәәжӢҝзў—жҺҘйӣЁпјҢжңүдәәи„ұдәҶйһӢиё©жіҘпјҢиҝҳжңүдёӘиҖҒеӨӘеӨӘзӣҙжҺҘи¶ҙеңЁең°дёҠпјҢиҖіжңөиҙҙзқҖең°йқўеҗ¬еҠЁйқҷгҖӮ
йӣЁдёӢдәҶдёҚеҲ°еҚҠдёӘж—¶иҫ°е°ұеҒңдәҶгҖӮ
еҸҜз”°йҮҢзҡ„еҸҳеҢ–и°ҒйғҪзңӢеҫ—и§ҒгҖӮеҺҹжң¬е№ІиЈӮзҡ„еңҹеҸҳеҫ—жқҫиҪҜпјҢзЁ»иӢ—й•ҝеҲ°е°Ҹи…ҝй«ҳпјҢз©—еӯҗиҷҪе°ҸеҚҙйҘұж»ЎеҸ‘дә®гҖӮиҸңең°йҮҢзҡ„з“ңи—ӨзҲ¬дәҶдёүе°әпјҢиұҶи§’жҢӮдәҶдёҖдёІгҖӮ
жқ‘дёңеӨҙдј жқҘе“ӯеЈ°гҖӮ
жҳҜдёӘжҠұзқҖеӯҷеӯҗзҡ„иҖҒеҰҮпјҢиҫ№е“ӯиҫ№зЈ•еӨҙпјҡвҖңе…Ҳз”ҹж•‘дәҶжҲ‘们е•ҠвҖҰвҖҰвҖқ
зҺӢе®Ҳд»Ғе·Із»Ҹиө°иҝӣз”°йҮҢгҖӮ
д»–и„ұдәҶйһӢпјҢиөӨи„ҡиё©еңЁжіҘдёҠпјҢејҜи…°жү¶иө·дёҖж Әиў«йЈҺеҗ№жӯӘзҡ„зҰҫиӢ—гҖӮиә«еҗҺдёҖзҫӨдәәи·ҹзқҖиҝӣжқҘпјҢжңүжғіи·Әзҡ„пјҢжңүжғіе–Ҡзҡ„пјҢйғҪиў«ж—Ғиҫ№зҡ„йӮ»еұ…жӢүдҪҸгҖӮ
вҖңеҲ«жӢңжҲ‘гҖӮвҖқд»–иҜҙпјҢвҖңдҪ 们иҮӘе·ұз§Қзҡ„ең°пјҢиҮӘе·ұжөҒзҡ„жұ—пјҢжүҚжҳҜзңҹеҠҹгҖӮвҖқ
жІЎдәәеҠЁгҖӮ
д»–зӣҙиө·иә«пјҢд»ҺжҖҖйҮҢж‘ёеҮәеҸҰдёҖдёӘе°ҸиҚҜзҪҗвҖ”вҖ”иҝҷжҳҜиөөеҜЎеҰҮд»Ҡж—©еЎһз»ҷд»–зҡ„пјҢйҮҢйқўиЈ…дәҶеҚҠзҪҗзЁҖзІҘгҖӮд»–жү“ејҖзӣ–еӯҗпјҢжҺҘдәҶзӮ№йӣЁж°ҙжҗ…дәҶжҗ…пјҢе–қдәҶдёҖеҸЈпјҢ然еҗҺйҖ’з»ҷиә«иҫ№зҡ„иҖҒеҶңгҖӮ
иҖҒеҶңе“Ҷе—ҰзқҖжүӢжҺҘиҝҮпјҢд»°еӨҙе–қдәҶгҖӮ
е‘Ёеӣҙзҡ„дәәиҝҷжүҚжқҫеҸЈж°”пјҢи„ёдёҠжңүдәҶз¬‘жЁЎж ·гҖӮ
еҪ“жҷҡпјҢзҺӢе®Ҳд»ҒеӣһеҲ°д№ҰйҷўгҖӮ
зҒҜиҝҳдә®зқҖпјҢжЎҢдёҠж‘ҠзқҖзәёгҖӮд»–жҸҗ笔еҶҷдәҶзҜҮгҖҠзҘҖи®®гҖӢпјҢеӯ—дёҚеӨҡпјҢж„ҸжҖқеҫҲжҳҺзҷҪпјҡзҘ еҸҜд»Ҙе»әпјҢеғҸеҸҜд»ҘеЎ‘пјҢдҪҶдёҚиғҪз§°зҘһз§°еңЈпјҢеҸӘи®ёеҲ»вҖңдёәж°‘иҖ…вҖқдёүдёӘеӯ—гҖӮ
еҶҷе®Ңеҗ№е№ІеўЁиҝ№пјҢжҠҳеҘҪж”ҫиҝӣдҝЎе°ҒгҖӮ
вҖңжҳҺеӨ©и®©еј е®ҲжӢҷиҙҙеҮәеҺ»гҖӮвҖқд»–иҮӘиЁҖиҮӘиҜӯгҖӮ
第дәҢеӨ©дёҖж—©пјҢжқ‘еҸЈжқҘдәҶеҚҒеҮ дёӘеЈ®жұүпјҢжҠ¬зқҖдёӘжңЁеғҸгҖӮ
жҳҜиҝһеӨңйӣ•зҡ„пјҢжүӢиүәдёҚз®—зІҫз»ҶпјҢдҪҶзңүзңјжңүдёғе…«еҲҶеғҸзҺӢе®Ҳд»ҒгҖӮиә«дёҠжҠ«дәҶ件жҙ—ж—§зҡ„йқӣи“қзӣҙиЈ°пјҢйӮЈжҳҜжқ‘ж°‘еҮ‘еёғж–ҷзјқзҡ„гҖӮеә•еә§з”Ёзҡ„жҳҜеұұйҮҢжңҖзЎ¬зҡ„й“ҒжқүжңЁпјҢеҲ·дәҶдёүеұӮжЎҗжІ№гҖӮ
зҺӢе®Ҳд»Ғз«ҷеңЁд№Ұйҷўй—ЁеҸЈзңӢзқҖгҖӮ
жІЎдәәиҜ·д»–иҝҮеҺ»пјҢд№ҹжІЎдәәиҜҙиҜқгҖӮйҳҹдјҚдёҖи·Ҝиө°еҲ°й©ҝз«ҷдёңиҫ№зҡ„з©әең°пјҢжҠҠжңЁеғҸж”ҫдёӢгҖӮйӮЈйҮҢе·Із»Ҹеһ’еҘҪдәҶзҹіеҹәпјҢжңқеҚ—ејҖеҗ‘йҳіе…үгҖӮ
жңүдёӘиҖҒжңЁеҢ жҺҸеҮәеҮҝеӯҗпјҢеңЁеә•еә§жӯЈйқўеҲ»дәҶдёүдёӘеӯ—пјҡвҖңдёәж°‘иҖ…вҖқгҖӮ
дј—дәәзӮ№еӨҙгҖӮ
зӯүеӨ§е®¶ж•ЈеҺ»пјҢйӮЈжңЁеҢ еҸҲеҒ·еҒ·зҝ»иҝҮеә•еә§пјҢеңЁиғҢйқўи§’иҗҪеҲ»дәҶдёӨдёӘе°Ҹеӯ—пјҡвҖңж–ҮеңЈвҖқгҖӮеҲ»е®ҢжҠ№дәҶеұӮжіҘйҒ®дҪҸпјҢи°Ғд№ҹжІЎзңӢи§ҒгҖӮ
дёӯеҚҲж—¶еҲҶпјҢеҮ дёӘеӯ©еӯҗеңЁз”°еҹӮдёҠзҺ©гҖӮ
еҝҪ然жңүдёӘе°Ҹеӯ©и·іиө·жқҘе–ҠпјҡвҖңеӨ©дёҠиҝҳжңүеӯ—пјҒвҖқ
е…¶д»–дәәжҠ¬еӨҙгҖӮ
йӣЁж—©е°ұеҒңдәҶпјҢеҸҜдә‘еұӮиҫ№зјҳиҝҳйЈҳзқҖдәӣж®ӢдҪҷзҡ„йҮ‘зә№пјҢж–ӯж–ӯз»ӯз»ӯз»„жҲҗдёҖеҸҘиҜқпјҡвҖңж·ұиҖ•жҳ“иҖЁпјҢеҠЎзЁјз©‘гҖӮвҖқ
еӯ©еӯҗ们дёҖдёӘжҺҘдёҖдёӘеҝөеҮәжқҘгҖӮ
жңүдёӘи®ӨдёҚеҫ—еӯ—зҡ„е°ҸеЁғй—®пјҡвҖңиҝҷжҳҜи°ҒеҶҷзҡ„пјҹвҖқ
еӨ§зӮ№зҡ„еӯ©еӯҗиҜҙпјҡвҖңиӮҜе®ҡжҳҜе…Ҳз”ҹеҶҷзҡ„пјҒд»–еҶҷзҡ„д№ҰйғҪиғҪйЈһдёҠеӨ©пјҒвҖқ
иҝҷиҜқдј еҫ—еҝ«пјҢеҚҲйҘӯеҗҺеҮ д№ҺдәәдәәйғҪзҹҘйҒ“дәҶгҖӮжңүдәәиҜҙжҳЁжҷҡжўҰи§ҒдёҖжң¬йҮ‘д№Ұд»ҺеӨ©иҖҢйҷҚпјҢзҝ»ејҖе…ЁжҳҜз§Қең°зҡ„жі•еӯҗпјӣжңүдәәиҜҙзҒ¶еҸ°дёҠзҡ„й”…зӣ–еҶ…дҫ§жҳҫеҮәдёҖиЎҢе°Ҹеӯ—пјҢж•ҷ他们жҖҺд№ҲжӢҢиӮҘеңҹгҖӮ
иөөеҜЎеҰҮи№ІеңЁеҺЁжҲҝй—ЁеҸЈеүҠеңҹиұҶпјҢеҝҪ然еҸ‘зҺ°й”…зӣ–еҸҚйқўзңҹзҡ„жңүдёҖиЎҢж·ЎзәўеҚ°и®°пјҢеҶҷзқҖвҖңзІӘе®ңзҶҹпјҢж°ҙе®ңйқҷвҖқгҖӮ
еҘ№ж„ЈдәҶеҮ з§’пјҢиҪ¬иә«иҝӣеұӢпјҢжҠҠеҺӢз®ұеә•зҡ„дёҖеқ—зәўеёғжӢҝеҮәжқҘпјҢеүӘжҲҗеӣӣж–№еқ—пјҢжҢӮеңЁдәҶз”ҹзҘ й—ЁеҸЈгҖӮ
йӮЈжҳҜеҘ№дёҲеӨ«д»ҺеүҚжү“д»—еёҰеӣһжқҘзҡ„жҠӨиә«з¬ҰгҖӮ
еӮҚжҷҡпјҢзҺӢе®Ҳд»ҒеҺ»дәҶз”ҹзҘ гҖӮ
жІЎдәәйҷӘд»–пјҢд№ҹжІЎдәәжӢҰгҖӮд»–з«ҷеңЁжңЁеғҸеүҚзңӢдәҶдёҖдјҡе„ҝпјҢжІЎиҜҙиҜқгҖӮиҪ¬иә«ж—¶жіЁж„ҸеҲ°еә•еә§иғҢйқўжңүж–°еҮҝз—•пјҢи№ІдёӢз”ЁжүӢж‘ёдәҶж‘ёгҖӮ
жҢҮи…№еҲ®иҝҮвҖңж–ҮеңЈвҖқдёӨдёӘеӯ—гҖӮ
д»–жІЎж“ҰпјҢд№ҹжІЎй—®гҖӮз«ҷиө·иә«жӢҚдәҶжӢҚиЈӨеӯҗпјҢеӣһдәҶд№ҰйҷўгҖӮ
еӨңйҮҢдёӢдәҶ第дәҢеңәйӣЁгҖӮ
жӣҙз»ҶпјҢжӣҙиҪ»гҖӮйӣЁзҸ йҮҢзҡ„еӯ—д№ҹеҸҳдәҶпјҢжҲҗдәҶгҖҠзӨјиҝҗгҖӢйҮҢзҡ„дёҖеҸҘпјҡвҖңеӨ§йҒ“д№ӢиЎҢд№ҹпјҢеӨ©дёӢдёәе…¬гҖӮвҖқ
з”°йҮҢзҡ„зЁ»з©—еҸҲй•ҝдәҶдёҖжҲӘгҖӮ
жқ‘иҘҝеӨҙйҳҝдёғ家еұӢйЎ¶жјҸйӣЁпјҢйӣЁж°ҙж»ҙиҝӣзў—йҮҢпјҢз«ҹжҺ’жҲҗдёҖиЎҢе°Ҹеӯ—пјҡвҖңдҝ®еұӢе®ңи¶ҒжҷҙгҖӮвҖқ
他第дәҢеӨ©дёҖж—©е°ұзҲ¬дёҠжҲҝйЎ¶иЎҘз“ҰгҖӮ
第дёүеӨ©жё…жҷЁпјҢеј е®ҲжӢҷеёҰзқҖе‘ҠзӨәжқҘиҙҙгҖӮ
и·ҜдёҠйҒҮи§ҒеҮ дёӘжүӣй”„еӨҙзҡ„жқ‘ж°‘пјҢй—®д»–пјҡвҖңе…Ҳз”ҹжңҖиҝ‘зҙҜдёҚзҙҜпјҹвҖқ
еј е®ҲжӢҷиҜҙпјҡвҖңиҝҳеҘҪпјҢе°ұжҳҜиғғз—…зҠҜдәҶдёӨж¬ЎгҖӮвҖқ
йӮЈдәәзӮ№зӮ№еӨҙпјҡвҖңйӮЈдҪ еӣһеҺ»е‘ҠиҜүд»–пјҢжҳЁеӨңдёӢйӣЁзҡ„ж—¶еҖҷпјҢжҲ‘家еЁғеҸ‘зғ§йҖҖдәҶгҖӮд»–еЁҳиҜҙпјҢжҳҜе…Ҳз”ҹеҶҷзҡ„еӯ—йЈҳиҝӣзӘ—жҲ·пјҢз»•еәҠиҪ¬дәҶдёүеңҲгҖӮвҖқ
еј е®ҲжӢҷжІЎеә”еЈ°гҖӮ
д»–жҠҠгҖҠзҘҖи®®гҖӢиҙҙеңЁжқ‘еҸЈе…¬е‘Ҡж ҸпјҢеҸҲеҺ»д№ҰйҷўжүҫзҺӢе®Ҳд»ҒгҖӮ
жҺЁй—ЁиҝӣеҺ»пјҢзңӢи§Ғд»–жӯЈеқҗеңЁжЎҢеүҚзҶ¬иҚҜгҖӮ
зӮүзҒ«жҷғзқҖд»–еҚҠиҫ№и„ёпјҢеҸҰдёҖдҫ§иҗҪеңЁйҳҙеҪұйҮҢгҖӮиҚҜзҪҗе’•еҳҹе“ҚпјҢи’ёжұҪеҫҖдёҠзҲ¬пјҢеңЁжҲҝжўҒдёӢеҮқжҲҗдёҖзүҮзҷҪйӣҫгҖӮ
вҖңз”ҹзҘ з«ӢеҘҪдәҶгҖӮвҖқеј е®ҲжӢҷиҜҙпјҢвҖңжӮЁеҶҷзҡ„规зҹ©д№ҹйғҪз…§еҠһдәҶгҖӮвҖқ
зҺӢе®Ҳд»ҒзӮ№зӮ№еӨҙпјҢжІЎжҠ¬еӨҙгҖӮ
вҖңеҸӘжҳҜвҖҰвҖҰвҖқеј е®ҲжӢҷйЎҝдәҶйЎҝпјҢвҖңеә•еә§еҗҺйқўпјҢжңүдәәеҲ»дәҶвҖҳж–ҮеңЈвҖҷгҖӮвҖқ
зҺӢе®Ҳд»Ғжҗ…иҚҜзҡ„жүӢеҒңдәҶдёҖдёӢгҖӮ
然еҗҺ继з»ӯжҗ…гҖӮ
вҖңйҡҸ他们еҗ§гҖӮвҖқд»–иҜҙгҖӮ
зӘ—еӨ–пјҢжҷЁе…үеҲҡз…§еҲ°з”ҹзҘ еұӢйЎ¶гҖӮйҰҷзӮүжҳҜж–°еҒҡзҡ„пјҢз©әзқҖпјҢжІЎзӮ№йҰҷгҖӮдҪҶең°дёҠе·ІжңүеҮ жқҹйҮҺиҠұпјҢж•ҙж•ҙйҪҗйҪҗж‘ҶеңЁжңЁеғҸи„ҡдёӢгҖӮ
жңүдёӘз©ҝзІ—еёғиЎЈзҡ„е°Ҹеӯ©и№ІеңЁйӮЈйҮҢпјҢжүӢйҮҢжӢҝзқҖж №ж ‘жһқпјҢеңЁжіҘең°дёҠдёҖ笔дёҖз”»еҶҷзқҖд»Җд№ҲгҖӮ
еҶҷзҡ„жҳҜвҖңзҹҘиЎҢеҗҲдёҖвҖқгҖӮ
зҺӢе®Ҳд»Ғз«Ҝиө·иҚҜзҪҗпјҢеҖ’иҝӣзў—йҮҢгҖӮ
иӨҗиүІзҡ„ж¶ІдҪ“жҷғдәҶжҷғпјҢиЎЁйқўжө®зқҖдёҖеұӮжІ№е…үгҖӮд»–еҗ№дәҶеҸЈж°”пјҢеҮҶеӨҮе–қгҖӮ
иҝҷж—¶пјҢй—ЁеӨ–дј жқҘи„ҡжӯҘеЈ°гҖӮ
еҫҲжҖҘгҖӮ
й—Ёиў«жҺЁејҖдёҖжқЎзјқпјҢиөөеҜЎеҰҮжҺўиҝӣеӨҙпјҢи„ёиүІеҸҳдәҶпјҡвҖңе…Ҳз”ҹпјҒз”ҹзҘ йӮЈиҫ№вҖҰвҖҰжңүдәәеҫҖйҰҷзӮүйҮҢеҖ’дәҶдёңиҘҝпјҒвҖқ
зҺӢе®Ҳд»Ғж”ҫдёӢзў—гҖӮ
иҚҜжұҒиҝҳеңЁеҶ’зғӯж°”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ө¶е°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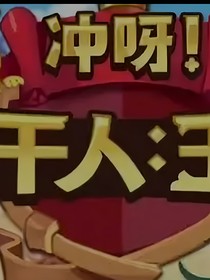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йҘје№ІдәӢи®°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еңЁејӮз•Ңзә№д№қйҫҷжӢүжЈә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Ҫ’е°ҳеҲӣдё–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家з”өи§ҶжңәиғҪз©ҝи¶ҠдёҮз•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