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з« пјҡеҰ–зҺӢжҖ’еҸ·дј пјҢз«ӢиӘ“еҶҚжҲҳжқҘ
йЈҺд»ҺеҢ—иҫ№еҗ№иҝҮжқҘзҡ„ж—¶еҖҷпјҢең°йқўиЈӮејҖдәҶгҖӮ
дёҚжҳҜеҶ»еҮәжқҘзҡ„йӮЈз§Қз»Ҷзә№пјҢжҳҜж·ұдёҚи§Ғеә•зҡ„еҸЈеӯҗпјҢеғҸиў«дәәз”ЁеҲҖеҲ’ејҖгҖӮзҺӢе®Ҳд»Ғз«ҷеңЁй•ҮйӮӘзў‘еүҚпјҢи„ҡдёӢзҡ„зҹіжқҝе·Із»ҸзўҺжҲҗеҮ еқ—пјҢиЈӮзјқйҮҢеҶ’еҮәеҜ’ж°”пјҢеёҰзқҖи…Ҙе‘ігҖӮ
д»–жІЎеҠЁгҖӮ
еҸіжүӢиҝҳжҗӯеңЁжҷәиҖ…зҡ„иӮ©дёҠпјҢеҲҡжүҚйӮЈдёҖеҸҘвҖңдҪ ж—©е°ұиғҪвҖқпјҢиҜқйҹіиҝҳжІЎж•ЈгҖӮеҸҜзҺ°еңЁпјҢд»–зҡ„жүӢ慢慢收дәҶеӣһжқҘпјҢиҪ¬иә«йқўеҗ‘еҢ—ж–№гҖӮ
еӨ©иүІжҡ—дәҶгҖӮ
й»‘дә‘еҺӢдёӢжқҘпјҢдёҚжҳҜд№Ңдә‘пјҢжҳҜжө“еҫ—еҢ–дёҚејҖзҡ„еҰ–йӣҫпјҢзҝ»ж»ҡзқҖеҫҖиҝҷиҫ№ж¶ҢгҖӮиҝңеӨ„йӣӘеұұйЎ¶дёҠпјҢдёҖеЈ°еҗјеҸ«з©ҝз ҙйЈҺйӣӘпјҢйңҮеҫ—еұұдҪ“жҠ–дәҶдёүжҠ–гҖӮ
еј е®ҲжӢҷеҶІиҝӣжқ‘еҸЈж—¶пјҢе·ҰжүӢжҢҮиҠӮе…ЁжҳҜиЎҖгҖӮ
д»–дёҖи·Ҝи·‘жқҘпјҢжҢҮз”Іеҙ©дәҶдёӨж №пјҢдёүж”ҜжҜӣ笔ж”ҘеңЁжүӢйҮҢпјҢиө°еҲ°еҚҠи·ҜзӘҒ然йҪҗеҲ·еҲ·ж–ӯжҲҗе…ӯжҲӘгҖӮ笔尖иҗҪең°йӮЈеҲ»пјҢд»–иҶқзӣ–дёҖиҪҜпјҢе·®зӮ№и·ӘдёӢгҖӮ
вҖңе…Ҳз”ҹпјҒвҖқд»–е–Ҡеҫ—е–үе’ҷеҸ‘е“‘пјҢвҖңжҳҜиӢҚйӘЁпјҒвҖқ
зҺӢе®Ҳд»ҒзңӢдәҶд»–дёҖзңјгҖӮ
еј е®ҲжӢҷе–ҳзқҖж°”пјҢжҠҠж–ӯ笔еЎһиҝӣи…°й—ҙйұјзҜ“пјҢжҠ¬еӨҙд№ҹжңӣеҗ‘еҢ—иҫ№гҖӮйӮЈиҫ№зҡ„дә‘ејҖе§Ӣж—ӢиҪ¬пјҢжёҗжёҗжҳҫеҮәдёҖеј и„ёвҖ”вҖ”йӘ·й«…еӨҙпјҢзңјзӘқйҮҢзғ§зқҖи“қзҒ«пјҢеҳҙдёҖеј дёҖеҗҲпјҢжІЎжңүеЈ°йҹіпјҢдҪҶж•ҙдёӘжқ‘еӯҗзҡ„дәәйғҪеҗ¬и§ҒдәҶйӮЈеҸҘиҜқпјҡ
вҖңзҺӢе®Ҳд»ҒвҖҰвҖҰдҪ жҠӨдёҚдҪҸ他们гҖӮвҖқ
иҜқиҗҪзҡ„дёҖзһ¬пјҢ家家жҲ·жҲ·зҡ„зӘ—зәёе“—е•Ұе“ҚгҖӮжңүеӯ©еӯҗе°–еҸ«пјҢжҠұзқҖи„‘иўӢи№ІеңЁең°дёҠпјӣдёҖдёӘиҖҒжұүзҢӣең°жҠ“иө·й”„еӨҙз ёеҗ‘иҮӘ家门жЎҶпјҢеҳҙйҮҢе–ҠзқҖвҖңеҲ«иҝӣжқҘвҖқпјӣиөөеҜЎеҰҮд»ҺеҺЁжҲҝеҶІеҮәжқҘпјҢиҸңеҲҖжЁӘеңЁиғёеүҚпјҢи„ёиүІеҸ‘зҷҪгҖӮ
иҝҷдёҚжҳҜж”»еҮ»гҖӮ
жҳҜеҺӢгҖӮ
еғҸдёҖеқ—еҚғж–ӨйҮҚзҡ„зҹіеӨҙжҗҒеңЁеҝғеҸЈпјҢе–ҳдёҚдёҠж°”гҖӮжңүдәәејҖе§ӢиҖійёЈпјҢжңүдәәзңјеүҚеҸ‘й»‘пјҢж–Үж°”з¬ҰзәёиҙҙеңЁй—ЁжҘЈдёҠпјҢдә®дәҶдёҖдёӢе°ұзҒӯдәҶгҖӮ
зҺӢе®Ҳд»ҒдҪҺеӨҙзңӢдәҶзңӢжЎғжңЁеү‘гҖӮ
еү‘иә«иҝҳеңЁйўӨпјҢиЈӮз—•йҮҢзҡ„зҙ«е…үеҝҪжҳҺеҝҪжҡ—гҖӮд»–ејҜи…°пјҢжҠҠе®ғжҸ’иҝӣй•ҮйӮӘзў‘ж—Ғзҡ„зҹізјқйҮҢпјҢе’ҢеҲҡжүҚдёҖж ·пјҢйҮ‘зә№йЎәзқҖең°зјқзҲ¬еҮәеҺ»пјҢдҪҶиҝҷж¬ЎеҸӘ蔓延дәҶдёүе°әе°ұеҒңдәҶгҖӮ
дёҚеӨҹгҖӮ
д»–дјёжүӢиҝӣиў–еҸЈпјҢжҺҸеҮәдёҖеҚ·зәёгҖӮ
гҖҠж–Үе®«зҜҮгҖӢзҡ„жүӢзЁҝпјҢеўЁиҝ№жңӘе№ІпјҢжҳҜд»–й—ӯе…іж—¶дёҖ笔дёҖ笔еҶҷдёӢжқҘзҡ„гҖӮзәёи§’жңүдәӣеҸ‘зҡұпјҢиҫ№зјҳиҝҳжІҫзқҖиҚҜжұҒзҡ„й»„жёҚгҖӮ
д»–еҚ•иҶқи·Әең°пјҢе°Ҷж•ҙеҚ·зәёжҢүиҝӣзў‘еҹәзҡ„иЈӮзјқдёӯгҖӮ
жүӢжҺҢеҺӢдёӢеҺ»зҡ„зһ¬й—ҙпјҢең°еә•дј жқҘйңҮеҠЁгҖӮ
дёҖйҒ“йҮ‘е…үд»Һзў‘еә•зӮёејҖпјҢеғҸж°ҙжіўдёҖж ·еҫҖеӨ–жҺЁгҖӮжүҖиҝҮд№ӢеӨ„пјҢж®ӢеҶ°иһҚеҢ–пјҢеҶ»еңҹеҸҳиҪҜпјҢеұӢжӘҗдёӢзҡ„еҶ°й”Ҙж»ҙж»ҙзӯ”зӯ”еҫҖдёӢжҺүж°ҙгҖӮйӮЈдәӣзҶ„зҒӯзҡ„ж–Үж°”з¬ҰзәёйҮҚж–°зҮғиө·жҡ–е…үпјҢиҝһжҢӮеңЁеўҷдёҠзҡ„ж—§д№ҰйғҪж— йЈҺиҮӘеҠЁпјҢйЎөйЎөзҝ»йЈһгҖӮ
еј е®ҲжӢҷйҖҖдәҶдёҖжӯҘпјҢзһӘеӨ§зңјзқӣгҖӮ
д»–зңӢи§ҒиҮӘе·ұйұјзҜ“йҮҢйӮЈеҮ ж”Ҝж–ӯ笔пјҢ笔жқҶдёҠзҡ„иЈӮзә№жӯЈеңЁжё—еҮәеҫ®ејұзҡ„йҮ‘иҠ’гҖӮ
еҢ—ж–№зҡ„еҰ–дә‘жҷғдәҶжҷғгҖӮ
йӘ·й«…и„ёжүӯжӣІдәҶдёҖдёӢпјҢи“қзҒ«и·іеҠЁеҫ—жӣҙжҖҘгҖӮдҪҶе®ғжІЎйҖҖгҖӮ
зҺӢе®Ҳд»Ғз«ҷиө·иә«пјҢжӢҚдәҶжӢҚжүӢгҖӮ
д»–иө°еҲ°жқ‘дёӯеӨ®зҡ„з©әең°дёҠпјҢиё©еңЁйӮЈйҒ“йҮ‘е…үжңҖдә®зҡ„дҪҚзҪ®пјҢжҠ¬еӨҙзңӢеӨ©гҖӮ
вҖңж–ҮдёҚеңЁй«ҳеҸ°пјҢеңЁж°‘еҝғгҖӮвҖқд»–иҜҙпјҢвҖңйҒ“дёҚеңЁй•ҝз”ҹпјҢеңЁжӢ…еҪ“гҖӮвҖқ
иҜҙе®ҢпјҢд»–жҠ¬иө·еҸіжүӢпјҢеңЁз©әдёӯеҲ’дәҶеӣӣдёӘеӯ—гҖӮ
вҖңзҹҘиЎҢеҗҲдёҖгҖӮвҖқ
еӯ—жҳҜйҮ‘иүІзҡ„пјҢжӮ¬еңЁеҚҠз©әдёүжҒҜжүҚж•ЈгҖӮйЈҺдёҖеҗ№пјҢзўҺжҲҗзӮ№зӮ№йҮ‘е°ҳпјҢйЈҳиҝӣжҜҸдёҖ家жҜҸдёҖжҲ·гҖӮжңүдёӘжӯЈеҸ‘жҠ–зҡ„е°Ҹеӯ©еҝҪ然дёҚжҠ–дәҶпјҢдјёжүӢжҺҘдҪҸдёҖзӮ№е…үпјҢжҸЎеңЁжүӢеҝғгҖӮ
зҺӢе®Ҳд»ҒиҪ¬иҝҮиә«пјҢйқўеҜ№жқ‘ж°‘гҖӮ
他们еӣҙеңЁеӣӣе‘ЁпјҢжңүзҡ„з«ҷзқҖпјҢжңүзҡ„и№ІзқҖпјҢи„ёдёҠиҝҳжңүжғҠйӯӮжңӘе®ҡгҖӮд»–еЈ°йҹідёҚй«ҳпјҢд№ҹдёҚжҝҖжҳӮпјҢе°ұеғҸе№іж—¶и®ІиҜҫйӮЈж ·гҖӮ
вҖңе‘ҠиҜүдҪ 们зҡ„еӯ©еӯҗгҖӮвҖқд»–иҜҙпјҢвҖңиӢҘеҶҚжңүеҰ–йЈҺжқҘиўӯпјҢдёҚеҝ…иәІи—ҸгҖӮжӢҝиө·з¬”пјҢеҶҷдёӢдҪ еҝғдёӯзҡ„жӯЈеӯ—гҖӮйӮЈдёҖ笔дёҖз”»пјҢе°ұжҳҜжҲ‘们зҡ„еҲҖеү‘гҖӮвҖқ
жІЎдәәиҜҙиҜқгҖӮ
еҸӘжңүйЈҺеҗ№иҝҮеұӢйЎ¶зҡ„еЈ°йҹігҖӮ
д»–жңҖеҗҺзңӢдәҶдёҖзңјеҢ—ж–№пјҢжҠ¬й«ҳеЈ°йҹіпјҡвҖңиӢҚйӘЁпјҒйҫҷеңәй©ҝжңүдёүеҚғж–ҮзҒ«пјҢзҡҶеҸҜз„ҡе°”еҰ–йӯӮвҖ”вҖ”жҲ‘зӯүдҪ еҶҚжқҘпјҒвҖқ
иҜқйҹіиҗҪдёӢпјҢж•ҙдёӘжқ‘еӯҗзҡ„ең°йқўеҸҲжҳҜдёҖйңҮгҖӮ
зҺӢе®Ҳд»Ғз«ӢеҲ»зӣҳеқҗдёӢжқҘпјҢеҸіжүӢйЈҹжҢҮиҳёдәҶзӮ№е”Үиҫ№зҡ„иЎҖпјҢеңЁең°дёҠејҖе§ӢеҶҷеӯ—гҖӮ
еҶҷзҡ„жҳҜгҖҠж–Үе®«зҜҮгҖӢзҡ„ж ёеҝғж®өиҗҪгҖӮ
жҜҸеҶҷдёҖдёӘеӯ—пјҢең°дёӢе°ұдј еҮәдёҖеЈ°й—·е“ҚпјҢеғҸжҳҜеӨ§ең°еңЁеӣһеә”гҖӮиҝңеӨ„з”°еҹӮгҖҒеұұеЈҒгҖҒиҖҒж ‘ж №дёӢпјҢйҡҗйҡҗжө®зҺ°еҮәеҸӨиҖҒзҡ„ж–Үеӯ—пјҢжӯӘжӯӘжүӯжүӯпјҢеҚҙиҝһжҲҗдёҖзүҮгҖӮ
еј е®¶йҳҝе©ҶжҠұзқҖеӯҷеӯҗеқҗеңЁй—Ёж§ӣдёҠпјҢеҝҪ然еҸ‘зҺ°жҖҖйҮҢзҡ„еӯ©еӯҗдёҫиө·е°ҸжүӢпјҢеңЁз©әдёӯжҜ”еҲ’гҖӮ
еҘ№ж„ЈдҪҸгҖӮ
йӮЈжҳҜдёӘвҖңдәәвҖқеӯ—гҖӮ
жқ‘дёңеӨҙпјҢй“ҒеҢ й“әзҡ„иҖҒжқҺжӯЈж“ҰзқҖж–§еӨҙпјҢеҝҪ然и§үеҫ—иғёеҸЈеҸ‘зғӯгҖӮд»–дҪҺеӨҙдёҖзңӢпјҢжҢӮеңЁи„–еӯҗдёҠзҡ„еҚҠеқ—й“ңй’ұзүҢпјҢжӯЈйқўжңқеӨ–зҡ„йӮЈдёҖйқўпјҢз«ҹжө®еҮәдёӨдёӘе°Ҹеӯ—пјҡвҖңе®Ҳд№үвҖқгҖӮ
иҘҝеӨҙиөөеҜЎеҰҮ家зҒ¶еҸ°иҫ№пјҢй”…йҮҢзҡ„зІҘе’•еҳҹеҶ’жіЎпјҢи’ёжұҪеҫҖдёҠеҶІпјҢз«ҹеңЁеўҷдёҠжҠ•еҮәдёҖдёӘе®Ңж•ҙзҡ„вҖңд»ҒвҖқеӯ—иҪ®е»“пјҢдёүжҒҜдёҚж•ЈгҖӮ
зҺӢе®Ҳд»Ғи¶ҠеҶҷи¶Ҡеҝ«гҖӮ
жҢҮеӨҙзЈЁз ҙдәҶпјҢиЎҖж··зқҖжіҘпјҢеңЁең°дёҠжӢ–еҮәй•ҝй•ҝзҡ„з—•иҝ№гҖӮжңҖеҗҺдёҖдёӘеӯ—иҗҪ笔时пјҢд»–ж•ҙдёӘдәәжҷғдәҶдёҖдёӢпјҢйқ дҪҸж—Ғиҫ№зҡ„зҹіеў©жүҚжІЎеҖ’дёӢгҖӮ
дҪҶе°ұеңЁйӮЈдёҖеҲ»вҖ”вҖ”
е…Ёжқ‘дёүеҚғжҲ·дәә家пјҢзӘ—жЈӮгҖҒй—ЁзҺҜгҖҒзҒ¶еҸ°гҖҒдә•жІҝпјҢеҮЎжҳҜиғҪжҳ е…үзҡ„ең°ж–№пјҢе…ЁйғҪеҚҮиө·дёҖдёқеҫ®ејұзҡ„зҒ«иӢ—гҖӮ
дёҚжҳҜзңҹзҒ«гҖӮ
жҳҜж–ҮзҒ«гҖӮ
ж·ЎйҮ‘иүІпјҢеҸӘжңүжҢҮе°–йӮЈд№Ҳй«ҳпјҢж‘ҮжӣізқҖпјҢеҚҙдёҚзҒӯгҖӮдёүеҚғйҒ“зҒ«иӢ—еҚҮеҲ°еҚҠз©әпјҢжұҮжҲҗдёҖзүҮе…үжө·пјҢеғҸдёҖеұӮи–„зәұзӣ–еңЁж•ҙдёӘжқ‘еӯҗдёҠз©әгҖӮ
еҢ—ж–№зҡ„еҰ–дә‘ж’һдёҠжқҘгҖӮ
жІЎжңүзҲҶзӮёпјҢд№ҹжІЎжңүеҳ¶еҗјгҖӮ
е°ұеғҸзғӯж°ҙжіјдёҠеҶ°еқ—пјҢй»‘дә‘иҫ№зјҳиҝ…йҖҹж¶ҲиһҚгҖӮйӘ·й«…и„ёеҸ‘еҮәдёҖеЈ°дҪҺжІүзҡ„е’Ҷе“®пјҢйҡҸеҚіиў«йҮ‘е…үеҗһжІЎгҖӮж•ҙзүҮдә‘и°ғеӨҙеҗ‘иҘҝпјҢйЈһйҖҹйҖҖеҺ»пјҢзңЁзңјж¶ҲеӨұеңЁзҫӨеұұд№Ӣй—ҙгҖӮ
еӨ§ең°е®үйқҷдәҶгҖӮ
йЈҺеҒңдәҶпјҢиЈӮзјқдёҚеҶҚжү©еӨ§пјҢиҝһз©әж°”йҮҢзҡ„и…Ҙе‘ійғҪж·ЎдәҶгҖӮ
еј е®ҲжӢҷз«ҷеңЁзҺӢе®Ҳд»Ғиә«еҗҺдә”жӯҘиҝңпјҢеҸҢжүӢзҙ§жҸЎйұјзҜ“иҫ№зјҳпјҢжҢҮиҠӮеҸ‘зҷҪгҖӮд»–дёҖзӣҙзӣҜзқҖеӨ©йҷ…пјҢзӣҙеҲ°жңҖеҗҺдёҖзј•й»‘йӣҫж¶ҲеӨұпјҢжүҚзј“зј“еҗҗеҮәдёҖеҸЈж°”гҖӮ
зҺӢе®Ҳд»ҒжІЎеӣһеӨҙгҖӮ
д»–еқҗзқҖпјҢиғҢжҢәеҫ—зӣҙпјҢеҸҢзңјй—ӯзқҖпјҢе‘јеҗёе№ізЁігҖӮжЎғжңЁеү‘йқҷйқҷжҸ’еңЁзў‘ж—ҒпјҢйҮ‘зә№е·Із»Ҹзј©еӣһеү‘иә«пјҢеҸӘеңЁиЈӮз—•ж·ұеӨ„иҝҳжңүдёҖзӮ№еҫ®е…үй—ӘеҠЁгҖӮ
жқ‘еӯҗйҮҢејҖе§ӢжңүеҠЁйқҷгҖӮ
жңүдәәжҺЁејҖжҲҝй—ЁпјҢжҺўеҮәеӨҙпјӣеӯ©еӯҗжӢүзқҖеЁҳзҡ„иЎЈи§’й—®вҖңеҰ–жҖӘиө°дәҶеҗ—вҖқпјӣиөөеҜЎеҰҮз«ҜзқҖдёҖзӣҶзғӯж°ҙиө°еҮәжқҘпјҢзңӢеҲ°йҷўеӯҗйҮҢйӮЈеұӮж·Ўж·Ўзҡ„йҮ‘е…үпјҢжҖ”дәҶдёҖдёӢпјҢ然еҗҺиҪ»иҪ»жҠҠж°ҙеҖ’иҝӣжІҹйҮҢгҖӮ
еј е®ҲжӢҷиө°иҝҮеҺ»пјҢеңЁзҺӢе®Ҳд»Ғиә«иҫ№и№ІдёӢгҖӮ
вҖңе…Ҳз”ҹгҖӮвҖқд»–дҪҺеЈ°иҜҙпјҢвҖңжӮЁж„ҹи§үеҲ°дәҶеҗ—пјҹеҲҡжүҚеҶҷеӯ—зҡ„ж—¶еҖҷпјҢең°еә•дёӢвҖҰвҖҰеҘҪеғҸжңүдёңиҘҝеңЁи·ҹзқҖжӮЁеҝөгҖӮвҖқ
зҺӢе®Ҳд»ҒзқҒејҖзңјгҖӮ
зӣ®е…үе№ійқҷгҖӮ
вҖңйӮЈжҳҜж–Үи„үгҖӮвҖқд»–иҜҙпјҢвҖңд»ҘеүҚж–ӯдәҶпјҢзҺ°еңЁйҖҡдәҶгҖӮвҖқ
еј е®ҲжӢҷзӮ№зӮ№еӨҙпјҢиҝҳжғіиҜҙд»Җд№ҲпјҢеҝҪ然иә«еӯҗдёҖеғөгҖӮ
д»–зҢӣең°жҠ¬еӨҙгҖӮ
еҢ—ж–№еӨ©иҫ№пјҢдёҖйҒ“жһҒз»Ҷзҡ„зәўзәҝеҲ’з ҙдә‘еұӮпјҢдёҖй—ӘиҖҢиҝҮгҖӮ
зҙ§жҺҘзқҖпјҢдёҖеЈ°жҖ’еҗјд»ҺжһҒиҝңеӨ„дј жқҘгҖӮ
дёҚжҳҜйҖҡиҝҮиҖіжңөеҗ¬еҲ°зҡ„гҖӮ
жҳҜзӣҙжҺҘеңЁи„‘еӯҗйҮҢзӮёејҖзҡ„гҖӮ
вҖңзҺӢе®Ҳд»ҒвҖ”вҖ”вҖқ
дёӨдёӘеӯ—пјҢеғҸй“Ғй”Өз ёеңЁеҝғеӨҙгҖӮ
еј е®ҲжӢҷжҚӮдҪҸиҖіжңөпјҢеҳҙи§’жәўеҮәиЎҖдёқгҖӮеҮ дёӘзҰ»еҫ—иҝ‘зҡ„еӯ©еӯҗе“Үең°е“ӯдәҶеҮәжқҘгҖӮ
зҺӢе®Ҳд»Ғзј“зј“з«ҷиө·иә«гҖӮ
д»–иө°еҲ°зў‘еүҚпјҢжӢ”еҮәжЎғжңЁеү‘гҖӮ
еү‘иә«иҪ»йўӨпјҢеғҸжҳҜж„ҹеә”еҲ°дәҶд»Җд№ҲгҖӮ
д»–жҠ¬еӨҙжңӣзқҖйӮЈйҒ“е·Іж¶ҲеӨұзҡ„зәўзәҝпјҢеҳҙе”ҮеҠЁдәҶеҠЁпјҢжІЎиҜҙиҜқгҖӮ
еј е®ҲжӢҷжҠ№дәҶжҠҠеҳҙпјҢз«ҷиө·жқҘпјҢз«ҷеҲ°д»–дҫ§еҗҺж–№гҖӮ
дёӨдәә并иӮ©з«ҷзқҖпјҢдёҖдёӘжҸЎеү‘пјҢдёҖдёӘз©әжүӢпјҢйғҪзңӢзқҖеҢ—иҫ№гҖӮ
жқ‘еӨ–еұұеқЎдёҠпјҢдёҖеҸӘйҮҺе…”д»ҺжҙһйҮҢжҺўеҮәеӨҙпјҢйј»еӯҗжҠҪдәҶжҠҪпјҢеҸҲзј©дәҶеӣһеҺ»гҖӮ
зҺӢе®Ҳд»Ғзҡ„иў–еҸЈж»‘дёӢдёҖж»ҙиҚҜжұҒпјҢиҗҪеңЁең°дёҠпјҢжё—иҝӣжіҘеңҹ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ө¶е°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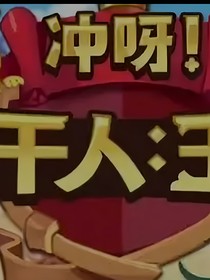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йҘје№ІдәӢи®°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еңЁејӮз•Ңзә№д№қйҫҷжӢүжЈә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Ҫ’е°ҳеҲӣдё–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家з”өи§ҶжңәиғҪз©ҝи¶ҠдёҮз•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