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з« пјҡеҝғе®«жҳҫзңҹеҪўпјҢж–ҮйҒ“и·ғж–°еўғ
зҺӢе®Ҳд»Ғзҡ„ж„ҸиҜҶжІүдәҶдёӢеҺ»гҖӮ
дёҚжҳҜжҳҸиҝ·пјҢд№ҹдёҚжҳҜзқЎзқҖпјҢжҳҜеғҸдёҖеқ—зҹіеӨҙиҗҪиҝӣж·ұдә•пјҢз©ҝиҝҮеұӮеұӮй»‘ж°ҙпјҢдёҖзӣҙеҫҖдёӢеқ гҖӮиҖіиҫ№жІЎжңүеЈ°йҹіпјҢиә«дҪ“жІЎжңүзҹҘи§үпјҢеҸӘжңүзңүеҝғйӮЈйў—иӣҮеҰ–еҶ…дё№иҝҳеңЁеҸ‘зғ«пјҢеғҸдёҖж №й’үеӯҗжҠҠд»–еҫҖжҹҗдёӘең°ж–№жӢҪгҖӮ
д»–зқҒејҖзңјзҡ„ж—¶еҖҷпјҢеҸ‘зҺ°иҮӘе·ұз«ҷеңЁдёҖзүҮиҷҡз©әйҮҢгҖӮ
еӨҙйЎ¶жІЎжңүеӨ©пјҢи„ҡдёӢжІЎжңүең°пјҢеӣӣе‘ЁжјӮжө®зқҖж— ж•°еҚ·д№ҰеҶҢпјҢеғҸжҳҜиў«йЈҺеҗ№ж•Јзҡ„зәёйЎөпјҢзј“зј“ж—ӢиҪ¬гҖӮжҜҸдёҖйЎөдёҠйғҪеҶҷзқҖеӯ—пјҢжңүзҡ„жҳҜд»–иҜ»иҝҮзҡ„гҖҠи®әиҜӯгҖӢпјҢжңүзҡ„жҳҜд»–жҠ„иҝҮзҡ„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пјҢиҝҳжңүд»–иҮӘе·ұеҶҷдёӢзҡ„ж–Үз« ж®өиҗҪпјҢдёҖиЎҢиЎҢжӮ¬еңЁз©әдёӯпјҢеғҸжҳҹжҳҹдёҖж ·дә®гҖӮ
иҝҷе°ұжҳҜд»–зҡ„еҝғе®«гҖӮ
д»–зҹҘйҒ“гҖӮ
дёҚз”Ёи°Ғе‘ҠиҜүд»–пјҢд»–е°ұжҳҜзҹҘйҒ“гҖӮиҝҷдәӣд№ҰгҖҒиҝҷдәӣеӯ—гҖҒиҝҷдәӣеҝөеӨҙпјҢйғҪжҳҜд»–жҙ»еҲ°дёүеҚҒдәҢеІҒж”’дёӢжқҘзҡ„дёңиҘҝгҖӮдёҚжҳҜжӯ»и®°зЎ¬иғҢпјҢдёҚжҳҜдёәдәҶиҖғ科дёҫпјҢиҖҢжҳҜд»–зңҹжӯЈдҝЎиҝҮгҖҒеҒҡиҝҮгҖҒз—ӣиҝҮзҡ„дәӢгҖӮ
д»–еҫҖеүҚиө°дәҶдёҖжӯҘгҖӮ
и„ҡиё©зҡ„ең°ж–№жІЎжңүе®һдҪ“пјҢеҸҜд»–ж„ҹи§үеҲ°дәҶж”Ҝж’‘гҖӮиҝҷең°ж–№и®Өеҫ—д»–гҖӮ
д»–дјёеҮәжүӢпјҢжғіеҺ»зў°жңҖиҝ‘зҡ„дёҖжң¬д№ҰгҖӮе°Ғзҡ®дёҠеҶҷзқҖгҖҠеә„еӯҗгҖӢдёӨдёӘеӯ—пјҢеўЁиҝ№зҶҹжӮүпјҢжҳҜд»–е№ҙиҪ»ж—¶дёҙж‘№зҡ„жүӢ笔гҖӮ
жҢҮе°–еҲҡзў°еҲ°д№Ұи§’пјҢйӮЈжң¬д№ҰзӘҒ然дёҖйўӨгҖӮ
жҺҘзқҖпјҢж•ҙзүҮжҳҹзҫӨзӮёејҖдәҶгҖӮ
д№ҰйЎөзўҺжҲҗзІүжң«пјҢж–Үеӯ—еҢ–дҪңй»‘йЈҺжү‘йқўиҖҢжқҘгҖӮйЈҺйҮҢжңүеЈ°йҹіпјҢдёҖдёӘжҺҘдёҖдёӘең°е–Ҡпјҡ
вҖңдҪ ж јз«№дёғж—ҘпјҢеҗҗиЎҖдёүеҚҮпјҢеҸҜжӣҫж јеҮәдёӘйҒ“зҗҶпјҹвҖқ
вҖңдҪ е©ҡзӨјеҪ“еӨ©дёҚеҺ»жҙһжҲҝпјҢзӢ¬еқҗд№Ұж–ӢпјҢз®—д»Җд№Ҳз”·дәәпјҹвҖқ
вҖңдҪ ж•‘йӮЈеӯ©еӯҗпјҢеҶҷдёӢвҖҳд»ҒвҖҷеӯ—пјҢеҸҜеҗҺжқҘе‘ўпјҹд№Ұйҷўең°дёӢдёүзҷҫз«Ҙе°ёпјҢйўқдёҠд№ҹеҲ»зқҖвҖҳж–ҮвҖҷеӯ—пјҒвҖқ
зҺӢе®Ҳд»Ғз«ҷеңЁеҺҹең°жІЎеҠЁгҖӮ
д»–зҹҘйҒ“иҝҷжҳҜеҝғйӯ”гҖӮ
дёҚжҳҜеӨ–жқҘзҡ„еҰ–пјҢжҳҜи—ҸеңЁд»–иҮӘе·ұеҝғйҮҢзҡ„йӮЈдәӣжҖҖз–‘гҖҒйӮЈдәӣдёҚз”ҳгҖҒйӮЈдәӣеӨңйҮҢзҝ»жқҘиҰҶеҺ»зқЎдёҚзқҖж—¶й—®иҮӘе·ұзҡ„иҜқгҖӮ
д»–жІЎеҸҚй©ігҖӮ
зӣҙеҲ°й»‘йЈҺеҚ·еҲ°зңјеүҚпјҢеҮ д№ҺиҰҒжҠҠд»–ж’•ејҖзҡ„ж—¶еҖҷпјҢд»–жүҚејҖеҸЈгҖӮ
вҖңжҲ‘ж јз«№пјҢдёҚжҳҜдёәдәҶеҪ“еңЈдәәгҖӮвҖқд»–иҜҙпјҢвҖңжҳҜдёәдәҶиҜ•иҜ•иҝҷжқЎи·ҜиғҪдёҚиғҪиө°йҖҡгҖӮвҖқ
йЈҺйЎҝдәҶдёҖдёӢгҖӮ
вҖңжҲ‘йӮЈеӨ©жІЎиҝӣжҙһжҲҝпјҢжҳҜеӣ дёәжҲ‘еңЁжғіпјҢеҰӮжһңзӨјж•ҷиҝһдёҖдёӘеӯ©еӯҗзҡ„вҖҳд»ҒвҖҷеӯ—йғҪиҰҒжҜҒпјҢйӮЈиҝҷзӨјпјҢиҝҳжҳҜдёҚжҳҜдёәдәәжңҚеҠЎзҡ„пјҹвҖқ
еҸҲдёҖйҳөйЈҺжү‘жқҘпјҢеёҰзқҖи…Ҙж°”гҖӮ
вҖңжҲ‘е»әзҷҪй№ҝжҙһд№ҰйҷўпјҢдёҚжҳҜдёәдәҶеҗҚз•ҷйқ’еҸІгҖӮвҖқд»–еЈ°йҹіжІЎеҸҳпјҢвҖңжҳҜдёәдәҶи®©з©·дәә家зҡ„еӯ©еӯҗд№ҹиғҪжҠ¬еӨҙеҶҷеӯ—гҖӮиҮідәҺең°дёӢйӮЈдәӣе°ёйҰ–вҖҰвҖҰйӮЈжҳҜеҰ–еҗҺе№Ізҡ„пјҢдёҚжҳҜжҲ‘гҖӮвҖқ
жңҖеҗҺеҮ дёӘеӯ—иҗҪдёӢпјҢй»‘йЈҺеҝҪ然еҒңдәҶгҖӮ
йӮЈдәӣзўҺзүҮиҲ¬зҡ„ж–Үеӯ—еңЁз©әдёӯжӮ¬зқҖпјҢдёҚеҶҚж”»еҮ»пјҢд№ҹдёҚж•ЈеҺ»гҖӮ
иҝңеӨ„дј жқҘдёҖеЈ°зҗҙйҹігҖӮ
еҫҲиҪ»пјҢдҪҶз©ҝйҖҸдәҶиҝҷзүҮиҷҡз©әгҖӮ
зҺӢе®Ҳд»Ғеҗ¬еҮәжқҘдәҶпјҢжҳҜгҖҠе№ҝйҷөж•ЈгҖӢзҡ„ејҖеӨҙеҮ еҸҘгҖӮдёғејҰзҗҙпјҢеј№еҫ—ж–ӯж–ӯз»ӯз»ӯпјҢеғҸжҳҜжңүдәәеңЁеӢүејәж’‘зқҖгҖӮ
д»–зҹҘйҒ“жҳҜи°ҒгҖӮ
еҘ№дёҚеңЁиҝҷйҮҢпјҢеҸҜеҘ№зҡ„зҗҙеЈ°жқҘдәҶгҖӮеғҸдёҖж №зәҝпјҢжҠҠд»–еҝ«иҰҒйЈҳж•Јзҡ„зҘһиҜҶжӢүдҪҸгҖӮ
д»–й—ӯдёҠзңјпјҢйҮҚж–°з«ҷе®ҡгҖӮ
вҖңзҹҘжҳҜиЎҢд№Ӣе§ӢпјҢиЎҢжҳҜзҹҘд№ӢжҲҗгҖӮвҖқд»–иҜҙпјҢвҖңжҲ‘жІЎжңүзҹҘиҖҢдёҚиЎҢпјҢд№ҹжІЎжңүиЎҢиҖҢдёҚеқҡгҖӮжҲ‘жүҖзҹҘзҡ„жҜҸдёҖеҸҘиҜқпјҢйғҪз”Ёе‘ҪеҺ»иҜ•иҝҮпјӣжҲ‘жүҖеҒҡзҡ„жҜҸдёҖ件дәӢпјҢйғҪд»ҺеҝғйҮҢеҮәеҸ‘гҖӮвҖқ
иҜқйҹіиҗҪпјҢеҝғе®«йңҮеҠЁгҖӮ
дёӨйҒ“е…үд»Һиҷҡз©әдёӯеҚҮиө·гҖӮ
е·Ұиҫ№жҳҜйҮ‘иүІзҡ„еӨ§еӯ—вҖ”вҖ”вҖңзҹҘвҖқгҖӮ
еҸіиҫ№жҳҜжјҶй»‘зҡ„еӨ§еӯ—вҖ”вҖ”вҖңиЎҢвҖқгҖӮ
дёӨдёӘеӯ—дёҖејҖе§ӢзҰ»еҫ—еҫҲиҝңпјҢдёӯй—ҙйҡ”зқҖз©әиҚЎиҚЎзҡ„й»‘жҡ—гҖӮе®ғ们еғҸжҳҜдә’зӣёжҺ’ж–ҘпјҢи°Ғд№ҹдёҚиӮҜйқ иҝ‘гҖӮ
зҺӢе®Ҳд»ҒзңӢзқҖе®ғ们пјҢ继з»ӯиҜҙпјҡвҖңжҲ‘иҜ»еңЈиҙӨд№ҰпјҢжҳҜзҹҘгҖӮжҲ‘жөҒж”ҫи·ҜдёҠж•‘дәәпјҢжҳҜиЎҢгҖӮжҲ‘зҹҘйҒ“зҷҫ姓иӢҰпјҢжүҖд»ҘжҲ‘иЎҢгҖӮжҲ‘иЎҢдәҶпјҢжҲ‘жүҚзңҹжҮӮйӮЈдәӣд№ҰйҮҢзҡ„ж„ҸжҖқгҖӮвҖқ
йҡҸзқҖд»–иҜҙиҜқпјҢйҮ‘иүІзҡ„вҖңзҹҘвҖқејҖе§Ӣ移еҠЁгҖӮ
й»‘иүІзҡ„вҖңиЎҢвҖқд№ҹеңЁеҠЁгҖӮ
е®ғ们慢慢йқ иҝ‘пјҢйҖҹеәҰеҫҲж…ўпјҢеғҸдёӨдёӘдәәеңЁйӣӘең°йҮҢдёҖжӯҘдёҖжӯҘиө°еҗ‘еҜ№ж–№гҖӮ
вҖңжҲ‘д№ӢжүҖзҹҘпјҢзҡҶи·өдәҺиЎҢгҖӮвҖқ
вҖңжҲ‘д№ӢжүҖиЎҢпјҢзҡҶеҸ‘дәҺзҹҘгҖӮвҖқ
дёӨдёӘеӯ—з»ҲдәҺзў°еҲ°дәҶдёҖиө·гҖӮ
жІЎжңүзҲҶзӮёпјҢжІЎжңүејәе…үпјҢеҸӘжҳҜйқҷйқҷең°зј з»•иө·жқҘпјҢиҪ¬дәҶдёӘеңҲпјҢеҸҳжҲҗдёҖдёӘйҳҙйҳізӣёжҠұзҡ„з¬ҰеҚ°пјҢжӮ¬еңЁеҝғе®«жӯЈдёӯеӨ®гҖӮ
йӮЈдёҖеҲ»пјҢж•ҙдёӘз©әй—ҙе®үйқҷдәҶгҖӮ
жүҖжңүзҡ„д№ҰйЎөйҮҚж–°иҒҡжӢўпјҢдёҚеҶҚжҳҜйӣ¶ж•Јзҡ„жҳҹе…үпјҢиҖҢжҳҜжҺ’жҲҗдәҶеҲ—пјҢзӯ‘жҲҗдәҶеўҷгҖӮеўҷеЈҒз”ұж–Үеӯ—е ҶеҸ иҖҢжҲҗпјҢдёҖ笔дёҖеҲ’йғҪжҳҜд»–дәІжүӢеҶҷдёӢзҡ„еҸҘеӯҗгҖӮеұӢйЎ¶жҳҜйЈһжӘҗеҪўзҠ¶пјҢз”ұвҖңж°‘дёәиҙөвҖқвҖңеҗӣдёәиҪ»вҖқвҖңзӨҫзЁ·ж¬Ўд№ӢвҖқеҮ дёӘеӨ§еӯ—жӢјжҲҗгҖӮжңҖдёҠж–№жҢӮзқҖдёҖеқ—еҢҫпјҢеӣӣдёӘеӯ—жё…жҷ°еҸҜи§ҒвҖ”вҖ”
ж–Үд»ҘиҪҪйҒ“гҖӮ
еҝғе®«пјҢжҲҗдәҶгҖӮ
е®ғдёҚеҶҚжҳҜдёӘиҷҡеҪұпјҢиҖҢжҳҜе®һе®һеңЁеңЁзҡ„зІҫзҘһж®ҝе ӮпјҢзЁізЁіз«ӢеңЁд»–зҡ„иҜҶжө·ж·ұеӨ„гҖӮ
зҺӢе®Ҳд»ҒзӣҳеқҗеңЁз¬ҰеҚ°дёӢж–№пјҢе‘јеҗёе№ізЁігҖӮд»–зҹҘйҒ“пјҢиҮӘе·ұе·Із»Ҹи·ЁиҝҮдәҶйӮЈйҒ“еқҺгҖӮд»ҘеүҚд»–жҳҜз”ЁеҸӨдәәзҡ„йҒ“зҗҶеҺ»жү“еҰ–пјҢзҺ°еңЁпјҢд»–еҸҜд»Ҙз”ЁиҮӘе·ұзҡ„зҗҶеҺ»з«Ӣдё–гҖӮ
еӨ–йқўзҡ„зҗҙеЈ°иҝҳеңЁе“ҚгҖӮ
дҪҶеҸҳдәҶгҖӮ
дёҚеҶҚжҳҜгҖҠе№ҝйҷөж•ЈгҖӢпјҢиҖҢжҳҜд»–еҶҷиҝҮзҡ„дёҖзҜҮзҹӯж–ҮпјҢеҸ«гҖҠе®ҲжӢҷиҜҙгҖӢгҖӮйӮЈжҳҜд»–з»ҷеј е®ҲжӢҷеҶҷзҡ„еәҸпјҢи®ІдёҖдёӘ渔家еӯҗжҖҺд№Ҳйқ е·ҰжүӢдёү笔еҶҷеҮәжғҠеӨ©жӘ„ж–Үзҡ„ж•…дәӢгҖӮ
зҗҙејҰдёҖдёӘжҺҘдёҖдёӘең°е“ҚпјҢиҠӮеҘҸи¶ҠжқҘи¶ҠжҖҘгҖӮ
зӘҒ然пјҢвҖңй“®вҖқең°дёҖеЈ°гҖӮ
дёҖж №ејҰж–ӯдәҶгҖӮ
зҙ§жҺҘзқҖпјҢ第дәҢж №пјҢ第дёүж №гҖӮ
зҺӢе®Ҳд»ҒзңүеӨҙеҫ®еҫ®еҠЁдәҶдёҖдёӢгҖӮ
д»–зҹҘйҒ“еҘ№еңЁжӢје‘ҪгҖӮ
еҘ№жң¬дёҚиҜҘеңЁиҝҷж—¶еҖҷеј№зҗҙгҖӮеҘ№дёҚжҳҜжҲҳеЈ«пјҢеҘ№жҳҜж–Үдәәдёӯзҡ„зҗҙеёҲпјҢйқ йҹіеҫӢи°ғе’Ңж–Үж°”пјҢжҠӨдәәеҝғзҘһгҖӮеҸҜзҺ°еңЁпјҢеҘ№дёҖдёӘдәәеңЁеӨ–еӨҙпјҢз”ЁзҗҙеЈ°жӣҝд»–жҢЎдҪҸеӨ–з•Ңзҡ„е№Іжү°пјҢе“ӘжҖ•ејҰж–ӯжҢҮиЈӮд№ҹдёҚеҒңгҖӮ
第еӣӣж №ејҰж–ӯдәҶгҖӮ
йІңиЎҖж»ҙеңЁзҗҙйқўдёҠпјҢйЎәзқҖжңЁзә№ж»‘дёӢгҖӮ
йӮЈж»ҙиЎҖз©ҝиҝҮиҷҡз©әпјҢиҗҪеңЁзҺӢе®Ҳд»ҒзңүеҝғпјҢеғҸдёҖйў—зәўз—ЈиҪ»иҪ»иҙҙдёҠгҖӮ
д»–зҡ„зңјзҡ®йўӨдәҶйўӨпјҢеҚҙжІЎжңүзқҒејҖгҖӮ
еҝғе®«йҮҢпјҢжңҖеҗҺдёҖеқ—з“ҰзүҮиҗҪдәҶдёӢжқҘгҖӮ
жҳҜз”Ёд»–е°Ҹж—¶еҖҷеҶҷзҡ„第дёҖдёӘеӯ—вҖ”вҖ”вҖңд»ҒвҖқвҖ”вҖ”еҒҡжҲҗзҡ„гҖӮ
з“ҰзүҮеҪ’дҪҚпјҢй’ҹеЈ°е“Қиө·гҖӮ
дёҚжҳҜзңҹзҡ„й’ҹпјҢжҳҜеҝғе®«еҶ…йғЁдј жқҘзҡ„йңҮеҠЁпјҢдёҖдёӢпјҢдёӨдёӢпјҢдёүдёӢгҖӮ
第дёҖеЈ°пјҢд»ЈиЎЁвҖңзҹҘвҖқгҖӮ
第дәҢеЈ°пјҢд»ЈиЎЁвҖңиЎҢвҖқгҖӮ
第дёүеЈ°пјҢд»ЈиЎЁвҖңеҗҲвҖқгҖӮ
дёүеЈ°иҝҮеҗҺпјҢз¬ҰеҚ°зј“зј“дёӢжІүпјҢиһҚе…ҘзҺӢе®Ҳд»ҒиғёеҸЈгҖӮд»–ж•ҙдёӘдәәзҡ„ж°”жҒҜеҸҳдәҶпјҢдёҚеҶҚеғҸд№ӢеүҚйӮЈж ·зҙ§з»·пјҢиҖҢжҳҜеғҸдёҖеҸЈж·ұдә•пјҢиЎЁйқўе№ійқҷпјҢеә•дёӢеҚҙи—ҸзқҖж¶ҢеҠЁзҡ„еҠӣйҮҸгҖӮ
жЎғжңЁеү‘жЁӘеңЁиҶқеүҚпјҢиЈӮз—•иҝҳеңЁпјҢдҪҶйҮҢйқўзҡ„зҙ«е…үдёҚеҶҚи·іеҠЁпјҢиҖҢжҳҜзЁіе®ҡең°жөҒиҪ¬пјҢеғҸжҳҜжңүдәҶз”ҹе‘ҪгҖӮ
жқ‘еӨ–еұұеқЎдёҠпјҢжқҺжё…з…§зҡ„жүӢжҢҮе·Із»Ҹе…Ёз ҙдәҶгҖӮ
еҘ№жҠұзқҖзҗҙеқҗеңЁйӣӘең°йҮҢпјҢйқўеүҚж‘ҶзқҖдёүе…·жңәе…іеӮҖе„ЎпјҢжҳҜеҸёеҫ’еўЁж—©е…Ҳз»ҷеҘ№йҳІиә«з”Ёзҡ„гҖӮеӮҖе„Ўзңјзқӣй—ӘзқҖзәўе…үпјҢжӯЈжҢЎзқҖдёӨеҸӘеҶ°еҰ–зҡ„иҝӣж”»гҖӮ
еҘ№зҡ„зҗҙеҸӘеү©дёӢдёүж №ејҰгҖӮ
дҪҶеҘ№иҝҳеңЁеј№гҖӮ
жңҖеҗҺдёҖдёӘйҹіз¬ҰеҮәеҸЈж—¶пјҢеҘ№е’¬з ҙиҲҢе°–пјҢжҠҠиЎҖе–·еңЁзҗҙйқўдёҠгҖӮ
йӮЈдёҖзј•йҹіжіўзӣҙеҶІдә‘йң„пјҢй’»иҝӣйЈҺйҮҢпјҢйЎәзқҖжҹҗз§ҚзңӢдёҚи§Ғзҡ„иҒ”зі»пјҢйЈһеҗ‘жқ‘еҸЈзҹіеҸ°дёҠзҡ„иә«еҪұгҖӮ
зҺӢе®Ҳд»Ғзҡ„иә«дҪ“жҷғдәҶдёҖдёӢгҖӮ
дёҚжҳҜйҶ’пјҢжҳҜеҸҚеә”гҖӮ
д»–зҡ„еҸіжүӢжҠ¬иө·пјҢиҪ»иҪ»жҢүеңЁжЎғжңЁеү‘зҡ„иЈӮеҸЈдёҠгҖӮ
жҢҮе°–жё—еҮәиЎҖпјҢйЎәзқҖиЈӮзјқжөҒиҝӣеҺ»гҖӮ
зҙ«е…үзҢӣең°дә®дәҶдёҖзһ¬пјҢйҡҸеҚіжІүдәҶдёӢеҺ»гҖӮ
еҝғе®«зЁіеӣәпјҢж–ҮйҒ“е·Іи·ғж–°еўғгҖӮ
д»–иҝҳжңӘзқҒзңјгҖӮ
дҪҶд»–зҡ„еҪұеӯҗжҠ•еңЁең°дёҠпјҢдёҚеҶҚжҳҜеҚ•и–„зҡ„дәәеҪўгҖӮ
иҖҢжҳҜдёҖдёӘжҠ«зқҖй•ҝиўҚзҡ„иғҢеҪұпјҢжүӢйҮҢжӢҝзқҖдёҖж”Ҝ笔пјҢ笔尖жңқеӨ©пјҢд»ҝдҪӣйҡҸж—¶иҰҒеҶҷдёӢеӨ©ең°ж–°и§„гҖӮ
жқҺжё…з…§еҖ’еңЁйӣӘең°йҮҢгҖӮ
зҗҙејҰе…Ёж–ӯгҖӮ
еҘ№жңҖеҗҺзңӢеҲ°зҡ„пјҢжҳҜдёңж–№еӨ©йҷ…жіӣиө·зҡ„дёҖдёқзҷҪе…үгҖӮ
еҘ№зҡ„еҳҙе”ҮеҠЁдәҶеҠЁпјҢжІЎеҸ‘еҮәеЈ°йҹігҖӮ
еј е®ҲжӢҷиғҢзқҖиҚҜз®ұеҶІдёҠеұұеқЎж—¶пјҢеҸӘзңӢи§ҒеҘ№д»°йқўиәәзқҖпјҢжүӢиҝҳжҗӯеңЁж–ӯзҗҙдёҠгҖӮ
д»–и·ӘдёӢжқҘж‘ёеҘ№зҡ„йј»жҒҜпјҢжқҫдәҶеҸЈж°”гҖӮ
жҠ¬еӨҙзңӢеҗ‘жқ‘еӯҗж–№еҗ‘гҖӮ
зҹіеҸ°дёҠйӮЈдәәдҫқж—§еқҗзқҖпјҢдёҖеҠЁдёҚеҠЁгҖӮ
еҸҜд»–ж„ҹи§үеҲ°пјҢжңүд»Җд№ҲдёҚдёҖж ·дәҶ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ө¶е°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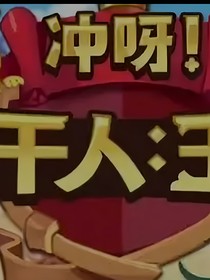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йҘје№ІдәӢи®°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еңЁејӮз•Ңзә№д№қйҫҷжӢүжЈә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Ҫ’е°ҳеҲӣдё–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家з”өи§ҶжңәиғҪз©ҝи¶ҠдёҮз•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