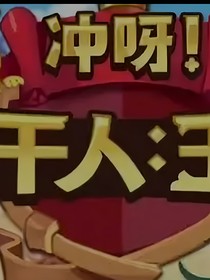第65章:智者远道来,求道护村计
天刚亮,门外的脚步声停了。
王守仁正坐在桌边,手里还捏着那张写过“辰时初,祭坛有人”的纸条。药罐里的残渣已经凉透,他没再喝。
门被敲了三下。
不是阿七那种急促的节奏,也不是张守拙的轻叩。这声音稳,慢,像是来人不怕等。
他放下纸条,起身开门。
一个驼背老人站在门口,披着粗麻斗篷,脸上沟壑纵横,像被人用刀刻过。他拄着一根乌木拐杖,杖身密布纹路,有些像卦象,又不像。
身后,几个村民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个孩子,脸色青白,嘴唇发紫,呼吸若有若无。
“先生。”老人开口,声音沙哑,“我叫坎离子,从五里坡来。这孩子昨夜突然昏倒,村中郎中说脉息全无,却未断气。我们听说您能驱邪救命,特来求您一看。”
王守仁没说话,低头看向孩子。
他伸手探向孩童额头,指尖微光一闪,一缕金气缓缓渗入其眉心。片刻后,他收回手,眉头皱起。
“是夺舍术。”他说,“有人想把他魂魄挤出去,自己钻进来。还好没完成,不然现在睁眼的就不是他了。”
村民一片哗然。
“妖人又来了?”
“是不是县令干的?”
“烧了吧,别让邪祟沾上村子!”
王守仁转身走进屋,拿起药罐放在担架旁。罐身上“克己复礼”四字微微发亮,压住了孩子身上隐隐浮动的一层黑气。
“谁敢动他,我就让他也躺下去。”他声音不高,但没人再敢吭声。
他走到人群前,站定。
“这孩子还能救。夺舍的人怕正念,你们只要安静守着,心里别乱想,别怕,也别恨。邪术靠人心缝隙钻进来,你们心稳,他就进不去。”
有人点头,有人抹泪,还有人往后退了两步。
王守仁回头看了眼老人:“你带他走这么远,不怕路上出事?”
老人摇头:“我不怕。我走山路三十年,夜里鬼哭狼嚎也不绕道。但我怕今天晚一步,这孩子就没了。”
王守仁盯着他:“你知道这是夺舍术?”
“我知道。”老人低声,“三夜之间,七村十二童失踪,都是这样。有的醒来变了性情,有的再没醒。我去过三座道观,两处书院,没人肯管。有人说这是天罚,有人说该献祭平灾……可他们不是妖,是人啊!”
王守仁沉默。
他看向那根拐杖。杖头隐约有两道纹路在转,一深一浅,一明一暗,像是水火相济,又像阴阳轮替。
他忽然问:“你懂《易》?”
“不懂。”老人说,“但我爷爷传下这根杖,说它能感应天地动静。昨晚它一直在震,指向龙场驿。我知道,这里有能救人的人。”
王守仁没再问。
他蹲下身,手指在空中划了四个字:守中抱一。
文气凝成虚影,缓缓沉入孩童胸口。孩子的呼吸慢慢平稳,脸上青色淡了些。
围观村民松了口气。
王守仁站起来,对抬担架的人说:“找个干净屋子,把他放好,门口挂艾草,点柏枝香。一天换三次水,水里加半勺盐、一片姜。不准任何人单独靠近他。”
村民们应声照办,小心翼翼抬着孩子走了。
院子里只剩王守仁和老人。
晨风吹过,药罐边缘结了一层薄霜,被阳光一照,裂开几道细纹。
老人忽然双膝跪地。
动作干脆,没有犹豫。
“先生。”他抬头,眼里有光,“我想学文气诀。”
王守仁没拦他。
“为什么?”
“为了护村。”老人握紧拐杖,“我们山民不信官,不信神,只信能挡在前面的人。可这次来的不是野兽,不是土匪,是能钻进人脑袋里的东西。我们打不了,跑不掉,连怎么死都不知道。您能救一个,救不了十二个。您能来一次,不能天天守着。”
王守仁看着他:“练文气会伤身。普通人强行引气入体,轻则吐血,重则瘫痪。我没师父教过这些,我自己也是拿命试出来的。”
“我知道。”老人说,“但我七十岁了,身子早烂透了。儿子死在矿上,孙子被邪术夺了魂,媳妇疯了三年。我没啥可赔的。要是能学会一点点,能在村里布个阵,能让孩子们多活一夜……我这条命,够本了。”
王守仁没说话。
他走到院角,捡起一块碎瓦片,在地上画了个圈。
“文气不是武功,练了不会飞檐走壁。它是念头,是意志,是你相信什么,就能发出什么光。你们要的不是杀招,是守住心神的办法。”
老人点头。
“我可以教。”王守仁说,“明天辰时,村口老槐树下。我讲养气入门,怎么静坐,怎么守神,怎么用意念挡住外邪。只讲一遍,听懂多少算多少。不准私下乱练,不准传给外人,不准打着我的名号行事。违者,我亲手废了他。”
老人猛地磕了个头。
“谢先生!”
“别谢。”王守仁扶起他,“你先告诉我,这夺舍术是从哪来的?有没有规律?什么时候发作?”
老人站起身,喘了口气:“每到月圆前后三天,必定出事。地点都在村子北口,靠近那片乱石岗。孩子都是半夜失踪,第二天在井边或祠堂出现,像睡着了一样。可醒来后,有的不认识爹娘,有的半夜爬起来写满墙鬼画符。”
王守仁眼神一凝。
“写的是什么?”
“看不懂。”老人摇头,“像是字,又不是汉字。弯弯曲曲,像虫爬。”
王守仁想起什么。
他快步回屋,从书架抽出一本《齐民要术》,翻到第三页。夹着的油纸还在,上面是他昨夜写下的几行笔记。
其中一行写着:“申时三刻,祭坛机关开启,血槽注满。”
他盯着那句话,忽然笑了。
原来不是骗县令。
是县令在配合别人演戏。
真正的猎手,根本不在县城。
他转身走出屋子,对老人说:“你回去准备场地。我要在村口画一个‘镇魂阵’,用文气连通地脉。你带几个人,把全村的铜铃、铁锅、陶瓮都搬来,围成一圈。再找十二个没生过病的孩子,辰时站到阵眼里。”
老人愣住:“这……有用吗?”
“不知道。”王守仁说,“但总比等着他们来抓人强。”
老人重重点头,转身要走。
“等等。”王守仁叫住他,“你那根杖,借我看看。”
老人迟疑一下,递了过去。
王守仁接过拐杖,手指抚过杖身纹路。那些符号看似杂乱,实则暗合节气流转。他在杖头一处凹陷停下。
那里有个极小的印记,形如眼睛,中间一点红。
像血。
又像朱砂。
他没说话,把杖还了回去。
“明天别空手来。”他说,“带上你的全部本事。我要知道,这根杖到底是谁留下的。”
老人握紧拐杖,低头应下。
太阳升得更高了。
王守仁站在门口,看着老人蹒跚离去的背影。
他摸了摸腰间的桃木剑。
剑柄还是湿的。
昨夜露水打过,还没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