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з« пјҡзңјзәҝжҡ—жҪңе…ҘпјҢеҒҮдҝЎиҜұеёҲиЎҢ
еӨңйЈҺд»ҺеәҹеўҹдёҠеҗ№иҝҮпјҢеҚ·иө·еҮ зүҮз„ҰзәёгҖӮзҺӢе®Ҳд»Ғйқ зқҖж®Ӣзў‘еқҗзқҖпјҢзңјзҡ®жІүйҮҚпјҢжүӢжҢҮиҝҳжҗӯеңЁж–ӯеү‘дёҠгҖӮд»–жІЎзқЎпјҢеҸӘжҳҜй—ӯзқҖзңји°ғжҒҜгҖӮзҷҫ姓们еӣҙеңЁдёҚиҝңеӨ„пјҢжңүдәәй“әдәҶиҚүеёӯпјҢжңүдәәе®ҲзқҖзҒ«е ҶгҖӮйӮЈдёүдёӘзҒ°зғ¬еҶҷжҲҗзҡ„еӯ—вҖ”вҖ”вҖңж°‘дёәиҙөвҖқвҖ”вҖ”иҝҳеңЁз©әдёӯйЈҳзқҖпјҢжІЎдәәж•ўзў°гҖӮ
еј е®ҲжӢҷеқҗеңЁдёҖж—ҒпјҢе·ҰжүӢдёүж”Ҝ笔еӨ№еңЁжҢҮй—ҙпјҢеҸіиҮӮж—§дјӨйҡҗйҡҗдҪңз—ӣгҖӮд»–зӣҜзқҖе…Ҳз”ҹзҡ„иғҢеҪұпјҢдёҖеҸҘиҜқжІЎиҜҙгҖӮ
иҝҮдәҶи®ёд№…пјҢзҺӢе®Ҳд»ҒзқҒејҖзңјпјҢж…ўж…ўз«ҷиө·иә«гҖӮи…ҝжңүзӮ№иҪҜпјҢдҪҶд»–ж’‘дҪҸдәҶгҖӮд»–жӢҚдәҶжӢҚиЎЈдёҠзҡ„зҒ°пјҢиө°еҗ‘йӮЈй—ҙеӢүејәиҝҳиғҪз”Ёзҡ„д№ҰжҲҝгҖӮй—ЁжҳҜжӯӘзҡ„пјҢзӘ—зәёз ҙдәҶеҮ дёӘжҙһпјҢжЎҢдёҠе ҶзқҖзғ§дәҶдёҖеҚҠзҡ„д№ҰзЁҝе’ҢеҮ еј иҚүзәёгҖӮ
д»–еқҗдёӢпјҢзӮ№зҒҜпјҢжҸҗ笔гҖӮ
гҖҠй©ұйӮӘдёүзҜҮгҖӢеҫ—йҮҚжҠ„дёҖйҒҚпјҢеҲҶз»ҷеҗ„жқ‘гҖӮиҝҷдәӢдёҚиғҪжӢ–гҖӮеҰ–иҷҪйҷӨпјҢдәәеҝғжңӘзЁіпјҢиӢҘеҶҚжңүйӮӘзҘҹеҖҹжңәдҪңд№ұпјҢзҷҫе§“ж— йҳІпјҢеҸӘдјҡеҶҚжӯ»дәәгҖӮ
д»–дёҖ笔дёҖеҲ’ең°еҶҷпјҢеӯ—иҝ№з«ҜжӯЈеҚҙдёҚеҚҺдёҪгҖӮеҶҷеҲ°дёҖеҚҠпјҢе’іе—ҪдәҶеҮ еЈ°пјҢиғёеҸЈй—·еҫ—ж…ҢгҖӮд»–д»ҺжҖҖйҮҢж‘ёеҮәйқ’з“·иҚҜзҪҗпјҢе–қдәҶдёҖеҸЈпјҢ继з»ӯеҶҷгҖӮ
еӨ–еӨҙжІЎдәҶеҠЁйқҷгҖӮзҷҫ姓йғҪзҙҜдәҶпјҢйҷҶз»ӯжӯҮдёӢгҖӮеҸӘжңүиҝңеӨ„еұұжһ—еҒ¶е°”дј жқҘйёҹеҸ«гҖӮ
е°ұеңЁиҝҷж—¶пјҢйҷўеўҷеӨ–дёҖйҒ“й»‘еҪұиҪ»иҪ»и·ғе…ҘгҖӮйӮЈдәәз©ҝзқҖзҹӯжү“пјҢи„ёдёҠи’ҷзқҖеёғе·ҫпјҢеҠЁдҪңиҪ»е·§еҚҙз•Ҙжҳҫз”ҹз–ҸгҖӮд»–иҙҙзқҖеўҷж №иө°пјҢйҒҝејҖжңҲе…үпјҢзӣҙеҘ”д№ҰжҲҝеҗҺзӘ—гҖӮ
зӘ—жҲ·жІЎе…ідёҘпјҢз•ҷдәҶжқЎзјқгҖӮд»–дјёжүӢдёҖжҺЁпјҢзј“зј“жӢүејҖпјҢзҝ»иә«иҝӣеҺ»пјҢиҗҪең°ж—¶иё©еҲ°дёҖеқ—зўҺз“ҰпјҢеҸ‘еҮәиҪ»еҫ®е“ҚеҠЁгҖӮ
зҺӢе®Ҳд»Ғ笔尖йЎҝдәҶдёҖдёӢпјҢжІЎжҠ¬еӨҙгҖӮ
йӮЈдәәеұҸдҪҸе‘јеҗёпјҢи№ІеңЁд№Ұжһ¶ж—ҒпјҢиҝ…йҖҹд»ҺжҖҖдёӯжҺҸеҮәдёҖе°ҒдҝЎпјҢеЎһиҝӣдёҖжң¬жіӣй»„зҡ„ж—§д№ҰйҮҢгҖӮйӮЈд№Ұе°ҒйқўеҶҷзқҖгҖҠйҪҗж°‘иҰҒжңҜгҖӢпјҢиҫ№и§’зЈЁжҚҹпјҢжҳҫ然жҳҜеёёзҝ»д№Ӣзү©гҖӮ
дҝЎе°ҒдёҠжңүжңұеҚ°пјҢзӣ–зқҖвҖңе·һеәңжҖҘд»ӨвҖқеӣӣдёӘеӯ—гҖӮ
д»–еҲҡеЎһеҘҪпјҢжӯЈиҰҒйҖҖпјҢй—ЁеӨ–дј жқҘи„ҡжӯҘеЈ°гҖӮ
дёҚжҳҜзҺӢе®Ҳд»Ғзҡ„гҖӮ
жҳҜеј е®ҲжӢҷжқҘдәҶгҖӮд»–жҠұзқҖдёҖеқ—ж–°еҲ»еҘҪзҡ„зҹіжқҝжӢ“зүҮпјҢеҮҶеӨҮи®©е…Ҳз”ҹиҝҮзӣ®гҖӮи§Ғд№ҰжҲҝзҒҜдә®пјҢдҫҝжҺЁй—ЁиҖҢе…ҘгҖӮ
й—ЁдёҖејҖпјҢеұӢеҶ…зғӣе…үжҷғдәҶжҷғгҖӮ
зңјзәҝз«ӢеҲ»зј©иә«иәІеҲ°д№ҰжЎҲеҗҺпјҢи№ІеңЁең°дёҠдёҚж•ўеҠЁгҖӮ
еј е®ҲжӢҷиҝӣй—ЁпјҢйЎәжүӢжҠҠжӢ“зүҮж”ҫеңЁжЎҢдёҠпјҢзӣ®е…үжү«иҝҮд№Ұе ҶгҖӮд»–зңӢи§ҒйӮЈжң¬гҖҠйҪҗж°‘иҰҒжңҜгҖӢжңүзӮ№жӯӘпјҢжҠҪеҮәжқҘжғіжү¶жӯЈпјҢз»“жһңдёҖйЎөзәёж»‘дәҶеҮәжқҘвҖ”вҖ”жӯЈжҳҜйӮЈе°Ғи°ғд»ӨгҖӮ
д»–зҡұзңүпјҢжӢҝиө·дҝЎзңӢдәҶдёҖзңјгҖӮ
жңұеҚ°йІңзәўпјҢж–Үеӯ—е·Ҙж•ҙпјҡвҖңеҘүе·һеәңд»ӨпјҢеҸ¬зҺӢе®Ҳд»ҒеҚіеҲ»иөҙеҗҺеұұзҘӯеқӣпјҢйқўйҷҲеҰ–жӮЈе§Ӣжң«пјҢдёҚеҫ—延иҜҜгҖӮвҖқ
д»–зӣҜзқҖйӮЈжһҡеҚ°зңӢдәҶеҮ з§’пјҢеҝҪ然жҠҪеҮәдёҖж”Ҝ笔пјҢ用笔尖иҪ»иҪ»еҲ®дәҶеҲ®еҚ°жіҘиҫ№зјҳгҖӮ
зҒҜе…үдёӢпјҢеҚ°зә№з»ҶеӨ„жө®зҺ°еҮәдёҖз»„иҠұзә№вҖ”вҖ”дёҖжңөзј жһқиҺІпјҢиҠұз“Јдёғз“ЈпјҢеҸ¶е°ҫеёҰй’©гҖӮ
д»–зңјзҘһдёҖеҮқгҖӮ
иҝҷзә№и·Ҝд»–и§ҒиҝҮгҖӮ
дёүеӨ©еүҚд»–йҖҒйұјеҺ»еҺҝиЎҷеҗҺеҺЁпјҢи·ҜиҝҮеӨ«дәәйҷўеӯҗпјҢзңӢи§ҒеҘ№жү“ејҖйҰ–йҘ°зӣ’еҸ–йҮ‘й’—гҖӮйӮЈзӣ’еӯҗзӣ–еӯҗдёҠпјҢе°ұеҲ»зқҖеҗҢж ·зҡ„иҠұгҖӮеҪ“ж—¶д»–иҝҳеӨҡзңӢдәҶдёӨзңјпјҢеӣ дёәйӮЈиҠұе°‘и§ҒпјҢдёғз“ЈиҺІиҠұдёҖиҲ¬еҸӘз”ЁдәҺиҙөж—ҸеҘізң·гҖӮ
зҺ°еңЁпјҢиҝҷеҚ°з«ҹе’ҢйҰ–йҘ°зӣ’дёҠзҡ„йӣ•иҠұдёҖжЁЎдёҖж ·пјҹ
д»–дҪҺеӨҙеҸҲзңӢдҝЎзәёжқҗиҙЁвҖ”вҖ”жҳҜжҷ®йҖҡз«№зәёпјҢдҪҶиҫ№и§’еҫ®еҫ®еҸ‘и“қпјҢеғҸжҳҜжіЎиҝҮиҚҜж°ҙгҖӮиҝҷз§ҚзәёпјҢе®ҳеәңдёҚз”ЁпјҢеҖ’жҳҜеҺҝд»ӨеӨ«дәәе–ңж¬ўжӢҝжқҘеҢ…йҰҷж–ҷгҖӮ
д»–жІЎеҠЁеЈ°иүІпјҢжҠҠдҝЎж”ҫеӣһеҺҹеӨ„пјҢиҪ¬еӨҙзңӢеҗ‘зҺӢе®Ҳд»ҒпјҡвҖңе…Ҳз”ҹгҖӮвҖқ
зҺӢе®Ҳд»ҒжҠ¬зңјгҖӮ
вҖңиҝҷдҝЎвҖҰвҖҰжҳҜи°ҒйҖҒжқҘзҡ„пјҹвҖқ
вҖңжҲ‘没收еҲ°дҝЎгҖӮвҖқзҺӢе®Ҳд»Ғж‘ҮеӨҙпјҢвҖңдҪ жүӢдёҠйӮЈе°ҒпјҢжҲ‘д№ҹжҳҜ第дёҖж¬Ўи§ҒгҖӮвҖқ
еј е®ҲжӢҷеЈ°йҹіеҺӢдҪҺпјҡвҖңеҸҜиҝҷеҚ°пјҢжҳҜд»ҺеҺҝд»ӨеӨ«дәәйҰ–йҘ°зӣ’зӣ–дёҠжӢ“дёӢжқҘзҡ„гҖӮжҲ‘и®Өеҫ—йӮЈжңөдёғз“ЈиҺІгҖӮвҖқ
зҺӢе®Ҳд»ҒзңјзҘһдёҖжІүгҖӮ
д»–ж”ҫдёӢ笔пјҢзј“зј“иө·иә«гҖӮ
е°ұеңЁиҝҷж—¶пјҢиә«еҗҺд№Ұжһ¶еҗҺдј жқҘдёҖдёқиЎЈж–ҷж‘©ж“Ұзҡ„еЈ°йҹігҖӮ
дёӨдәәеҗҢж—¶иҪ¬еӨҙгҖӮ
з©әиҚЎиҚЎзҡ„д№ҰжҲҝпјҢеҸӘжңүзғӣзҒ«и·іеҠЁгҖӮ
дҪҶеј е®ҲжӢҷе·Із»ҸеҶІдәҶиҝҮеҺ»пјҢдёҖи„ҡиёўзҝ»д№Ұжһ¶гҖӮдёҖе Ҷж—§д№Ұе“—е•ҰеҖ’дёӢпјҢйңІеҮәеҗҺйқўиң·зј©зҡ„дәәеҪұгҖӮ
зңјзәҝзҢӣең°еј№иө·пјҢиҪ¬иә«е°ұеҫҖзӘ—еҸЈи·‘гҖӮ
зҺӢе®Ҳд»ҒдёҖжӯҘи·ЁеҮәпјҢжЎғжңЁеү‘жЁӘеңЁиғёеүҚпјҢжӢҰдҪҸеҺ»и·ҜгҖӮ
йӮЈдәәзЎ¬з”ҹз”ҹеҲ№дҪҸи„ҡпјҢйўқеӨҙеҶ’жұ—гҖӮ
еј е®ҲжӢҷд»ҺиғҢеҗҺи·ғдёҠжҲҝжўҒпјҢдёүж”Ҝ笔甩жүӢжҺ·еҮәпјҢй’үе…ҘзӘ—жЎҶпјҢе°Ғжӯ»йҖҖи·ҜгҖӮ
вҖңдҪ жҳҜеҺҝд»Өзҡ„дәәпјҹвҖқзҺӢе®Ҳд»Ғй—®гҖӮ
йӮЈдәәдёҚзӯ”пјҢжүӢдјёеҗ‘и…°й—ҙпјҢжғіж‘ёд»Җд№ҲдёңиҘҝгҖӮ
еј е®ҲжӢҷзңјз–ҫжүӢеҝ«пјҢйЈһиә«дёҠеүҚдёҖжҠҠжүЈдҪҸд»–жүӢи…•пјҢеҸҚжӢ§еҲ°иғҢеҗҺгҖӮйӮЈдәәй—·е“јдёҖеЈ°пјҢиў«жҢүеңЁең°дёҠгҖӮ
зҺӢе®Ҳд»Ғиө°иҝҮеҺ»пјҢи№ІдёӢпјҢжӢҝиө·йӮЈе°ҒдҝЎпјҢеҶҚж¬Ўжү“йҮҸжңұеҚ°гҖӮ
вҖңе·һеәңдёҚдјҡз”Ёиҝҷз§ҚзәёгҖӮвҖқд»–иҜҙпјҢвҖңд№ҹдёҚдјҡжӢҝеҰҮдәәйҰ–йҘ°зӣ’еҪ“еҚ°жЁЎгҖӮиҝҷжҳҜеҒҮзҡ„гҖӮвҖқ
д»–жҠ¬еӨҙзңӢзқҖзңјзәҝпјҡвҖңи°Ғи®©дҪ жқҘзҡ„пјҹжҳҜиҰҒжҲ‘еҺ»дәҶеҗҺеұұпјҢ然еҗҺе‘ўпјҹиў«еҹӢдјҸпјҹиҝҳжҳҜзӣҙжҺҘеҪ“жҲҗвҖҳз§ҒйҖҡеҰ–зұ»вҖҷеҪ“еңәж јжқҖпјҹвҖқ
йӮЈдәәе’¬зҙ§зүҷе…іпјҢдёҖеЈ°дёҚеҗӯгҖӮ
еӨ–йқўеҝҪз„¶дј жқҘдёүеЈ°жўҶеӯҗе“ҚгҖӮ
вҖңе’ҡгҖҒе’ҡгҖҒе’ҡгҖӮвҖқ
зј“ж…ўпјҢйҳҙжЈ®пјҢиҠӮеҘҸеҘҮзү№гҖӮ
зҺӢе®Ҳд»ҒзҢӣең°еӣһеӨҙпјҢзңӢеҗ‘зӘ—еӨ–гҖӮ
иҝҷеЈ°йҹід»–и®°еҫ—гҖӮ
дёүеӨ©еүҚиӣҮеҰ–зҺ°иә«еүҚеӨңпјҢд№ҹжҳҜиҝҷдёӘжү“жӣҙиҠӮеҘҸгҖӮеҪ“ж—¶д»–д»ҘдёәеҸӘжҳҜеҜ»еёёжҠҘж—¶пјҢжІЎеңЁж„ҸгҖӮеҸҜеҗҺжқҘеӣһжғіпјҢйӮЈжҷҡеҺҝд»ӨдёҚеңЁе·ЎеӨңпјҢй¬јеёӮзҲӘзүҷеҚҙеҮҶж—¶еҮәеҠЁпјҢж—¶й—ҙе®Ңе…ЁеҜ№еҫ—дёҠгҖӮ
иҝҷдёҚжҳҜе·§еҗҲгҖӮ
иҝҷжҳҜдҝЎеҸ·гҖӮ
д»–зӣҜзқҖзңјзәҝпјҡвҖңдҪ еҗ¬еҲ°дәҶеҗ—пјҹиҝҷдёүеЈ°жўҶеӯҗпјҢе’ҢйӮЈжҷҡдёҖжЁЎдёҖж ·гҖӮдҪ 们早е°ұдёІйҖҡеҘҪдәҶпјҢжҳҜдёҚжҳҜпјҹеҺҝд»Өе…»еҰ–пјҢдҪ д»¬дј дҝЎпјҢдёҖжӯҘжӯҘжҠҠжҲ‘еҫҖйҷ·йҳұйҮҢеј•гҖӮвҖқ
йӮЈдәәи„ёиүІеҸҳдәҶгҖӮ
еј е®ҲжӢҷз”ЁеҠӣдёҖжӢ§д»–иғіиҶҠпјҢйҖјд»–жҠ¬еӨҙпјҡвҖңиҜҙдёҚиҜҙпјҹеҶҚдёҚиҜҙпјҢжҲ‘жҠҠдҪ жү”иҝӣзҒ¶иҶӣйҮҢзғӨдәҶгҖӮвҖқ
вҖңжҲ‘вҖҰвҖҰжҲ‘еҸӘжҳҜеҘүе‘ҪиЎҢдәӢпјҒвҖқйӮЈдәәз»ҲдәҺејҖеҸЈпјҢеЈ°йҹіеҸ‘жҠ–пјҢвҖңеҺҝд»ӨеӨ§дәәиҜҙпјҢеҸӘиҰҒжҠҠдҝЎж”ҫиҝӣд№ҰжҲҝпјҢжҳҺеӨ©иҮӘ然жңүдәәжқҘжҺҘеә”вҖҰвҖҰиҮідәҺеҗҺз»ӯвҖҰвҖҰжҲ‘зңҹзҡ„дёҚзҹҘйҒ“пјҒвҖқ
вҖңжҺҘеә”пјҹвҖқзҺӢе®Ҳд»ҒеҶ·з¬‘пјҢвҖңжҺҘеә”зҡ„жҳҜеҲҖпјҢиҝҳжҳҜзҒ«пјҹвҖқ
вҖңжҲ‘дёҚзҹҘйҒ“пјҒзңҹзҡ„дёҚзҹҘйҒ“пјҒ他们еҸӘи®©жҲ‘д»ҠжҷҡеҠЁжүӢпјҢеҲ«зҡ„жІЎиҜҙпјҒвҖқ
зҺӢе®Ҳд»ҒзӣҜзқҖд»–зңӢдәҶеҮ з§’пјҢеҝҪ然伸жүӢпјҢжҸӯдёӢд»–и„ёдёҠи’ҷзҡ„еёғе·ҫгҖӮ
дёҖеј йҷҢз”ҹзҡ„и„ёпјҢдёүеҚҒеІҒдёҠдёӢпјҢеҳҙе”Үи–„пјҢзңји§’дёӢеһӮпјҢеғҸжҳҜеёёе№ҙеҒҡдҪҺдјҸе°Ҹзҡ„дәәгҖӮ
вҖңдҪ дёҚжҳҜе·®еҪ№гҖӮвҖқзҺӢе®Ҳд»ҒиҜҙпјҢвҖңдҪ жҳҜеҺҝд»Ө家зҡ„еҘҙжүҚгҖӮйӮЈеӨ©еңЁиЎҷй—ЁеҸЈпјҢжҲ‘и§ҒиҝҮдҪ з»ҷд»–зүө马гҖӮвҖқ
йӮЈдәәжө‘иә«дёҖйўӨпјҢдҪҺдёӢеӨҙгҖӮ
еј е®ҲжӢҷжқҫејҖжүӢпјҢжҠҠд»–жӢҪиө·жқҘпјҢжҢүеңЁеўҷдёҠпјҡвҖң既然жҳҜ家еҘҙпјҢйӮЈе°ұжӣҙиҜҘжё…жҘҡеҶ…幕гҖӮдҪ иҜҙдёҚеҮәжқҘпјҢжҲ‘е°ұеёҰдҪ еҺ»и§Ғзҷҫ姓гҖӮ让他们问问пјҢжҳҜи°ҒжҜҸжҷҡеҒ·еҒ·еҫҖеҺҝиЎҷеҗҺйҷўиҝҗй»‘еқӣеӯҗпјҹжҳҜи°ҒжҠҠз«Ҙз”·з«ҘеҘізҡ„еҗҚеӯ—и®°еңЁзәўеҶҢдёҠпјҹвҖқ
вҖңеҲ«пјҒвҖқйӮЈдәәж…ҢдәҶпјҢвҖңжҲ‘иҜҙвҖҰвҖҰжҲ‘иҜҙдёҖйғЁеҲҶвҖҰвҖҰдҪҶжҲ‘зҹҘйҒ“зҡ„зңҹдёҚеӨҡпјҒвҖқ
вҖңиҜҙгҖӮвҖқ
вҖңжҳҜеӨ«дәәвҖҰвҖҰжҳҜеӨ«дәәи®©жҲ‘жқҘзҡ„гҖӮеҘ№иҜҙеҸӘиҰҒжҠҠдҝЎж”ҫиҝӣеҺ»пјҢе°ұиғҪжҚўеҚҒдёӨ银еӯҗпјҢиҝҳиғҪи®©жҲ‘е„ҝеӯҗиҝӣиЎҷй—ЁеҪ“е·®вҖҰвҖҰжҲ‘дёҚзҹҘйҒ“жҳҜеҒҮдҝЎе•ҠпјҒжҲ‘зңҹдёҚзҹҘйҒ“пјҒвҖқ
вҖңеӨ«дәәпјҹвҖқзҺӢе®Ҳд»ҒзңҜзңјпјҢвҖңеҘ№дёҖдёӘеҰҮйҒ“дәә家пјҢиғҪжҢҮжҢҘе·һеәңи°ғд»ӨпјҹвҖқ
вҖңдёҚжҳҜеҘ№дёҖдёӘдәәвҖҰвҖҰиҝҳжңүйҷҲе…¬еӯҗвҖҰвҖҰе°ұжҳҜйҷҲе…ғжҳҠвҖҰвҖҰд»–еүҚеӨ©жқҘиҝҮеҺҝиЎҷпјҢе’ҢиҖҒзҲ·еҜҶи°ҲеҫҲд№…вҖҰвҖҰеҗҺжқҘвҖҰвҖҰеҗҺжқҘе°ұжңүдәҶиҝҷе°ҒдҝЎвҖҰвҖҰвҖқ
еј е®ҲжӢҷжҖ’еҗјпјҡвҖңеҸҲжҳҜйҷҲе…ғжҳҠпјҒиҝҷ家дјҷйҳҙйӯӮдёҚж•ЈпјҒвҖқ
зҺӢе®Ҳд»ҒжІЎиҜҙиҜқпјҢзӣ®е…үиҗҪеңЁйӮЈе°ҒдҝЎдёҠгҖӮ
йҷҲе…ғжҳҠжҸ’жүӢдәҶгҖӮ
иҝҷж„Ҹе‘ізқҖд»Җд№Ҳпјҹ
дёҚеҸӘжҳҜең°ж–№йҳҙи°ӢпјҢиҖҢжҳҜжңқе ӮеҠҝеҠӣе·Із»ҸејҖе§ӢеҠЁжүӢгҖӮйҷҲе…ғжҳҠиғҢеҗҺз«ҷзқҖйҰ–иҫ…пјҢиҖҢйҰ–иҫ…вҖҰвҖҰжӣҫжҳҜд»–еҗҢ科иҝӣеЈ«гҖӮ
д»–жҸЎзҙ§жЎғжңЁеү‘пјҢжҢҮиҠӮеҸ‘зҷҪгҖӮ
еј е®ҲжӢҷеҜҹи§үеҲ°д»–зҡ„ејӮж ·пјҢдҪҺеЈ°й—®пјҡвҖңе…Ҳз”ҹпјҢжҺҘдёӢжқҘжҖҺд№ҲеҠһпјҹвҖқ
зҺӢе®Ҳд»ҒзңӢзқҖиў«еҲ¶дҪҸзҡ„зңјзәҝпјҢеЈ°йҹіеҶ·дәҶдёӢжқҘпјҡвҖңе…Ҳе…іиө·жқҘгҖӮзӯүеӨ©дә®е®ЎгҖӮвҖқ
вҖңжҖ•д»–еҳҙзЎ¬гҖӮвҖқ
вҖңдёҚжҖ•гҖӮвҖқзҺӢе®Ҳд»Ғж·Ўж·ЎйҒ“пјҢвҖңдәәеҸӘиҰҒжҙ»еңЁиҝҷдё–дёҠпјҢе°ұжңүејұзӮ№гҖӮ银еӯҗгҖҒе„ҝеӯҗгҖҒжҖ§е‘ҪпјҢжҖ»жңүдёҖж ·иғҪж’¬ејҖд»–зҡ„еҳҙгҖӮвҖқ
д»–иҪ¬иә«иө°еҲ°жЎҢеүҚпјҢжӢҝиө·йӮЈе°ҒеҒҮдҝЎпјҢеңЁзғӣзҒ«дёҠзӮ№зҮғгҖӮ
зҒ«иӢ—зӘңиө·пјҢз…§дә®д»–еҚҠиҫ№и„ёгҖӮ
вҖң他们жғіи®©жҲ‘еҺ»еҗҺеұұгҖӮвҖқд»–иҜҙпјҢвҖңйӮЈжҲ‘е°ұеҒҸдёҚеҺ»гҖӮвҖқ
еј е®ҲжӢҷзӮ№еӨҙпјҡвҖңеҜ№пјҢе’ұ们д»ҘйқҷеҲ¶еҠЁгҖӮвҖқ
вҖңдёҚгҖӮвҖқзҺӢе®Ҳд»ҒзңӢзқҖзҒ«з„°пјҢвҖңжҲ‘иҰҒеҺ»гҖӮвҖқ
вҖңе•ҠпјҹвҖқ
вҖңжҲ‘еҺ»пјҢдҪҶдёҚжҳҜзҺ°еңЁгҖӮвҖқд»–е°Ҷзғ§е°Ҫзҡ„дҝЎзҒ°еҖ’е…ҘиҚҜзҪҗпјҢвҖңжҲ‘иҰҒ让他们д»Ҙдёәи®Ўи°Ӣеҫ—йҖһпјҢзӯү他们иҮӘе·ұжҠҠеә•зүҢдә®еҮәжқҘгҖӮвҖқ
еј е®ҲжӢҷж„ЈдҪҸпјҡвҖңжӮЁиҰҒе°Ҷи®Ўе°ұи®ЎпјҹвҖқ
зҺӢе®Ҳд»ҒжІЎеӣһзӯ”пјҢеҸӘжҳҜжҠҠиҚҜзҪҗзӣ–еҘҪпјҢж”ҫеӣһжҖҖйҮҢгҖӮ
д»–иө°еҲ°зӘ—еүҚпјҢжңӣзқҖжјҶй»‘зҡ„еұұжһ—гҖӮ
иҝңеӨ„пјҢеҸҲдј жқҘдёҖеЈ°жўҶеӯҗе“ҚгҖӮ
иҝҷж¬ЎжҳҜеӣӣеЈ°гҖӮ
иҠӮеҘҸеҸҳдәҶгҖӮ
д»–зңүеӨҙдёҖзҡұгҖӮ
еј е®ҲжӢҷд№ҹеҗ¬и§ҒдәҶпјҢдҪҺеЈ°й—®пјҡвҖңиҝҷж¬ЎдёҚдёҖж ·вҖҰвҖҰжҳҜдёҚжҳҜеҮәдәӢдәҶпјҹвҖқ
зҺӢе®Ҳд»ҒзӣҜзқҖеұұжһ—ж·ұеӨ„гҖӮ
зүҮеҲ»еҗҺпјҢд»–жҠ“иө·жЎғжңЁеү‘пјҢеӨ§жӯҘиө°еҮәд№ҰжҲҝгҖӮ
вҖңиө°пјҢеҺ»еҗҺеұұгҖӮвҖқ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ө¶е°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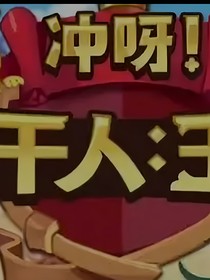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йҘје№ІдәӢи®°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еңЁејӮз•Ңзә№д№қйҫҷжӢүжЈә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Ҫ’е°ҳеҲӣдё–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家з”өи§ҶжңәиғҪз©ҝи¶ҠдёҮз•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