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з« пјҡеҰ–иЎҖеҢ–з”ҳйң–пјҢзҷҫ姓йӮӘж°”и§Ј
зҺӢе®Ҳд»ҒеҚ•иҶқи·ӘеңЁжіҘйҮҢпјҢж–ӯеү‘жҸ’иҝӣз„ҰеңҹпјҢйӣЁж°ҙйЎәзқҖд»–зҡ„еҸ‘жўўеҫҖдёӢж·ҢгҖӮд»–е–ҳзқҖж°”пјҢиғёеҸЈеғҸиў«зҹіеӨҙеҺӢдҪҸпјҢжҜҸеҗёдёҖеҸЈйғҪеёҰзқҖеҲәз—ӣгҖӮеҸіжүӢиҝҳж’‘зқҖең°йқўпјҢжҢҮе°–йҷ·иҝӣж№ҝжіҘпјҢжҢҮиҠӮжіӣзҷҪгҖӮ
еӨ©дёҠзҡ„дә‘жІЎж•ЈпјҢеҸҜйўңиүІеҸҳдәҶгҖӮдёҚеҶҚжҳҜйӮЈз§ҚжІүеҫ—и®©дәәе–ҳдёҚиҝҮж°”зҡ„й»‘пјҢдёӯй—ҙиЈӮејҖдёҖйҒ“еҸЈеӯҗпјҢйҖҸеҮәдёҖзӮ№е…үгҖӮйӣЁиҝҳеңЁдёӢпјҢжү“еңЁд»–и„ёдёҠпјҢжё©зҡ„гҖӮ
д»–еҲҡжғіжҠ¬жүӢжҠ№дёҖжҠҠи„ёдёҠзҡ„ж°ҙпјҢеҝҪ然еҜҹи§үдёҚеҜ№гҖӮ
еӨҙйЎ¶зҡ„йӣЁж»ҙи¶ҠжқҘи¶ҠеҜҶпјҢеҸҜиҗҪдёӢжқҘзҡ„и§Ұж„ҹеҸҳдәҶгҖӮдёҚжҳҜеҚ•зәҜзҡ„еҮүпјҢиҖҢжҳҜеёҰзқҖдёҖиӮЎи…Ҙж°”пјҢеғҸжҳҜй“Ғй”Ҳж··дәҶи…җиҚүзҡ„е‘ійҒ“гҖӮд»–зҢӣең°жҠ¬еӨҙпјҢзңӢи§Ғд№Ңдә‘ж·ұеӨ„зҝ»ж¶ҢзқҖжҡ—зәўпјҢдёҖж»ҙж»ҙж¶ІдҪ“д»Һз©әдёӯеқ иҗҪпјҢз ёеңЁйқ’зҹіжқҝдёҠпјҢеҸ‘еҮәвҖңж»ӢвҖқзҡ„иҪ»е“ҚпјҢеҶ’иө·зҷҪзғҹгҖӮ
иЎҖйӣЁгҖӮ
иӣҮеҰ–зҡ„ж®ӢиЎҖеҚҮдәҶз©әпјҢеҢ–жҲҗдәҶйӣЁгҖӮ
第дёҖж»ҙиҗҪеңЁдёҖдёӘиҖҒеҶңиӮ©еӨҙпјҢйӮЈзҡ®иӮӨз«ӢеҲ»жіӣеҮәйқ’з—•пјҢеғҸз”ҹдәҶйңүгҖӮиҖҒдәәй—·е“јдёҖеЈ°пјҢи·ӘеҖ’еңЁең°пјҢеҳҙиҫ№жәўеҮәй»‘жІ«гҖӮжҺҘзқҖжҳҜ第дәҢдёӘгҖҒ第дёүдёӘпјҢеҮЎжҳҜжІҫеҲ°йӣЁзҡ„дәәпјҢеӣӣиӮўжҠҪжҗҗпјҢзңјзҷҪзҝ»иө·пјҢжҺҢеҝғйӮЈдёӘй»‘зңјз¬ҰеҚ°еҸҲејҖе§Ӣи •еҠЁгҖӮ
зҺӢе®Ҳд»Ғе’¬зүҷз«ҷиө·пјҢи„ҡдёӢдёҖж»‘е·®зӮ№ж‘”еҖ’гҖӮд»–жү¶дҪҸж®Ӣзў‘пјҢе·ҰжүӢжҺўиҝӣжҖҖдёӯпјҢж‘ёеҲ°дәҶйӮЈеқ—еўЁзҺүзүҢгҖӮеҶ°еҮүзҡ„и§Ұж„ҹи®©д»–жё…йҶ’дәҶдёҖзһ¬гҖӮ
зүҢеӯҗдёҠеҲ»зқҖвҖңзҹҘиЎҢвҖқдёӨдёӘеӯ—пјҢжҳҜд»–еҪ“е№ҙиҗҪ第еҗҺпјҢжҒ©еёҲдәІжүӢдәӨз»ҷд»–зҡ„гҖӮйӮЈж—¶д»–иҜҙпјҡвҖңж–ҮдёҚеңЁзәёдёҠпјҢеңЁиЎҢдёӯгҖӮвҖқеҰӮд»Ҡд»–еҝ«иө°дёҚеҠЁдәҶпјҢеҸҜиҝҷеқ—зүҢеӯҗиҝҳеңЁгҖӮ
д»–з”ЁзүҷйҪҝж’•ејҖеҳҙе”ҮпјҢиЎҖйЎәзқҖеҳҙи§’жөҒдёӢпјҢжҠ№еңЁзҺүзүҢиғҢйқўгҖӮжүӢжҢҮйўӨжҠ–пјҢеҚҙиҝҳжҳҜе°Ҷе®ғдёҫиҝҮеӨҙйЎ¶гҖӮ
вҖңиҮҙзҹҘеңЁж јзү©вҖҰвҖҰвҖқ
еЈ°йҹіжІҷе“‘пјҢеҮ д№Һеҗ¬дёҚи§ҒгҖӮеҸҜйҡҸзқҖиҝҷеҸҘиҜқеҮәеҸЈпјҢзҺүзүҢзӘҒ然йңҮдәҶдёҖдёӢпјҢжө®еҲ°еҚҠз©әпјҢзј“зј“ж—ӢиҪ¬гҖӮеӣӣйҒ“е…үзә№д»ҺзүҢйқўе°„еҮәпјҢдәӨз»ҮжҲҗдјһзҠ¶пјҢзҪ©дҪҸж–№еңҶеҚҒеҮ дёҲгҖӮ
иЎҖйӣЁж’һдёҠе…ү幕пјҢеҸ‘еҮәвҖңе—Өе—ӨвҖқеЈ°пјҢеғҸзғ§зәўзҡ„зӮӯжөҮдәҶеҶ·ж°ҙгҖӮеҸҜиҝҷеұҸйҡңж’‘еҫ—еҗғеҠӣпјҢиҫ№зјҳе·Із»ҸејҖе§ӢеҸ‘жҡ—гҖӮ
зҺӢе®Ҳд»Ғзӣҳи…ҝеқҗдёӢпјҢжҠҠзҺүзүҢж”ҫеңЁжҺҢеҝғгҖӮд»–зҹҘйҒ“дёҚиғҪеҶҚзЎ¬жӢјдәҶгҖӮж–Үж°”еҝ«жІЎдәҶпјҢиә«дҪ“д№ҹеҝ«еһ®дәҶгҖӮдҪҶд»–иҝҳи®°еҫ—еј е®ҲжӢҷиҜҙиҝҮдёҖеҸҘиҜқпјҡвҖңе…Ҳз”ҹпјҢж–Үз« еҶҷеңЁзәёдёҠжҳҜжӯ»зҡ„пјҢеҶҷеңЁдәәеҝғйҮҢжүҚжҳҜжҙ»зҡ„гҖӮвҖқ
д»–й—ӯдёҠзңјпјҢй»ҳеҝөгҖҠдј д№ еҪ•гҖӢйҮҢзҡ„еҸҘеӯҗпјҡвҖңеҝғеҚізҗҶд№ҹгҖӮвҖқ
дёҖйҒҚпјҢдёӨйҒҚгҖӮ
иө·еҲқд»Җд№Ҳд№ҹжІЎеҸ‘з”ҹгҖӮиә«дёҠзҡ„йӣЁж°ҙиҝҳеңЁеҫҖдёӢжөҒпјҢзҷҫ姓зҡ„е’іе—ҪеЈ°ж–ӯж–ӯз»ӯз»ӯгҖӮеҸҜеҪ“他第дёүж¬Ўеҝөе®ҢпјҢжҺҢеҝғзҡ„зҺүзүҢзӘҒ然зғӯдәҶиө·жқҘгҖӮ
ең°дёӢжңүеҠЁйқҷгҖӮ
йӮЈдәӣиў«зҒ«зғ§жҲҗзҒ°зҡ„гҖҠй©ұйӮӘдёүзҜҮгҖӢж®ӢйЎөпјҢз«ҹдёҖзӮ№зӮ№йЈҳдәҶиө·жқҘпјҢз»•зқҖзҺүзүҢжү“иҪ¬гҖӮзҒ°зғ¬еңЁз©әдёӯжҺ’еҲ—пјҢеғҸжҳҜж— еҪўзҡ„жүӢеңЁд№ҰеҶҷгҖӮдёҖзҜҮзңӢдёҚи§Ғзҡ„ж–Үз« пјҢеңЁеӨ©ең°й—ҙжҲҗеҪўгҖӮ
е…ү幕зҡ„йўңиүІеҸҳдәҶгҖӮ
з”ұж·ЎйҮ‘иҪ¬дёәжҫ„й»„пјҢеғҸжё…жҷЁз¬¬дёҖзј•йҳіе…үгҖӮиЎҖйӣЁдёҖзў°дёҠеҺ»пјҢз«ӢеҲ»еҮҖеҢ–пјҢеҸҳжҲҗз»ҶеҜҶзҡ„з”ҳйң–жҙ’иҗҪгҖӮйҮ‘йӣЁиҗҪеңЁзҷҫ姓иә«дёҠпјҢйқ’иүІйҖҖеҺ»пјҢе‘јеҗёжёҗжёҗе№ізЁігҖӮ
жңүдёӘеӯ©еӯҗиәәеңЁжҜҚдәІжҖҖйҮҢпјҢе°Ҹи„ёеҸ‘зҙ«пјҢеҳҙе”Үе№ІиЈӮгҖӮдёҖж»ҙйҮ‘йӣЁиҗҪиҝӣд»–еҳҙйҮҢпјҢзқ«жҜӣйўӨдәҶйўӨпјҢе–үе’ҷеҠЁдәҶдёҖдёӢгҖӮ
зҺӢе®Ҳд»Ғиёүи·„иө·иә«пјҢдёҖжӯҘжӯҘиө°еҲ°дәәзҫӨдёӯй—ҙгҖӮд»–жҢЁдёӘжҹҘзңӢпјҢжңүдәәйўқеӨҙеҶ’жұ—пјҢжңүдәәдҪҺеЈ°е‘»еҗҹпјҢдҪҶйғҪдёҚеҶҚжҠҪжҗҗгҖӮжңҖеҗҺд»–еҒңеңЁдёҖдёӘжңҖе°Ҹзҡ„еӯ©з«ҘйқўеүҚгҖӮ
иҝҷеӯ©еӯҗжүҚдә”е…ӯеІҒпјҢиң·еңЁеҰҮдәәиҮӮејҜйҮҢпјҢжҺҢеҝғзҡ„й»‘з—Ӯе·Із»Ҹи„ұиҗҪпјҢйңІеҮәзІүе«©зҡ„зҡ®иӮӨгҖӮзҺӢе®Ҳд»ҒдјёжүӢжҺўдәҶжҺўд»–зҡ„йј»жҒҜпјҢзЁідәҶгҖӮ
жӯЈиҰҒ收еӣһжүӢпјҢйӮЈеӯ©еӯҗеҝҪ然зқҒејҖдәҶзңјгҖӮ
зңјзқӣеҫҲдә®пјҢеғҸдә•ж°ҙжҳ зқҖжҳҹгҖӮ
д»–жңӣзқҖеӨ©дёҠиҗҪдёӢзҡ„йҮ‘йӣЁпјҢе°ҸеЈ°иҜҙпјҡвҖңе…Ҳз”ҹвҖҰвҖҰжҲ‘жўҰи§ҒиҮӘе·ұиғҢзқҖгҖҠи®әиҜӯгҖӢпјҢз”Ёз«№з®Җжү“еҰ–жҖӘвҖҰвҖҰе®ғ们жҖ•еӯ—вҖҰвҖҰвҖқ
иҜҙе®Ңеҳҙи§’жү¬иө·пјҢ笑дәҶдёӢпјҢеҸҲй—ӯдёҠзңјзқЎдәҶиҝҮеҺ»гҖӮ
зҺӢе®Ҳд»Ғж„ЈеңЁеҺҹең°гҖӮ
д»–ж…ўж…ўи№ІдёӢпјҢжүӢжҢҮиҪ»иҪ»жҠҡиҝҮеӯ©еӯҗзҡ„йўқеӨҙгҖӮйӣЁж°ҙйЎәзқҖд»–зҡ„иў–еҸЈж»ҙдёӢжқҘпјҢз ёеңЁжіҘең°дёҠгҖӮд»–еј дәҶеј еҳҙпјҢжІЎиҜҙеҮәиҜқпјҢеҸӘдҪҺеЈ°йҒ“пјҡвҖңеҘҪеӯ©еӯҗпјҢзӯүдҪ йҶ’жқҘпјҢжҲ‘ж•ҷдҪ еҶҷ第дёҖдёӘвҖҳд»ҒвҖҷеӯ—гҖӮвҖқ
然еҗҺд»–з«ҷиө·иә«пјҢдёҖжӯҘдёҖжӯҘиө°еӣһж®Ӣзў‘ж—ҒгҖӮ
жЎғжңЁеү‘жЁӘж”ҫеңЁиҶқдёҠпјҢеү‘иә«еёғж»ЎиЈӮз—•пјҢеҸӘеү©еҚҠжҲӘгҖӮд»–жҠҠеўЁзҺүзүҢ收еӣһжҖҖйҮҢпјҢйқ зқҖзҹіжҹұеқҗдёӢгҖӮйЈҺеҗ№иҝҮжқҘпјҢж№ҝйҖҸзҡ„иЎЈиўҚиҙҙеңЁиғҢдёҠпјҢеҶ·еҫ—еҸ‘еғөгҖӮ
еҸҜд»–иҝҳйҶ’зқҖгҖӮ
зӣ®е…үиҗҪеңЁй©ҝйҒ“е°ҪеӨҙгҖӮйӮЈйҮҢд»Җд№Ҳд№ҹжІЎжңүпјҢеҸӘжңүиў«йӣЁж°ҙеҶІеҲ·иҝҮзҡ„жіҘеңҹи·ҜпјҢеқ‘жҙјдёҚе№іпјҢйҖҡеҗ‘иҝңж–№гҖӮ
зҷҫ姓们йғҪзқЎзқҖдәҶпјҢиәәеңЁйҮ‘йӣЁйҮҢпјҢеғҸзқЎеңЁжҳҘеӨ©зҡ„з”°еҹӮдёҠгҖӮ他们зҡ„и„ёиүІжҒўеӨҚдәҶдәӣи®ёиЎҖиүІпјҢе‘јеҗёеқҮеҢҖгҖӮйӮЈдёӘжӣҫжғіжқҖеЁҳзҡ„е°‘е№ҙиң·еңЁең°дёҠпјҢжүӢйҮҢиҝҳжҠ“зқҖдёҖжҠҠз„ҰеңҹгҖӮ
зҺӢе®Ҳд»ҒдҪҺеӨҙзңӢдәҶзңӢиҮӘе·ұзҡ„жүӢгҖӮжҢҮз”ІзјқйҮҢе…ЁжҳҜжіҘе’ҢиЎҖпјҢиў–еҸЈз ҙдәҶдёӘжҙһпјҢйңІеҮәз»“з—Ӯзҡ„дјӨеҸЈгҖӮиғғйҮҢдёҖйҳөз»һз—ӣпјҢд»–зҡұдәҶзҡұзңүпјҢеҚҙжІЎеҺ»ж‘ёиҚҜзҪҗвҖ”вҖ”йҮҢйқўж—©е°ұз©әдәҶгҖӮ
д»–жҠ¬иө·еӨҙпјҢзңӢеӨ©гҖӮ
йӣЁжІЎеҒңпјҢеҸҜдёҚеҶҚзәўдәҶгҖӮйҮ‘дёқиҲ¬зҡ„йӣЁзәҝеһӮиҗҪпјҢжҙ—зқҖж–ӯеўҷгҖҒзўҺз“ҰгҖҒзғ§еЎҢзҡ„еұӢжўҒгҖӮдёҖж №ж®Ӣжҹұз«ӢеңЁйӮЈйҮҢпјҢдёҠйқўйӮЈдёӘвҖңд»ҒвҖқеӯ—иў«йӣЁж°ҙжіЎеҫ—жЁЎзіҠпјҢеҸҜиҝҳиғҪи®ӨеҮәжқҘгҖӮ
йЈҺеҚ·зқҖзҒ°зғ¬жү«иҝҮеәҹеўҹпјҢиҝңеӨ„еұұеҙ–з©әиҚЎиҚЎзҡ„пјҢеҸӘеү©дёҖжҠҠж–ӯејҰзҡ„зҗҙйқҷйқҷиәәзқҖгҖӮ
д»–жІЎеҶҚзңӢйӮЈиҫ№гҖӮ
еҸӘжҳҜеқҗзқҖпјҢи„ҠиғҢйқ зқҖж®Ӣзў‘пјҢжүӢжҗӯеңЁж–ӯеү‘дёҠгҖӮзңјзҡ®и¶ҠжқҘи¶ҠйҮҚпјҢеҸҜд»–дёҚж•ўй—ӯзңјгҖӮд»–зҹҘйҒ“пјҢеҸӘиҰҒд»–иҝҳеқҗзқҖпјҢиҝҷзүҮеңҹең°е°ұиҝҳжІЎеҪ»еә•еҖ’дёӢгҖӮ
дёҚзҹҘиҝҮдәҶеӨҡд№…пјҢдёҖеЈ°иҪ»еҫ®зҡ„е’іе—Ҫе“Қиө·гҖӮ
жҳҜдёӘиҖҒжұүпјҢйҶ’дәҶгҖӮд»–еқҗиө·жқҘпјҢжҠ№дәҶжҠҠи„ёпјҢзңӢзңӢеӣӣе‘ЁпјҢеҸҲжңӣеҗ‘зҺӢе®Ҳд»ҒпјҢеҳҙе”ҮеҠЁдәҶеҠЁпјҢжІЎиҜҙиҜқпјҢеҸӘжҳҜж…ўж…ўзҲ¬иҝҮеҺ»пјҢи·ӘеңЁд»–йқўеүҚпјҢзЈ•дәҶдёӘеӨҙгҖӮ
жҺҘзқҖжҳҜ第дәҢдёӘпјҢ第дёүдёӘгҖӮ
жңүдәәе“ӯпјҢжңүдәәе–ҠвҖңе…Ҳз”ҹвҖқпјҢжңүдәәжҠұзқҖеӯ©еӯҗеҫҖиҝҷиҫ№жҢӘгҖӮ他们дёҚзҹҘйҒ“еҸ‘з”ҹдәҶд»Җд№ҲпјҢеҸӘзҹҘйҒ“йҶ’жқҘж—¶пјҢиә«дёҠзҡ„йӮӘеҠІжІЎдәҶпјҢеҝғйҮҢйӮЈиӮЎжғізғ§жҲҝеӯҗгҖҒжғіз Қдәәзҡ„еҝөеӨҙж¶ҲеӨұдәҶгҖӮ
дёҖдёӘе°ҸеҘіеӯ©зҲ¬еҲ°зҺӢе®Ҳд»Ғи„ҡиҫ№пјҢжӢҪдәҶжӢҪд»–зҡ„иЈӨи„ҡпјҡвҖңе…Ҳз”ҹпјҢйӣЁжҳҜз”ңзҡ„гҖӮвҖқ
д»–дҪҺеӨҙзңӢеҘ№гҖӮ
еӯ©еӯҗд»°зқҖи„ёпјҢиҲҢе°–жҺҘзқҖйӣЁж°ҙпјҢзңјзқӣдә®дә®зҡ„пјҡвҖңзңҹзҡ„пјҢеғҸзі–ж°ҙгҖӮвҖқ
зҺӢе®Ҳд»ҒзңӢдәҶеҘ№еҫҲд№…пјҢз»ҲдәҺжүҜдәҶжүҜеҳҙи§’гҖӮ笑еҫ—еҫҲиҪ»пјҢеҮ д№ҺзңӢдёҚеҮәжқҘгҖӮ
д»–дјёжүӢжҠҠеҘ№жҠұиө·жқҘпјҢж”ҫеңЁиҮӘе·ұиә«иҫ№гҖӮе°ҸеҘіеӯ©д№–д№–еқҗзқҖпјҢ继з»ӯжҺҘйӣЁе–қгҖӮ
е…¶д»–дәәеӣҙдәҶиҝҮжқҘпјҢи¶ҠиҒҡи¶ҠеӨҡгҖӮжІЎдәәиҜҙиҜқпјҢеҸӘжҳҜйқҷйқҷең°еқҗзқҖпјҢзңӢзқҖд»–пјҢеғҸжҳҜжҠҠд»–еҪ“жҲҗдәҶй”ҡгҖӮ
зҺӢе®Ҳд»Ғй—ӯдәҶдјҡе„ҝзңјпјҢеҸҲзқҒејҖгҖӮ
д»–зҹҘйҒ“иҝҷеңәйӣЁж•‘дёҚдәҶжүҖжңүдәәгҖӮйҫҷеңәй©ҝжҜҒдәҶпјҢй•ҮйӮӘзў‘зўҺдәҶпјҢиӣҮеҰ–иҷҪжӯ»пјҢеҰ–еҗҺзҡ„еЁҒиғҒиҝҳеңЁгҖӮзҷҪй№ҝжҙһеә•дёӢеҹӢзқҖдёүзҷҫе…·з«Ҙе°ёпјҢиҝҷдәӢдёҚиғҪеҝҳгҖӮ
еҸҜзңјдёӢпјҢиҝҷдәӣдәәжҙ»дәҶдёӢжқҘгҖӮ
他们иғҪе“ӯпјҢиғҪ笑пјҢиғҪи®°дҪҸи°Ғж•‘дәҶ他们гҖӮ
иҝҷе°ұеӨҹдәҶгҖӮ
д»–дјёжүӢж‘ёдәҶж‘ёж–ӯеү‘зҡ„зјәеҸЈпјҢжҢҮе°–иў«еҲ’дәҶдёҖдёӢпјҢеҮәдәҶзӮ№иЎҖгҖӮиЎҖж··зқҖйӣЁж°ҙжөҒеҲ°еү‘иә«дёҠпјҢйЎәзқҖиЈӮзјқеҫҖдёӢж»ҙгҖӮ
еҝҪ然пјҢд»–еҗ¬и§Ғи„ҡжӯҘеЈ°гҖӮ
дёҚжҳҜзҷҫ姓зҡ„пјҢд№ҹдёҚжҳҜйЈҺйҮҢзҡ„жқӮйҹігҖӮжҳҜж•ҙйҪҗзҡ„пјҢеёҰзқҖй“Ғз”Ізў°ж’һзҡ„еЈ°йҹіпјҢд»Һй©ҝйҒ“йӮЈеӨҙдј жқҘгҖӮ
д»–жҠ¬иө·зңјгҖӮ
йӣЁе№•дёӯпјҢдёҖйҳҹе®ҳе…өжӯЈжңқиҝҷиҫ№иө°жқҘгҖӮйўҶеӨҙзҡ„жҳҜдёӘеҺҝд»ӨжЁЎж ·зҡ„дәәпјҢжҠ«зқҖжІ№еёғж–—зҜ·пјҢжүӢйҮҢжӢҝзқҖдёҖеј зәёгҖӮиә«еҗҺи·ҹзқҖеҚҒеҮ дёӘе·®еҪ№пјҢжңүзҡ„жӢҺй”Ғй“ҫпјҢжңүзҡ„жҢҒеҲҖгҖӮ
他们еңЁеәҹеўҹеӨ–еҒңдёӢгҖӮ
еҺҝд»Өжү«дәҶдёҖеңҲпјҢзӣ®е…үжңҖеҗҺиҗҪеңЁзҺӢе®Ҳд»Ғиә«дёҠгҖӮ
д»–дёҫиө·жүӢдёӯзҡ„зәёпјҢеӨ§еЈ°иҜҙпјҡвҖңеҘүж—ЁжҚүжӢҝеҰ–иЁҖжғ‘дј—д№Ӣеҫ’зҺӢе®Ҳд»ҒпјҒдҪ д»ҘйӮӘжңҜж“ҚжҺ§зҷҫ姓пјҢз„ҡжҜҒй©ҝз«ҷпјҢзҪӘиҜҒзЎ®еҮҝвҖ”вҖ”вҖқ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ө¶е°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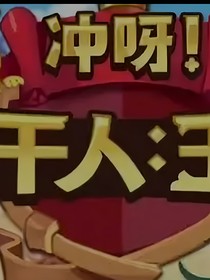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йҘје№ІдәӢи®°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еңЁејӮз•Ңзә№д№қйҫҷжӢүжЈә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Ҫ’е°ҳеҲӣдё–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家з”өи§ҶжңәиғҪз©ҝи¶ҠдёҮз•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