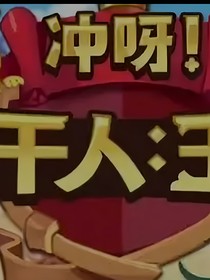第26章 谁在给我递刀
血腥气混杂着尘土,弥漫在黄沙漫天的战场上。
铁锈般的气息钻入鼻腔,带着温热的腥甜,仿佛每一口呼吸都舔舐过断刃与残肢。
风卷起焦黑的战旗一角,猎猎作响,远处哀嚎未绝,像野犬在夜林中低吠。
萧尘立于高坡之上,铠甲覆满血渍与沙尘,指尖仍残留着握剑太久的麻木感。
脚下是溃败的赤狄残部被驱赶入笼,士卒欢呼震天,声浪如潮水般拍打耳膜。
这是一场完胜——斩首八百,生擒三百,缴获牛马无数。
然而他的目光却越过庆功的人群,落在远处清点俘虏的区域。
那里,一名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的校尉正凶狠踹倒一名百夫长,脚底溅起的泥浆沾上对方惨白的脸颊,发出沉闷的“啪”声。
那人吼声如雷,震得近旁士兵下意识缩肩。
他正是赫连锋。
“绑紧了!都给老子老实点!”赫连锋一脚踹在一个赤狄百夫长的膝弯,动作凶悍,引得周围士卒纷纷侧目,投来敬佩的目光。
他亲手押着两名身份最高的俘虏,大步流星地穿过人群,来到萧尘面前,盔甲上的鲜血尚未凝固,在阳光下泛着黏腻的暗红光泽,衬得他那张粗犷的脸愈发勇武。
“将军!”赫连锋声如洪钟,单膝跪地,脸上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亢奋,“末将幸不辱命,生擒赤狄百夫长两名!这帮杂碎嘴硬得很,末将愿立下军令状,彻夜审讯,必从他们口中挖出赤狄主力大营的虚实!”
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忠勇之态溢于言表。
“赫连校尉辛苦了。”萧尘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赞许,亲自上前扶起他,“有你这等猛将,何愁赤狄不破?审讯之事,便交予你全权负责。”
“末将遵命!”赫连锋大喜过望,腰杆挺得更直了。
萧尘含笑点头,转身的刹那,那份温和的赞许便如潮水般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寒潭。
他的靴底碾过一摊半干的血泥,发出轻微的“咯吱”声。
他的目光看似不经意地向下扫去,精准地落在了赫连锋那双沾满泥土的军靴上。
皮革皲裂处嵌着湿漉漉的泥块,散发出一种不同于战场黄沙的独特腥味——那是潮湿红壤特有的腐殖气息。
靴底,附着着一层暗红色的湿泥。
那颜色,萧尘再熟悉不过——正是西谷隘口特有的红土。
昨夜,为了防备赤狄小股部队偷袭,西谷已被列为最高等级的禁区,严令任何人靠近。
站在萧尘身侧的影月,顺着主公的视线瞥了一眼,随即垂下眼帘,如同一尊没有感情的影子,唯有手指微不可查地动了一下,已然在心中将“赫连锋”这个名字用血色标记。
一切不动声色。
当晚,烛火摇曳。
萧尘执笔研墨,在素笺上缓缓写下一封“密信”。
墨汁滴落纸面,晕开如血花绽放。
他唇角微扬:“要钓大鱼,先得喂饵。”
影月静立身后,低声道:“赫连锋贪婪好名,必会上钩。”
“那就给他一场梦。”萧尘吹干墨迹,将信纸裹入蜡丸,盖上仿制火漆,“让他以为,自己终于爬上了棋盘。”
次日清晨,天光微明,营地已悄然流传一则消息:将军昨夜修书一封,拟于今晨遣快马送往兵部报捷。
赫连锋听闻,眼神微闪。
巡营至传令驿道拐角处,一处堆放废弃文书的角落时,眼角忽然捕捉到一抹不自然的红光——那是兵部火漆独有的朱砂色泽,藏于枯叶之间,宛如一只窥视的眼睛。
他左右张望,见四下无人,迅速弯腰将其捡起,藏入袖中。
指尖触到蜡丸的瞬间,一股隐秘的战栗顺着手臂窜上脊背。
那兵部的火漆烙印,让他心跳骤然加速。
两日后,南门外风平浪静。
第三日黄昏,溪流水位悄然上涨,守卒察觉异样,上报却被斥“疑神疑鬼”。
入夜,蛙鸣骤止,犬吠不闻,天地陷入诡异寂静,连风都像是被扼住了喉咙。
午夜时分,大地震动,轰鸣如雷自上游奔袭而来——
“决堤了!上游的堤坝被人挖开了!”一名负责巡查的老卒,瘸着腿,连滚带爬地冲进营中,声音凄厉,带着哭腔。
洪水如猛兽般奔涌而下,幸亏发现及时,守营将士拼死用沙袋堵截,才堪堪保住了临时营寨,但也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若非如此,数千将士将在睡梦中被洪水吞噬。
萧尘雷霆震怒,当即下令封锁全营,任何人不得出入。
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亲提赫连锋至帅帐。
赫连锋被两名亲卫押进来时,脸上还带着一丝茫然和被人打扰的不悦,但当他看到萧尘那双冰冷刺骨的眼睛时,心头猛地一沉,掌心渗出冷汗,浸湿了袖中残留的蜡屑。
“说吧,为什么?”萧尘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敲在赫连锋的心上。
“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赫连锋脖子一梗,怒吼道,“南门决堤,与我何干?这是栽赃!我赫连家三代从军,忠烈满门,岂会做出通敌叛国之事!”
他演得声泪俱下,仿佛蒙受了天大的冤屈。
萧尘看着他,不怒反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怜悯,一丝嘲讽。
他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只是轻轻拍了拍手。
影月无声地走上前,将三件物证一一呈列在案几上。
第一件,是一个小小的油纸包,里面装着一些暗红色的泥土样本,旁边还有一份勘验记录,明确指出,这泥土与西谷隘口的土壤完全吻合,也与从赫连锋靴底刮下的泥土,别无二致。
第二件,是赫连锋从不离身的贴身匕首。
影月当着他的面,用细针挑开柄缝,露出内壁一道极细的刻痕——蟠龙缠绕,鳞爪分明,正是昭灵观秘印。
她冷冷道:“此符非俗匠所能刻,乃观中‘信刃’之记。”
第三件,是一片被撕裂的信纸残角。边缘焦灼,似曾焚毁未尽。
看到这片残角,赫连锋的瞳孔骤然收缩!
这正是他藏入怀中那封“密信”上,因太过紧张而不慎遗漏的一角!
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嘴唇哆嗦着,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
“这……这是陷害!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他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做着最后的挣扎。
萧尘挥了挥手。
影月上前,快如鬼魅,一把捏住赫连锋的下颚,将一颗黑色的药丸弹入他口中。
赫连锋喉头滚动,被迫咽了下去。
药力发作得很快,他眼中的愤怒与惊恐渐渐褪去,变得涣散而迷茫,开始喃喃自语:
“……不能让他赢……龙纹佩……西谷……昨夜我去过……他们说只要毁掉伏击计划……京城就会动手……姓李的……粮册有问题……他说只要萧尘败绩,户部账目便可掩盖……龙脉重开之日……便是新君登基之时……”
话到此处,他眼中猛然闪过一丝清明,似乎是残存的意志在做最后的抵抗。
他舌头猛地一卷,竟是要咬舌自尽!
影月屈指一弹,一道劲风封住了他的咽喉经络。
赫连锋顿时如被扼住脖颈的公鸭,喉咙里发出嗬嗬的痛苦呻吟,却再也无法断气,也无法再发出一句完整的话。
整个帅帐,死一般的寂静。
萧尘静静地听完,忽然站起身,缓缓踱步。
帐内的烛火,将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宛如一头择人而噬的凶兽。
“原来在你们眼里,我只是个挡路的废物少爷?”他走到赫连锋面前,俯下身,盯着他那双因痛苦和恐惧而布满血丝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
“可你们似乎都忘了——真正的棋手,从来不急着掀翻棋盘。”
当夜,一道命令从帅帐传出:校尉赫连锋通敌罪证确凿,畏罪发狂,剜去双目,囚于地牢最深处。
与此同时,苏文砚在萧尘的口述下,将赫连锋的供词一字不漏地誊抄成副本,用三道火漆密封入一个玄铁匣子。
数个时辰后,这只匣子通过一条最隐秘的渠道,被送往千里之外的京城,收件人是御史台一位从不结党、以刚正闻名的老臣。
窗外,月色如霜,冰冷地洒在营帐之上。
萧尘处理完这一切,走到窗边,目光穿过层层营房,望向了那些临时搭建、关押着数千赤狄俘虏的栅栏。
夜风拂面,带来铁链拖地的叮当声,夹杂着俘虏们断续的哭嚎与呻吟,像钝刀割肉般磨人心神。
他将那封送往京城的密报回执,在烛火上缓缓点燃,看着它化为灰烬。
火苗跳跃,映照着他深邃的眸子,里面没有半分波澜,只有一片沉寂的冰海。
一枚棋子死了,棋盘上,还剩下多少活着的棋子呢?
活着的,又该如何落子,才能让这盘棋,更有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