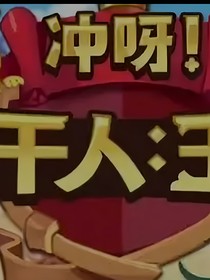第17章 你们跪着喊饶命 我才刚热完身
那尊魔神,已然睁开了双眼。
京观筑成的第二日,血腥的阴云笼罩在京城上空,尚未散去的铁锈味仿佛凝成实质,压得人喘不过气。
消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随着四散的商队和驿卒的快马,传遍了整个大周乃至更远的地方。
漠北草原,刚刚结束一场血腥内斗的北狄可汗,在王帐中听完斥候的汇报,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惊惧。
他当即推开怀中的美人,沐浴更衣,亲自点燃三炷高香,对着南方长跪不起,祭祀着草原的天神。
随后,一道严苛至极的命令传遍所有部落:全族禁酒三日,任何人不得高声喧哗,以免触怒那位从地狱归来的“杀神”。
东南西北的四座藩王府邸,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演着相似的戏码。
那些被他们视作心腹,耗费重金安插在京城的密探,被一封封八百里加急的密令连夜召回。
藩王们怕的不是皇帝,而是那位手段酷烈到令人发指的少年。
他们生怕自己的探子被错当成李党余孽,成为下一座京观的材料。
就连那些一向自诩“化外之人”,不尊王法的江湖门派,也罕见地变得顺从。
各大门派掌门纷纷派出门下弟子,向就近的官府递上拜帖,言辞恳切地表示“坚决拥护朝廷清查奸佞”,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了忠君爱国的典范。
整个天下,都在因一座骷髅京观而战栗。
风暴中心的镇北王府别院,却是一片死寂。
萧尘端坐于书案前,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
影月单膝跪地,声音压得极低,汇报着京中的动向:“少主,十二家世袭罔替的勋贵,已经派人送来了厚礼。礼单在此,他们遣来的使者言辞卑微,称愿……愿为王府效死,永世效忠。”
“效忠?”萧尘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眼底却没有半分笑意,“说得真好听。他们不是想效忠,他们是怕死。”
他不再理会那份足以买下半座城池的礼单,仿佛那只是一堆废纸。
他提起狼毫笔,饱蘸浓墨,手腕翻飞间,三封内容截然不同的密信一挥而就。
“这封,交给韩破虏,让他按计划行事。”
“这封,给秦烈,告诉他,我要让京城里每一只老鼠都活在恐惧里。”
“最后一封,让陈七郎亲自送出城,目标……天机阁。”
影月接过密信,只觉得那薄薄的纸张重如千钧,她不敢多问,身影一闪,悄然融入了阴影之中。
与此同时,皇城金銮殿内,气氛凝重得几乎要滴出水来。
早朝的钟声刚刚敲响,文武百官还未站稳,须发皆白的御史大夫裴延年便手持玉笏,一步踏出,声如洪钟,响彻整个大殿:“臣,都察院御史大夫裴延年,弹劾太师李崇安!其人身为国之柱石,食君之禄,不想报国,反蓄谋不轨!私调边军,勾结外寇,意图兵变!致使我大周九万忠勇将士,枉死于荒野,尸骨无存!此等罪行,罄竹难书,罪通于天!恳请陛下明正典刑,昭告天下,以慰九万将士在天之灵!”
“轰”的一声,整个朝堂炸开了锅。
这番话,字字诛心!
龙椅上的皇帝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握着扶手的手指因过度用力而指节发白。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又有六名御史接连出列,齐刷刷跪倒在地,异口同声地泣血叩首:“非诛李氏一族,不足以平天下之怨!请陛下圣断!”
声浪滚滚,直冲殿顶。
那些往日里唯李崇安马首是瞻,将太师府门槛都快踏破的官员们,此刻一个个缩着脖子,噤若寒蝉,恨不得将自己变成殿内的一根柱子,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他们的“恩师”辩解半句。
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这出戏码,他们演得比谁都熟练。
萧尘没有去皇宫,他甚至没有踏出别院半步。
此刻,他正坐在一间茶楼的雅间内,凭栏远眺。
整个京城的风吹草动,似乎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的指间,正把玩着一枚新制的骨符。
那是一块昨夜从战场上带回来的,浸透了将士鲜血的石片,经过系统提炼后,竟自动凝聚出了整整五点天命点。
就在此时,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在他脑海中悄然响起:
【检测到大规模命运线被强行扭转,世界因果发生剧烈变动……天命点生成机制已变更。】
【新机制:凡因宿主谋划布局而直接或间接死亡者,其消散的‘气运残烬’将根据其生前影响力,自动转化为微量天命点。】
萧尘的动作微微一顿,他摊开手掌,凝视着那枚骨符上微不可见的莹莹之光,仿佛能看到无数哀嚎的灵魂在其中沉浮。
他忽然低低地笑了起来,那笑声很轻,却带着一丝说不出的邪异。
“原来是这样……死的人越多,我就越强。”
一抹猩红的光芒自他眼底深处一闪而逝,那一瞬间,他仿佛听见了体内亿万生魂的嘶吼与低语,那不是负担,而是一曲……悦耳的赞歌。
京城,彻底变成了一张由萧尘亲手编织的大网。
韩破虏奉命接管了京畿防务,以“协防”的名义,将三千玄甲营精锐布控在了五座城门。
所有进出的官员,无论品级高低,都必须下马接受盘查,查验腰牌与通关文书,稍有差池,便会被当场拿下。
秦烈则被授予了一个临时参军的虚职,带着三十名煞气腾腾的玄甲骑兵,终日在街上巡弋宣令:“奉镇北王府令:凡窝藏李党余孽者,夷三族!主动揭发者,赏千金,官升一级!”
一时间,告密之风盛行。
昔日门庭若市的太师府,一夜之间连遭数次纵火,府内三名不愿受辱的家眷被捕后,当场自尽。
而早已被关押在地牢深处的柳氏,隐约听到了外面的风声,她那早已被恐惧和绝望侵蚀的神志彻底崩溃,疯了般地抓着牢门哭喊:“我不是主谋!不是我!是李景桓!是他让我去给萧凝雪下药的啊!是他!”
然而,她的哭喊,除了引来狱卒一顿无情的鞭打,再无人理会。
深夜,月凉如水。
萧尘独自立于别院最高的屋顶之上,夜风吹动他的衣袍,猎猎作响。
他眺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皇宫,知道皇帝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
果然,没过多久,三道加盖玉玺的诏书便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全城:削去李崇安所有官爵,抄没全部家产,其子孙三代之内,尽数流放三千里外的岭南烟瘴之地,永世不得还朝。
李家,这棵盘踞在大周朝堂数十年的参天大树,倒了。
可萧尘的嘴角却没有丝毫上扬,反而眉头微蹙,陷入了沉思。
“李崇安……会这么轻易就认输吗?他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到那座京观,还没明白……那座京观真正的主人,到底是谁。”
话音刚落,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打破了深夜的宁静。
孙校尉纵马飞驰至别院门前,还未等马停稳便翻身滚落,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单膝跪地,神色是前所未有的凝重:“禀少主!西郊乱葬岗,发现了七具尸体!”
“说重点。”萧尘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
“是!”孙校尉咽了口唾沫,艰难道,“七人皆为太师府豢养的顶尖死士,一击毙命。致命伤在喉间,是被一根细如牛毛的钢针……从后颈贯穿而过。这手法……这手法,与影卫的杀人手法,一模一样!”
风,骤然穿过萧尘宽大的衣袖,发出呜咽般的声响。
少年原本平静的眸光,在这一刻骤然变得森寒刺骨。
“有意思。”他缓缓吐出两个字,声音冷得像是九幽寒冰,“有人,想把这盆脏水,泼到我的头上。”
是谁?
在李家倒台的这个微妙时刻,用这种天衣无缝的手段嫁祸于他?
这盘棋,似乎在所有人都以为即将终局的时候,又悄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