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з« дҪ иҖғеңәеҶҷж–Үз« пјҢжҲ‘жҡ—дёӯж”№е‘Ҫж ј
дә¬еҹҺзҡ„еӨ©пјҢеғҸжҳҜиў«жҚ…дәҶдёӘзӘҹзӘҝпјҢиҝһз»өзҡ„жҡҙйӣЁеҶІеҲ·дәҶж•ҙж•ҙдёүж—ҘпјҢд»ҝдҪӣиҰҒе°Ҷиҝҷеә§еҚғе№ҙеёқйғҪзҡ„з№ҒеҚҺдёҺзҪӘжҒ¶дёҖ并иҚЎж¶Өе№ІеҮҖгҖӮ
йӣЁж°ҙиҷҪеҒңпјҢдҪҶжҜ”жҪ®ж№ҝз©әж°”жӣҙд»ӨдәәзӘ’жҒҜзҡ„пјҢжҳҜжӮ„然ејҘжј«зҡ„жөҒиЁҖгҖӮ
иЎ—еӨҙе··е°ҫпјҢиҢ¶жҘјй…’иӮҶпјҢзӘғзӘғз§ҒиҜӯжұҮжҲҗдёҖиӮЎжұ№ж¶Ңзҡ„жҡ—жөҒгҖӮ
вҖңеҗ¬иҜҙдәҶеҗ—пјҹеӨӘеёҲеәңдёҠйӮЈдҪҚпјҢжғіжҠҠиҮӘе·ұдёҚжҲҗеҷЁзҡ„е°ҸиҲ…еӯҗжү¶дёҠеӨӘеӯҗд№ӢдҪҚпјҒвҖқвҖңдёҚжӯўе‘ўпјҢе®«йҮҢеӨҙй—№й¬јдәҶпјҒжҚ®иҜҙжҳҜеүҚжңқеҶӨжӯ»зҡ„еҰғеӯҗпјҢеӨңеӨңе•је“ӯпјҢжүҫйҷӣдёӢзҙўе‘ҪпјҒвҖқ
жөҒиЁҖеҰӮзҳҹз–«иҲ¬жү©ж•ЈпјҢзңҹеҒҮйҡҫиҫЁпјҢеҚҙзІҫеҮҶең°жҲідёӯдәҶдә¬еҹҺеҗ„ж–№еҠҝеҠӣзҡ„з—ӣеӨ„гҖӮ
ж°‘еҝғжө®еҠЁпјҢзҷҫе®ҳжғҠз–‘гҖӮ
йҫҷжӨ…дёҠзҡ„йӮЈдҪҚеӨ©еӯҗпјҢз«ҹд№ҹз ҙеӨ©иҚ’ең°дёҖиҝһдёүж—Ҙй—ӯж®ҝдёҚеҮәпјҢд»»з”ұжңқж”ҝиҝ‘д№ҺеҒңж‘ҶгҖӮ
иҖҢжҳ”ж—ҘжқғеҖҫжңқйҮҺзҡ„еӨӘеёҲжқҺеҙҮе®үпјҢе…¶еәңйӮёеӨ–еӣҙпјҢдёҚзҹҘдҪ•ж—¶е·Іиў«зҰҒеҶӣеӣҙеҫ—ж°ҙжі„дёҚйҖҡпјҢй—ЁеҸҜзҪ—йӣҖпјҢжҳ”ж—ҘиҪҰж°ҙ马йҫҷзҡ„зӣӣжҷҜпјҢдёҖеӨңд№Ӣй—ҙеҢ–дёәжіЎеҪұгҖӮ
жқғеҠӣзҡ„зңҹз©әпјҢдҫҝжҳҜйҮҺеҝғзҡ„жІғеңҹгҖӮ
еҹҺеҚ—дёҖеӨ„еғ»йқҷзҡ„еҲ«йҷўеҶ…пјҢиҗ§е°ҳз«ҜеқҗдәҺеҜҶе®Өдё»дҪҚпјҢжҢҮе°–иҪ»еҸ©зқҖзҙ«жӘҖжңЁжЎҢйқўпјҢеҸ‘еҮәжІүй—·иҖҢжңүиҠӮеҘҸзҡ„еЈ°е“ҚгҖӮ
д»–иә«еүҚзҡ„з©әж°”дёӯпјҢдјјд№Һиҝҳж®Ӣз•ҷзқҖйӣЁеҗҺзҡ„ж№ҝеҶ·пјҢдҪҶд»–зҡ„зңјзҘһеҚҙжҜ”зӘ—еӨ–зҡ„еҜ’жҳҹжӣҙдә®пјҢжӣҙеҶ·гҖӮ
вҖңеҚҒдёүгҖӮвҖқд»–ж·Ўж·ЎејҖеҸЈгҖӮ
дҫҚз«ӢеңЁдҫ§зҡ„й’ұеҚҒдёүиә¬иә«еә”йҒ“пјҡвҖңе…¬еӯҗпјҢжңүдҪ•еҗ©е’җпјҹвҖқ
иҗ§е°ҳжҠ¬зңёпјҢзӣ®е…үеҰӮй№°йҡјиҲ¬й”җеҲ©пјҢиҗҪеңЁй’ұеҚҒдёүиә«дёҠпјҡвҖңжҲ‘иҰҒдҪ еңЁдёғж—Ҙд№ӢеҶ…пјҢи®©дёҖдёӘеҗҚеӯ—е“ҚеҪ»дә¬еҹҺвҖ”вҖ”е‘Ёж–ҮжҳӯгҖӮвҖқ
иҜқйҹіжңӘиҗҪпјҢд»–еҸіжүӢзҢӣ然дёҖжҸЎпјҢдёҖжһҡеҲ»зқҖеҸӨжңҙз¬Ұж–Үзҡ„йӘЁз¬ҰеңЁд»–жҺҢеҝғеә”еЈ°еҢ–дёәйҪ‘зІүгҖӮ
еҮ д№ҺжҳҜеҗҢдёҖзһ¬й—ҙпјҢиҗ§е°ҳзҡ„иҜҶжө·ж·ұеӨ„пјҢйӮЈйҒ“йңёйҒ“з»қдјҰзҡ„зҷҪиө·ж®ӢйӯӮиҷҡеҪұзј“зј“йҖҖж•ЈпјҢеҸ–иҖҢд»Јд№Ӣзҡ„пјҢжҳҜдёҖйҒ“йҳҙеҶ·иҖҢиҜЎи°Ізҡ„ж°”жҒҜпјҢеҰӮжҜ’иӣҮиҲ¬ж— еЈ°ж— жҒҜең°йЎәзқҖжҹҗз§ҚзҘһз§ҳзҡ„иҒ”зі»пјҢж¶Ңе…ҘдәҶй’ұеҚҒдёүзҡ„дҪ“еҶ…гҖӮ
гҖҗеҸ®пјҒ
иӢұзҒөеҸ¬е”Өе®ҢжҲҗпјҡиҙҫиҜ©пјҲжҜ’еЈ«пјүпјҢзҒөдҪ“йҷ„иә«зҠ¶жҖҒпјҢеҸҜжҢҒз»ӯеҪұе“Қе®ҝдё»жҖқз»ҙ7ж—ҘпјҢж¶ҲиҖ—600еӨ©е‘ҪзӮ№гҖӮгҖ‘
й’ұеҚҒдёүзҡ„иә«еҪўзҢӣең°дёҖеғөпјҢзңјзҘһеҮәзҺ°дәҶдёҖеҲ№йӮЈзҡ„з©әжҙһдёҺиҝ·иҢ«гҖӮ
дҪҶд»…д»…жҳҜзүҮеҲ»д№ӢеҗҺпјҢд»–зј“зј“жҠ¬иө·еӨҙпјҢйӮЈеҸҢеҺҹжң¬зІҫжҳҺеҚҙдёҚеӨұжҒӯйЎәзҡ„зңёеӯҗйҮҢпјҢжӯӨеҲ»з«ҹжҳҜж·ұдёҚи§Ғеә•зҡ„з®—и®ЎдёҺе№Ҫе…үгҖӮ
д»–зҡ„еҳҙи§’пјҢеӢҫиө·дёҖжҠ№е…Ёз„¶дёҚеұһдәҺд»–иҮӘе·ұзҡ„пјҢеёҰзқҖдёүеҲҶжҲҸи°‘дёҺдёғеҲҶжЈ®еҜ’зҡ„еҶ·з¬‘гҖӮ
вҖңе…¬еӯҗвҖҰвҖҰиҝҷжҳҜжғізҺ©дёҖеұҖж–Үеңәеұ йҫҷпјҹвҖқд»–зҡ„еЈ°йҹідҫқж—§жҳҜй’ұеҚҒдёүзҡ„пјҢдҪҶиҜӯи°ғдёӯзҡ„йӮЈиӮЎеӯҗиҝҗзӯ№её·е№„гҖҒи§ҶеӨ©дёӢдёәжЈӢзӣҳзҡ„ж„Ҹе‘іпјҢеҚҙд»ӨдәәдёҚеҜ’иҖҢж —гҖӮ
ж¬Ўж—ҘпјҢеӨ©иүІе°ҶжҳҺжңӘжҳҺгҖӮ
科дёҫдјҡиҜ•ж”ҫжҰңзҡ„еүҚеӨ•пјҢдә¬еҹҺзҡ„з©әж°”дёӯејҘжј«зқҖдёҖз§ҚиҜЎејӮзҡ„з„ҰзҒјгҖӮ
еҹҺиҘҝдёҖй—ҙз ҙж—§зҡ„дјҡйҰҶйҮҢпјҢ新科乡иҜ•и§Је…ғе‘Ёж–ҮжҳӯпјҢжӯЈеҖҹзқҖеҫ®ејұзҡ„зғӣе…үпјҢдёҖдёқдёҚиӢҹең°иӘҠжҠ„зқҖиҮӘе·ұиҝһеӨңеҶҷе°ұзҡ„зӯ–и®әгҖӮ
д»–зҡ„иЎЈиЎ«е·Іжҙ—еҫ—еҸ‘зҷҪпјҢдҪҶжөҶжҙ—еҫ—жһҒдёәе№ІеҮҖпјҢз©ҝеңЁд»–иә«дёҠпјҢжӣҙиЎ¬еҫ—д»–и„ҠжўҒжҢәзӣҙеҰӮжқҫгҖӮ
д»–дёҚзҹҘйҒ“пјҢдёҖеңәи¶ід»Ҙйў иҰҶж— ж•°дәәе‘Ҫиҝҗзҡ„йЈҺжҡҙпјҢжӯЈд»Ҙд»–зҡ„еҗҚеӯ—дёәдёӯеҝғпјҢжӮ„然й…қй…ҝгҖӮ
дёҺжӯӨеҗҢж—¶пјҢзӨјйғЁиЎҷй—ЁеҗҺе ӮпјҢзҒҜзҒ«йҖҡжҳҺгҖӮ
еҪ“жңқеӨӘе°үпјҢжқҺеҙҮе®үзҡ„ж”ҝж•ҢпјҢжқҺжҷҜжЎ“пјҢжӯЈдәІиҮӘеқҗй•ҮгҖӮ
д»–е°ҶдёҖеҸ еҺҡеҺҡзҡ„йҮ‘зҘЁпјҢдёҚзқҖз—•иҝ№ең°еЎһе…Ҙдё»иҖғе®ҳзҺӢеӨ§дәәзҡ„иў–дёӯпјҢеЈ°йҹіеҶ°еҶ·еҰӮй“ҒпјҡвҖңжҲ‘е„ҝжқҺжүҝдёҡзҡ„ж–Үз« пјҢжҳҺж—ҘеҠЎеҝ…зҪ®дәҺжҰңйҰ–гҖӮиӢҘжҳҜжңүд»Җд№ҲжқӮйҹівҖҰвҖҰзҺӢеӨ§дәәеә”иҜҘиҝҳи®°еҫ—пјҢеүҚе№ҙйӮЈдёӘвҖҳдёҚж…Һжі„йўҳвҖҷзҡ„еүҜдё»иҖғпјҢзҺ°еңЁеқҹеӨҙзҡ„иҚүжңүеӨҡй«ҳдәҶеҗ§пјҹвҖқ
зҺӢеӨ§дәәйўқеӨҙеҶ·жұ—涔涔пјҢиҝһиҝһз§°жҳҜпјҢжҸЎзқҖйҮ‘зҘЁзҡ„жүӢеҚҙжҠ–еҫ—еғҸз§ӢйЈҺдёӯзҡ„иҗҪеҸ¶гҖӮ
жҳҜеӨңпјҢеҹҺдёӯжңҖжңүеҗҚзҡ„й…’жҘјвҖңйҶүд»ҷеұ…вҖқеҶ…пјҢй’ұеҚҒдёүд»ҘвҖңеәҶиҙәиҖҒе®ўжҲ·й«ҳдёӯвҖқдёәеҗҚпјҢиұӘжҺ·еҚғйҮ‘пјҢиҜ·еҠЁдәҶдёүдҪҚеңЁдә¬дёӯйўҮжңүеҗҚжңӣеҚҙеұЎиҜ•дёҚ第зҡ„иҗҪйӯ„дёҫдәәйҘ®е®ҙгҖӮ
й…’иҝҮдёүе·ЎпјҢиҸңиҝҮдә”е‘іпјҢй’ұеҚҒдёүиЈ…дҪңдёҚиғңй…’еҠӣпјҢж»ЎйқўйҖҡзәўең°вҖңйҶүиҜӯвҖқйҒ“пјҡвҖңеҮ дҪҚе…„еҸ°вҖҰвҖҰд»Ҡе№ҙжҖ•жҳҜеҸҲзҷҪеҝҷжҙ»дәҶвҖҰвҖҰе°ҸејҹжҲ‘вҖҰвҖҰжҲ‘еҸҜжҳҜеҫ—дәҶеҮҶдҝЎе„ҝпјҢд»Ҡ科иҝҷдёүеҚҒе…ӯеҗҚиҝӣеЈ«зҡ„еҗҚйўқпјҢж—©е°ұвҖҰвҖҰж—©е°ұиў«дәә用银еӯҗз»ҷеЎ«ж»ЎдәҶпјҒвҖқ
дёүдҪҚдёҫдәәй—»иЁҖпјҢзҡҶжҳҜйқўиүІдёҖеҸҳгҖӮ
дёҖдәәдёҚдҝЎйҒ“пјҡвҖңй’ұжҺҢжҹңпјҢжӯӨиҜқеҪ“зңҹпјҹ科дёҫд№ғеӣҪд№ӢеӨ§е…ёпјҢеІӮж•ўеҰӮжӯӨе„ҝжҲҸпјҹвҖқ
й’ұеҚҒдёүеҳҝеҳҝдёҖ笑пјҢд»Һиў–дёӯж‘ёеҮәдёҖеј жҠҳеҸ зҡ„зәёпјҢж•…дҪңзҘһз§ҳең°еңЁеҮ дәәйқўеүҚдёҖжҷғпјҢеҸҲиҝ…йҖҹ收еӣһпјҡвҖңдҝЎдёҚдҝЎз”ұдҪ 们вҖҰвҖҰиҝҷеҸҜжҳҜд»ҺзӨјйғЁд№ҰеҗҸйӮЈе„ҝиҠұеӨ§д»·й’ұд№°жқҘзҡ„вҖҳеҶ…е®ҡеҗҚеҪ•вҖҷпјҢи°ҒжҺ’第еҮ пјҢиҠұдәҶеӨҡ少银еӯҗпјҢдёҖжё…дәҢжҘҡпјҒвҖқ
д»–иҝҷз•ӘеҚҠйҒ®еҚҠжҺ©зҡ„е§ҝжҖҒпјҢзһ¬й—ҙеӢҫиө·дәҶжүҖжңүдәәзҡ„еҘҪеҘҮеҝғдёҺдёҚз”ҳгҖӮ
еңЁдёүдәәзҡ„еҶҚдёүвҖңйҖјй—®вҖқдёӢпјҢй’ұеҚҒдёүжүҚвҖңдёҮиҲ¬ж— еҘҲвҖқең°е°ҶйӮЈд»ҪдјӘйҖ дҪҶз»ҶиҠӮйҖјзңҹеҲ°еҸҜжҖ•зҡ„иҲһејҠеҗҚеҪ•йҖ’дәҶеҮәеҺ»гҖӮ
еҗҚеҚ•д№ӢдёҠпјҢжқҺжҷҜжЎ“д№ӢеӯҗвҖңжқҺжүҝдёҡвҖқдёүеӯ—пјҢиө«з„¶й«ҳеұ…жҰңйҰ–пјҒ
дёүжӣҙйј“е“ҚпјҢеҜ’йЈҺиҗ§з‘ҹгҖӮ
йӮЈд»ҪеҗҚеҪ•пјҢе·ІеҰӮй•ҝдәҶзҝ…иҶҖдёҖиҲ¬пјҢеңЁеҹҺеҚ—еҗ„еӨ§д№ҰиӮҶй—ҙз–ҜзӢӮдј жҠ„гҖӮ
иҜ»д№Ұдәәзҡ„ж„ӨжҖ’пјҢдёҖж—Ұиў«зӮ№зҮғпјҢдҫҝеҰӮзҮҺеҺҹд№ӢзҒ«гҖӮ
第дә”ж—Ҙжё…жҷЁпјҢеӨ©еҲҡз ҙжҷ“гҖӮ
ж•°еҚҒеҗҚиЎЈиЎ«иӨҙиӨӣзҡ„еҜ’й—ЁеӯҰеӯҗпјҢзҫӨжғ…жҝҖж„Өең°еӣҙе өеңЁзӨјйғЁиЎҷй—ЁеҸЈпјҢ他们й«ҳдёҫзқҖжҠ„еҪ•зҡ„еҗҚеҪ•пјҢжҢҜиҮӮй«ҳе‘јпјҡвҖң科дёҫиҲһејҠпјҢеӨ©зҗҶйҡҫе®№пјҒвҖқвҖңиҝҳжҲ‘е…¬йҒ“пјҢдёҘжғ©иөғе®ҳпјҒвҖқ
еЈ°жөӘж»”еӨ©пјҢиҝ…йҖҹжғҠеҠЁдәҶж•ҙдёӘе®ҳеңәгҖӮ
еҗ‘жқҘд»ҘеҲҡжӯЈдёҚйҳҝи‘—з§°зҡ„еҫЎеҸІеҸ°й—»йЈҺиҖҢеҠЁпјҢж•°йҒ“еј№еҠҫжқҺжҷҜжЎ“дёҺзӨјйғЁзҡ„еҘҸжҠҳпјҢйӣӘзүҮиҲ¬йЈһе…ҘеӨ§еҶ…гҖӮ
й—ӯж®ҝдёүж—Ҙзҡ„зҡҮеёқз»ҲдәҺжңүдәҶеҠЁйқҷвҖ”вҖ”йҫҷйўңеӨ§жҖ’пјҢдёӢд»ӨеҪ»жҹҘпјҢжүҖжңүиҜ•еҚ·з«ӢеҲ»е°ҒеӯҳпјҢдәӨз”ұеӨ§зҗҶеҜәгҖҒеҲ‘йғЁгҖҒйғҪеҜҹйҷўдёүеҸёдјҡе®ЎпјҒ
еӨӘе°үеәңеҶ…пјҢжқҺжҷҜжЎ“ж°”еҫ—е°ҶеҝғзҲұзҡ„еҸӨи‘ЈиҠұ瓶摔еҫ—зІүзўҺпјҢжҡҙи·іеҰӮйӣ·гҖӮ
д»–жҢҮзқҖеҝғ腹幕еғҡзҺӢйҖҡзҡ„йј»еӯҗжҖ’еҗјпјҡвҖңжҹҘпјҒз»ҷжҲ‘жҹҘпјҒеҲ°еә•жҳҜе“ӘдёӘзҺҜиҠӮеҮәдәҶзә°жјҸпјҒжҲ‘иҰҒжҠҠжі„еҜҶд№ӢдәәзўҺе°ёдёҮж®өпјҒвҖқ
зҺӢйҖҡдёҚ愧жҳҜеҮәдәҶеҗҚзҡ„й…·еҗҸпјҢжүӢж®өзӢ иҫЈпјҢж•ҲзҺҮжһҒй«ҳгҖӮ
дёҖеӨңд№Ӣй—ҙпјҢд»–еҠЁз”ЁжүҖжңүеҠӣйҮҸпјҢжӢҳжҚ•дәҶеҚҒдҪҷеҗҚеҸӮдёҺдј жҠ„еҗҚеҪ•зҡ„д№Ұз”ҹе’Ңд№ҰиӮҶиҖҒжқҝгҖӮ
дёҘеҲ‘йҖјдҫӣд№ӢдёӢпјҢз«ҹзңҹзҡ„д»ҺдёҖдёӘд№ҰиӮҶзҡ„еӯҰеҫ’еҸЈдёӯпјҢжҢ–еҮәдәҶеҗ‘д»–е…ңе”®еҗҚеҪ•зҡ„зӨјйғЁе°ҸеҗҸгҖӮ
дәәиҜҒзү©иҜҒдҝұеңЁпјҢйӮЈе°ҸеҗҸеҫҲеҝ«дҫҝеңЁй…·еҲ‘дёӢвҖңжӢӣдҫӣвҖқпјҢжүҝи®ӨиҮӘе·ұеӣ иҙӘиҙўиҖҢеҒ·еҪ•дәҶйғЁеҲҶеҗҚеҚ•гҖӮ
жқҺжҷҜжЎ“еҫ—зҹҘж¶ҲжҒҜпјҢеҝғдёӯзЁҚе®үгҖӮ
иҷҪ然丢дәҶи„ёйқўпјҢдҪҶеҸӘиҰҒжҠҠзҪӘеҗҚйғҪжҺЁеҲ°иҝҷдёӘе°ҸеҗҸиә«дёҠпјҢе°ҶжӯӨжЎҲе®ҡжҖ§дёәвҖңе°ҸеҗҸиҙӘиҙўжі„еҜҶвҖқпјҢд»–дҫҝиғҪд»ҺйЈҺжҡҙдёӯеҝғи„ұиә«гҖӮ
д»–еҚҙдёҚзҹҘйҒ“пјҢиҝҷдёӘзңӢдјје®ҢзҫҺзҡ„вҖңжӣҝзҪӘзҫҠвҖқпјҢжӯЈжҳҜиҙҫиҜ©еҖҹй’ұеҚҒдёүд№ӢжүӢпјҢж—©еңЁеҚҠжңҲеүҚе°ұз”ЁйҮҚйҮ‘е®үжҸ’иҝӣзӨјйғЁзҡ„дёҖжһҡй—ІжЈӢгҖӮ
йӮЈе°ҸеҗҸзҡ„дҫӣиҜҚпјҢз»ҸиҝҮиҙҫиҜ©зҡ„зІҫеҝғи®ҫи®ЎпјҢзңӢдјјеӨ©иЎЈж— зјқпјҢеҚҙеңЁжңҖе…ій”®зҡ„ең°ж–№пјҢеҲ»ж„ҸйҒ—жјҸдәҶвҖңеҰӮдҪ•жҺҘи§ҰеҲ°жүҖжңүеҗҚеҚ•вҖқиҝҷдёҖзҺҜиҠӮпјҢе·§еҰҷең°з•ҷдёӢдәҶдёҖдёӘвҖң幕еҗҺеҸҰжңүдё»дҪҝвҖқзҡ„е·ЁеӨ§жӮ¬еҝөгҖӮ
иҗ§е°ҳе®үеқҗдәҺдёҖй—ҙдёҚиө·зңјзҡ„иҢ¶жҘјдәҢжҘјйӣ…й—ҙпјҢзӘ—еӨ–дҫҝжҳҜе–§й—№зҡ„иЎ—еёӮгҖӮ
й’ұеҚҒдёүжӯЈдҪҺеЈ°жұҮжҠҘзқҖзҺӢйҖҡзҡ„жңҖж–°еҠЁеҗ‘пјҡвҖңе…¬еӯҗпјҢзҺӢйҖҡе·Із»ҸејҖе§ӢжҖҖз–‘зӨјйғЁеҶ…йғЁиҝҳжңүй¬јпјҢжӯЈеңЁз§ҳеҜҶжҺ’жҹҘжүҖжңүдәІдҝЎгҖӮвҖқ
иҗ§е°ҳй—»иЁҖпјҢеҸӘжҳҜиҪ»е•ңдәҶдёҖеҸЈйҰҷиҢ—пјҢзҘһиүІж·Ўз„¶гҖӮ
д»–жҸҗиө·з¬”пјҢеңЁйқўеүҚзҡ„е®ЈзәёдёҠпјҢеҶҷдёӢдёүиЎҢйҫҷйЈһеҮӨиҲһзҡ„е°Ҹеӯ—пјҡ
вҖңж”ҫйЈҺвҖ”вҖ”жқҺжүҝдёҡж–Үз« еҮәиҮӘжһӘжүӢиғЎз§ҖжүҚд№ӢжүӢгҖӮвҖқ
вҖңиҜұйҘөвҖ”вҖ”许其全家и„ұзҪӘдҝқе‘ҪгҖӮвҖқ
вҖңж—¶жңәвҖ”вҖ”ж®ҝиҜ•еүҚеӨңгҖӮвҖқ
д»–е°ҶзәёжқЎжҠҳеҘҪпјҢйҖ’з»ҷиә«еҗҺзҡ„еҪұжңҲгҖӮ
еҪұжңҲжҺҘиҝҮпјҢиә«еҪўдёҖй—ӘпјҢдҫҝеҰӮй¬јйӯ…иҲ¬ж¶ҲеӨұеңЁиҢ¶жҘјзҡ„йҳҙеҪұдёӯгҖӮ
еҪ“еӨңпјҢеҹҺеҢ—дёҖеә§з ҙеәҷеҶ…гҖӮ
дёҖдёӘиЎЈиЎ«з ҙж—§гҖҒеҪўе®№жһҜж§Ғзҡ„иҖҒз§ҖжүҚвҖ”вҖ”иғЎз§ҖжүҚпјҢжӯЈиң·зј©еңЁи§’иҗҪйҮҢз‘ҹз‘ҹеҸ‘жҠ–гҖӮ
д»–дҫҝжҳҜеӨҡе№ҙжқҘдёҖзӣҙжӣҝжқҺжүҝдёҡд»ЈеҶҷе…«иӮЎгҖҒзӯ–и®әзҡ„вҖңжһӘжүӢвҖқгҖӮ
иҲһејҠжЎҲдёҖеҸ‘пјҢд»–дҫҝжҲҗдәҶжғҠеј“д№ӢйёҹгҖӮ
дёҖдёӘвҖңеҒ¶з„¶вҖқи·ҜиҝҮиў«д»–ж•‘жөҺдәҶеҚҠдёӘйҰ’еӨҙзҡ„д№һдёҗпјҢеңЁд»–иҖіиҫ№дҪҺиҜӯпјҡвҖңжңүдәәж„ҝеҮәдёҖеҚғдёӨй»„йҮ‘пјҢдҝқдҪ 全家иҖҒе°Ҹе®ү然еҮәеҹҺжҙ»е‘ҪгҖӮдҪ жүҖиҰҒеҒҡзҡ„пјҢеҸӘжҳҜеңЁж®ҝиҜ•ж”ҫжҰңйӮЈж—ҘпјҢеҪ“дј—е°ҶзңҹзӣёиҜҙеҮәжқҘгҖӮвҖқ
иғЎз§ҖжүҚжө‘иә«еү§йңҮпјҢиғҢеҸӣжқҺ家зҡ„дёӢеңәпјҢд»–жғійғҪдёҚж•ўжғігҖӮ
дҪҶйӮЈд№һдёҗжҺҘдёӢжқҘиҜҙзҡ„иҜқпјҢеҚҙи®©д»–еҪ»еә•еҙ©жәғпјҡвҖңзҺӢйҖҡзҡ„жүӢж®өдҪ иҜҘжё…жҘҡпјҢд»–еҫҲеҝ«е°ұдјҡжҹҘеҲ°дҪ еӨҙдёҠгҖӮеҲ°йӮЈж—¶пјҢдҪ дёҚдҪҶиҮӘе·ұиҰҒжӯ»пјҢдҪ зҡ„еҰ»е„ҝвҖҰвҖҰжҒҗжҖ•дјҡз”ҹдёҚеҰӮжӯ»гҖӮвҖқ
еңЁж— е°Ҫзҡ„й»‘жҡ—дёҺжёәиҢ«зҡ„з”ҹжңәд№Ӣй—ҙпјҢд»–йўӨжҠ–дәҶи®ёд№…пјҢз»ҲжҳҜеғҸжҠ“дҪҸдәҶжңҖеҗҺдёҖж №ж•‘е‘ҪзЁ»иҚүиҲ¬пјҢйҮҚйҮҚең°зӮ№дәҶзӮ№еӨҙгҖӮ
ж®ҝиҜ•еүҚеӨңпјҢеӨ©е…¬дёҚдҪңзҫҺпјҢйЈҺйӣЁеҶҚиҮігҖӮ
еӨӘе°үеәңзҡ„д№ҰжҲҝпјҢзҒҜзҒ«йҖҡжҳҺпјҢж°”ж°ӣеҺӢжҠ‘еҫ—д»ҝдҪӣиҰҒж»ҙеҮәж°ҙжқҘгҖӮ
зҺӢйҖҡиә¬иә«е‘ҲдёҠжңҖж–°зҡ„и°ғжҹҘз»“жһңпјҡвҖңеӨ§дәәпјҢиғЎз§ҖжүҚвҖҰвҖҰеӨұиёӘдәҶгҖӮжҚ®жҹҘпјҢд»–еҰ»еӯҗжҳЁеӨң收еҲ°дёҖдёӘеҢҝеҗҚзҡ„银иўӢпјҢд»Ҡж—ҘдёҖж—©дҫҝеёҰзқҖеӯ©еӯҗзҰ»ејҖдәҶдә¬еҹҺгҖӮвҖқ
вҖңиҪ°йҡҶпјҒвҖқдёҖйҒ“й—Әз”өеҲ’з ҙеӨңз©әпјҢжҳ з…§еҮәжқҺжҷҜжЎ“жүӯжӣІиҖҢзӢ°зӢһзҡ„йқўе®№гҖӮ
д»–жҖ’жһҒеҸҚ笑пјҢ笑声дёӯе……ж»ЎдәҶз–ҜзӢӮзҡ„жқҖж„ҸпјҡвҖңеҘҪпјҢеҘҪеҫ—еҫҲпјҒдёҖзҫӨиқјиҡҒпјҢд№ҹж•ўеңЁеӨӘеІҒеӨҙдёҠеҠЁеңҹпјҢзңҹд»Ҙдёәжң¬е®ҳзҡ„еҲҖдёҚеҲ©еҗ—пјҹвҖқ
д»–зҢӣең°дёҖжӢҚжЎҢеӯҗпјҢеҜ№зҺӢйҖҡдёӢиҫҫдәҶжңҖеҗҺзҡ„жҢҮд»ӨпјҡвҖңдј д»ӨдёӢеҺ»пјҢжҳҺж—Ҙж®ҝиҜ•пјҢжүҖжңүзҰҒеҶӣеҲҖдёҠиҶӣпјҢз®ӯдёҠејҰпјҒиӢҘжңүд»»дҪ•дәәеңЁж®ҝеүҚе–§е“—пјҢдёҚи®әиә«д»ҪпјҢдёҚи®әзјҳз”ұпјҢж јжқҖеӢҝи®әпјҒвҖқ
еҗҢдёҖж—¶еҲ»пјҢиҗ§е°ҳиҙҹжүӢз«ӢдәҺеҲ«йҷўзҡ„еұӢйЎ¶д№ӢдёҠпјҢд»»з”ұеҶ°еҶ·зҡ„йӣЁж°ҙжү“ж№ҝд»–зҡ„иЎЈиўҚгҖӮ
д»–йҒҘйҒҘжңӣзқҖзӨјйғЁзҡ„ж–№еҗ‘пјҢйӮЈйҮҢдјјд№ҺжңүзҒ«е…үеңЁйЈҺйӣЁдёӯж‘ҮжӣігҖӮ
д»–иә«еҗҺзҡ„еҪұжңҲпјҢеҰӮдёҖйҒ“зңҹжӯЈзҡ„еҪұеӯҗпјҢжӮ„ж— еЈ°жҒҜгҖӮ
вҖңдј д»Өй’ұеҚҒдёүпјҢвҖқиҗ§е°ҳзҡ„еЈ°йҹідёҚеӨ§пјҢеҚҙжё…жҷ°ең°з©ҝйҖҸдәҶйЈҺйӣЁпјҢвҖңжҳҺж—ҘеҚҲж—¶дёүеҲ»пјҢи®©е…ЁеҹҺжүҖжңүзҡ„иҜҙд№ҰдәәпјҢеңЁеҗ„иҮӘзҡ„еңәеӯҗйҮҢпјҢеҗҢж—¶ејҖи®ІдёҖдёӘж–°ж•…дәӢпјҢеҗҚеӯ—е°ұеҸ«вҖ”вҖ”гҖҠеҜ’й—ЁиЎҖжҰңгҖӢгҖӮвҖқ
иҜқйҹіеҲҡиҗҪпјҢеӨ©йҷ…д№ӢдёҠпјҢдёҖйҒ“жғҠйӣ·жҜ«ж— еҫҒе…Ҷең°зӮёе“ҚпјҢйӮЈзҙ«зҷҪиүІзҡ„з”өе…үд»ҝдҪӣиҰҒе°Ҷж•ҙдёӘеӨң幕撕жҲҗдёӨеҚҠпјҢз…§дә®дәҶдә¬еҹҺжҜҸдёҖеј жҲ–жғҠжҒҗгҖҒжҲ–жңҹеҫ…гҖҒжҲ–йә»жңЁзҡ„и„ёгҖӮ
иҝҷеңәеҚіе°ҶеҲ°жқҘзҡ„ж–ҮеңәйЈҺжҡҙпјҢз»ҲдәҺж•Іе“ҚдәҶе®ғжңҖе“Қдә®пјҢд№ҹжңҖиЎҖи…Ҙзҡ„第дёҖеЈ°дё§й’ҹгҖӮ
ж•ҙдёӘдә¬еҹҺпјҢ已然жҲҗдәҶдёҖеә§е·ЁеӨ§зҡ„жЈӢзӣҳпјҢжүҖжңүзҡ„жЈӢеӯҗйғҪе·Іе°ұдҪҚпјҢеҸӘеҫ…жҳҺж—Ҙзҡ„еӨӘйҳіеҚҮиө·пјҢйӮЈжү§жЈӢзҡ„жүӢпјҢдҫҝиҰҒиҗҪдёӢеҶіе®ҡз”ҹжӯ»зҡ„дёҖеӯҗгҖӮ
еӨңиүІж·ұжІүпјҢжқҖжңәеӣӣдјҸпјҢж— дәәзҹҘжҷ“пјҢеҪ“й»ҺжҳҺеҲ°жқҘд№Ӣж—¶пјҢиҝҷеә§еёқйғҪе°Ҷдјҡиў«жҖҺж ·зҡ„дёҖеңәиЎҖиүІжүҖжөёжҹ“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ө¶е°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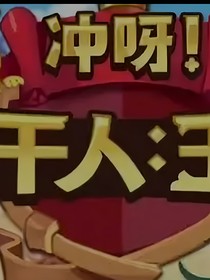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йҘје№ІдәӢи®°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еңЁејӮз•Ңзә№д№қйҫҷжӢүжЈә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Ҫ’е°ҳеҲӣдё–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家з”өи§ҶжңәиғҪз©ҝи¶ҠдёҮз•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