зђђдЇМеНБдєЭзЂ† зЙєжЃК
йЩҐиІТзЪДй£ОйУГ襀жЩЪй£ОжЛВеЊЧеПЃељУдљЬеУНпЉМзЙІдєШй£ОеЊАзЂєж§ЕдЄКдЄАзШЂпЉМй°ЇжЙЛжП™дЇЖзЙЗзЂєеПґеПЉеЬ®еШійЗМпЉМеРЂз≥КеЬ∞еПєж∞ФгАВ
жЬИеЕЙжЈМињЗйЭТз†ЦеЬ∞пЉМе∞ЖдїЦзЪДељ±е≠РжЛЙеЊЧиАБйХњпЉМеАТи°ђеЊЧињЩйЩҐе≠Рж†Ље§ЦеЃЙйЭЩгАВ
жЦєжЙНиРІдЇСзРЉзЬЉеЇХйВ£зВєиЧПдЄНдљПзЪДжИЊж∞ФпЉМеГПж†єзїЖйТИдЉЉзЪДжЙОеЬ®дїЦењГдЄКгАВ
ињЩе∞Пе≠РеИЖжШОжШѓжЬЙеЕ•й≠ФзЪДиЛЧе§ідЇЖпЉМеБПеБПиЗ™еЈ±ињШжЖЛзЭАдЄНиВѓиѓівАФвАФдєЯжШѓпЉМжНҐи∞Б襀жЬАдњ°дїїзЪДдЇЇжЭАдЇЖпЉМењГйЗМйГљеЊЧзХЩйБУзЦ§гАВ
вАЬеЫЫеЄИеЉЯеИЪйЧЃжИСпЉМиЛ•дїЦеЕ•й≠ФжИСдЉЪе¶ВдљХгАВзФ±ж≠§еПНжО®пЉМдЄКдЄАдЄЦдїЦењЕзДґеЕ•й≠ФдЇЖгАВ
дљЖе§ІеЄИеЕДзїЭйЭЮеЫ†дїЦеЕ•й≠Фе∞±зЧЫдЄЛжЭАжЙЛзЪДдЇЇпЉМжАІж†ЉдљњзДґпЉМдїЦеБЪдЄНеЗЇињЩзІНдЇЛгАВвАЭ
дїЦеѓєзЭАз©Їж∞ФеШАеТХпЉМжМЗе∞ЦжЧ†жДПиѓЖжХ≤зЭАжЙґжЙЛпЉМвАЬзЕІе§ІеЄИеЕДйВ£йЧЈиСЂиК¶зЪДжАІе≠РпЉМзЯ•йБУињЩдЇЛпЉМжАХжШѓжЖЛдЇЖеП•вАШдљ†иЛ•ж≤°иЄПйФЩиЈѓпЉМжИСдЊњжК§дљ†еИ∞еЇХвАЩпЉМеПѓжГЬдњ°жБѓдЉ†йАТ姱зЬЯпЉМе∞±жИРдЇЖвАШдљ†жХҐиµ∞йФЩдЄАж≠•жИСе∞±еКИдЇЖдљ†вАЩгАВвАЭ
дїЦеХІдЇЖе£∞пЉМжГ≥жГ≥йВ£еЬЇжЩѓе∞±иІЙеЊЧжЖЛе±ИпЉМвАЬиРІеЄИеЉЯзЉЇзЪДеУ™жШѓиІ£йЗКпЉМжШѓеП•жШОжШОзЩљзЩљзЪДвАШжИСдњ°дљ†вАЩеХКгАВвАЭ
иРІдЇСзРЉзЪДиЇЂдЄЦдїЦжЧ©жЬЙиА≥йЧїпЉМиЗ™еєЉзИґжѓНеПМдЇ°пЉМиРІеЃґеИЖеЃґзЪДдЇЇзЮІдЄНдЄКдїЦпЉМеНБе≤БйВ£еєіињЮеФѓдЄАжК§зЭАдїЦзЪДе•ґе•ґдєЯиµ∞дЇЖгАВ
жЙУе∞ПеЬ®еЃЧйЧ®йЗМе∞ПењГзњЉзњЉиЃ®зФЯжіїпЉМињЩж†ЈзЪДдЇЇжЬАжШѓжХПжДЯгАВ
дљ†зїЩдїЦдЄАеП•ж®°ж£±дЄ§еПѓзЪДиѓЭпЉМдїЦиГљеЬ®ењГйЗМзњїжЭ•и¶ЖеОїжГ≥дЄКзЩЊйБНпЉМиґКжГ≥иґКиІЙеЊЧжШѓиЗ™еЈ±зЪДйФЩгАВ
зЙІдєШй£ОжПЙдЇЖжПЙзЬЙењГпЉМењљзДґжГ≥иµЈдЄКжђ°иІБиРІдЇСзРЉеБЈеБЈзїЩеРОе±±зЪДжµБжµ™зМЂеЦВй£ЯпЉМеК®дљЬиљїеЊЧзФЯжАХеРУзЭАеѓєжЦєвАФвАФй™®е≠РйЗМжШОжШОиљѓеЊЧеЊИпЉМеБПи¶Би£ЕжИРеЄ¶еИЇзЪДж†Је≠РгАВ
зЂєеПґеЬ®йљњй׳襀еЪЉеЊЧеПСжґ©пЉМзЙІдєШй£ОеРРжОЙжЃЛжЄ£пЉМжЬЫзЭАж™РиІТзЪДжЬИдЇЃеЗЇз•ЮгАВ
дїЦжАїиІЙеЊЧе§ІеЄИеЕДиЇЂдЄКжЬЙзІНиѓідЄНеЗЇзЪДињЭеТМжДЯвАФвАФжШОжШОжШѓеЖЈз°ђзЪДжАІе≠РпЉМеНідЉЪеЬ®еЉЯе≠РзїГеЙСеПЧдЉ§жЧґпЉМжВДжВДеЊАиНѓеЇРе°ЮзУґдЄКе•љзЪДйЗСзЦЃиНѓпЉЫжШОжШОеѓєи∞БйГљжЈ°жЈ°зЪДпЉМеНіжАїеЬ®жЬЫжЬИжЧґзЫѓзЭАиРІдЇСзРЉзЪДжЦєеРСзЬЛеНКжЩМпЉМйВ£зЬЉз•ЮйЗМиЧПзЭАзЪДе§НжЭВпЉМдЄНеГПеНХзЇѓзЪДеРМйЧ®дєЛи∞КгАВ
вАЬе§ІеЄИеЕДпЉМжАХдЄНжШѓдєЯиЧПзЭАдїАдєИдЇЛгАВвАЭдїЦжСЄзЭАдЄЛеЈізРҐз£®пЉМвАЬеОїеєіжИСиЈЯдїЦжПРй≠ФдњЃжНЃзВєзЪДдљНзљЃпЉМдїЦињЮжЯ•иѓБйГљж≤°жЯ•иѓБе∞±еОїдЇЖпЉМеАТеГПжШѓжЧ©е∞±зЯ•йБУдЉЉзЪДгАВињШжЬЙдїЦзЬЛиРІеЄИеЉЯзЪДзЬЉз•ЮпЉМеУ™жШѓзЬЛеЄИеЉЯзЪДж†Је≠РпЉЯеИЖжШОжШѓвА¶вА¶вАЭ
дїЦжГ≥дЄНеЗЇеРИйАВзЪДиѓНпЉМеП™иІЙеЊЧйВ£зЬЉз•ЮеГП襀е≤БжЬИз£®еЊЧеПСдЇЃзЪДеЙСйЮШпЉМзЬЛзЭАж≤ЙеѓВпЉМеЖЕйЗМеНіиЧПзЭАзњїжґМзЪДжШЯж≤≥гАВ
е§Ьй£ОеНЈзЭАж°ВиК±й¶ЩжЉЂињЫжЭ•пЉМзЙІдєШй£ОдЉЄдЇЖдЄ™жЗТиЕ∞гАВ
з©њиґКеИ∞ињЩдњЃдїЩзХМжЬђе∞±е§Яз¶їе•ЗдЇЖпЉМеБПеПИжТЮдЄКињЩдЄАжСКе≠РеЙНдЄЦдїКзФЯзЪДзЇ†иСЫгАВ
дїЦжЩГдЇЖжЩГиДСиҐЛпЉМжККйВ£дЇЫе§НжЭВзЪДжО®жµЛзФ©еЉАпЉЪвАЬзЃ°дїЦдЄКдЄАдЄЦжШѓеИАеЕЙеЙСељ±ињШжШѓи°АжµЈжЈ±дїЗпЉМињЩдЄАдЄЦе§ІеЃґйГље•ље•љжіїзЭАпЉМе∞±жѓФдїАдєИйГљеЉЇгАВвАЭ
иЗ≥дЇОйВ£дЇЫиЧПеЬ®жЧґеЕЙйЗМзЪДзІШеѓЖпЉМжАїжЬЙдЄА姩дЉЪеГПињЩйЩҐиІТзЪДй£ОйУГпЉМ襀й£ОдЄАеРєпЉМе∞±жККиѓ•иѓізЪДиѓЭйГљжКЦиРљеЗЇжЭ•гАВ
з¶їеЕГжЧ•ињШжЬЙдЄЙ姩пЉМжЬЫжЬИеєњеЬЇзЪДйШµзЇєеЬ®жЧ•еЕЙдЄЛж≥ЫзЭАжµЕйЗСиЙ≤зЪДеЕЙгАВ
зЙІдєШй£ОеПЙзЭАиЕ∞зЂЩеЬ®йЂШеП∞дЄКпЉМеЧУе≠РйГљењЂеЦКеУСдЇЖпЉЪвАЬдЄЬиЊєпЉБиѓідЇЖеЊАдЄЬиµ∞пЉБдљ†дїђж؃襀йШµзЇєеРЄдЇЖй≠ВеРЧпЉЯвАЭ
дЄЛжЦєзЪДеЉЯе≠РдїђжЙЛењЩиДЪдє±еЬ∞и∞ГжХізЂЩдљНпЉМиИЮеЙСзЪДеК®дљЬйГљйАПзЭАиВ°ењГиЩЪгАВ
ињЩзЊ§е∞Пе≠Реє≥ж״襀дїЦзЃ°еЊЧжЭЊжХ£жГѓдЇЖпЉМињЩдЉЪеДњз®НдЄАдЄ•еОЙе∞±жЕМдЇЖз•ЮпЉМињЮжЬАеЯЇз°АзЪДеЙСз©ЧеПШдљНйГљиГљйФЩеЊЧдЄГйЫґеЕЂиРљгАВ
вАЬќµ=(¬іќњпљА*)))еФЙвАФвАФвАЭзЙІдєШй£ОеИЪжГ≥еЖНй™ВдЄ§еП•пЉМжЙЛйЗМе∞±иҐЂе°ЮдЇЖдЄ™еЗЙдЄЭдЄЭзЪДдЄЬи•њгАВ
вАЬеЕИж≠ЗзЭАгАВвАЭжЕХзГЫйШБзЪДе£∞йЯ≥еЬ®е§ій°ґеУНиµЈпЉМжОМењГињШжЙШзЭАеЗ†йҐЧиκ洶зЪДзБµжЮЬпЉМжЮЬзЪЃдЄКж≤ЊзЭАжЩ®йЬ≤пЉМдЄАзЬЛе∞±зЯ•йБУжШѓеИЪдїОеРОе±±зБµеЬГжСШзЪДгАВ
дїЦиє¶еИ∞жЧБиЊєзЪДзЯ≥йШґеЭРдЄЛпЉМзЬЛзЭАжЕХзГЫйШБиµ∞дЄКйЂШеП∞пЉМењљзДґиІЙеЊЧињЩеЬЇжЩѓжЬЙзВєзЬЉзЖЯвАФвАФе•љеГПжѓПеЫЮиЗ™еЈ±ењЩеЊЧзД¶е§ізГВйҐЭжЧґпЉМе§ІеЄИеЕДжАїдЉЪеГПињЩж†ЈжВДжЧ†е£∞жБѓеЬ∞еЗЇзО∞гАВ
зЙІдєШй£ОзЬЉзЭЫдЄАдЇЃпЉМдєЯдЄНеЃҐж∞ФпЉМжКУиµЈдЄАйҐЧе∞±еЊАеШійЗМе°ЮпЉЪвАЬињШжШѓе§ІеЄИеЕДзЦЉжИСпЉБвАЭ
дїЦзЫШиЕњеЭРеЬ®еП∞йШґдЄКпЉМзЬЛзЭАжЕХзГЫйШБиµ∞еИ∞еЬЇдЄ≠пЉМжєЫиЙ≤и°£иҐНеЬ®й£ОйЗМдЄАе±ХпЉМзЂЯжѓФеП∞дЄКзЪДйШµзЇєињШи¶БжЕСдЇЇгАВ
еЉЯе≠РдїђзЪДеПНеЇФењЂеЊЧжГКдЇЇгАВ
жЦєжЙНињШдЄЬеАТи•њж≠™зЪДйШЯдЉНзЮђйЧіжМЇзЫідЇЖиЕ∞пЉМињЮеСЉеРЄйГљжФЊиљїдЇЖгАВ
жЕХзГЫйШБж≤°иѓідЄАеП•иѓЭпЉМеП™еЊАеЬЇиЊєдЄАзЂЩпЉМйВ£еПМеє≥йЭЩжЧ†ж≥ҐзЪДзЬЉзЭЫжЙЂињЗи∞БпЉМи∞БзЪДеЙСе∞±жП°еЊЧжЫізіІдЄЙеИЖгАВ
жШОжШОдїЦињЮзЬЙе§ійГљж≤°зЪ±дЄАдЄЛпЉМеПѓжЙАжЬЙдЇЇйГљиІЙеЊЧеРОиГМеГПжКµзЭАжККеЙСвАФвАФдїњдљЫеП™и¶БеЙСе∞ЦеБПдЇЖеНКеИЖпЉМдЄЛдЄАзІТе∞±дЉЪ襀еЙСж∞ФжОАй£ЮгАВ
вАЬиµЈеКњгАВвАЭжЕХзГЫйШБзїИдЇОеЉАеП£пЉМе£∞йЯ≥дЄНйЂШпЉМеНіжЄЕжЩ∞еЬ∞дЉ†еИ∞жѓПдЄ™дЇЇиА≥дЄ≠гАВ
еЙСз©ЧеЬ®з©ЇдЄ≠еИТеЗЇжХійљРзЪДеЉІзЇњпЉМиДЪж≠•иЄПеЬ®зЯ≥жЭњдЄКзЪДе£∞йЯ≥еГПжХ≤йЉУпЉМдЄЙжђ°еПШдљНгАБдЄ§жђ°йШµеЮЛиљђжНҐпЉМзЂЯињЮеЙСз©ЧзЫЄзҐ∞зЪДжЭВйЯ≥йГљж≤°жЬЙгАВ
зЙІдєШй£ОеШійЗМзЪДзБµжЮЬеЈЃзВєжОЙеЗЇжЭ•пЉМеТВиИМйБУпЉЪвАЬеРИзЭАдљ†дїђеРГз°ђдЄНеРГиљѓеХКпЉЯвАЭ
жУНзїГзїУжЭЯжЧґпЉМеЉЯе≠РдїђзіѓеЊЧзШЂеЬ®еЬ∞дЄКпЉМеНіж≤°дЇЇжХҐжК±жА®гАВ
иЛПй±Љй±ЉжК±зЭАзБѓзЫПеЗСеИ∞еМЕжѓЕиЇЂиЊєпЉМеБЈеБЈеЊАйЂШеП∞дЄКзЮ•пЉЪвАЬдљ†зЬЛе§ІеЄИеЕДвА¶вА¶вАЭ
дЉЧдЇЇй°ЇзЭАдїЦзЪДзЫЃеЕЙзЬЛеОїпЉМеП™иІБжЕХзГЫйШБж≠£еЉѓиЕ∞зїЩзЙІдєШй£ОйАТж∞іеЫКпЉМжМЗе∞ЦзҐ∞еИ∞еѓєжЦєж±ЧжєњзЪДжЙЛиЕХжЧґпЉМињШзЙєжДПжФЊзЉУдЇЖеК®дљЬгАВ
жЦєжЙНйВ£иВ°иГљеЖїж≠їдЇЇзЪДе®БеОЛиН°зДґжЧ†е≠ШпЉМињЮзЬЙзЬЉйГљжЯФеТМдЇЖдЇЫпЉМзЂЯеГПжШѓжАХзҐ∞зҐОдЇЖдїАдєИзПНеЃЭгАВ
вАЬжИСе∞±иѓіеШЫпЉМвАЭеМЕжѓЕеОЛдљОе£∞йЯ≥пЉМвАЬдЄКжђ°дЄЙеЄИеЕД襀зљЪжКДйЧ®иІДпЉМжШОжШОжШѓе§ІеЄИеЕДдЇ≤жЙЛжККзљЪжКДжЬђйАТињЗеОїзЪДпЉМиљђе§іе∞±жЙЊйХњиАБиѓіжГЕпЉМиѓідЄЙеЄИеЕДжШѓдЄЇдЇЖи∞ГзГЯиК±йШµжЙНиѓѓдЇЖжЧґиЊ∞гАВвАЭ
вАЬињШжЬЙеОїеєійВ£жђ°еЕљжљЃпЉМе§ІеЄИеЕДдЄАжККзБЂзЗОдЇЖеНКеЇІе±±пЉМеНіеЬ®дЄЙеЄИеЕД襀зБµйєњиє≠дЇЖдЄЛиГ≥иЖКжЧґпЉМеПНжЙЛе∞±зїЩйВ£йєње•ЧдЇЖдЄ™з¶Биґ≥йШµгАВвАЭжЧБиЊєдЄАдЄ™еЬЖиДЄеЉЯе≠РжО•иѓЭпЉМзЬЉйЗМжї°жШѓеЕЂеН¶гАВ
вАЬдљ†дїђиБКдїАдєИеСҐпЉЯвАЭдЄАдЄ™еєійХњдЇЫзЪДеЖЕйЧ®еЉЯе≠РжХ≤дЇЖжХ≤дїЦзЪДиДСиҐЛпЉМвАЬдЄЙеЄИеЕДеПѓжШѓе§ІеЄИеЕДдЄАжЙЛеЄ¶е§ІзЪДпЉМиЈЯжИСдїђиГљдЄАж†ЈеРЧпЉЯељУеєідЄЙеЄИеЕДеИЪеЕ•еЃЧйЧ®жЧґжЙНйВ£дєИзВєе§ІпЉМеПСзЭАйЂШзГІиѓіиГ°иѓЭпЉМжШѓе§ІеЄИеЕДеЃИеЬ®дїЦеЇКиЊєдЄЙ姩дЄЙе§ЬпЉМдЇ≤иЗ™еЦВиНѓжУ¶иЇЂпЉМињЮеЃЧйЧ®и¶БеК°йГљжО®дЇЖгАВвАЭ
вАЬжА™дЄНеЊЧвА¶вА¶вАЭдЉЧдЇЇжБНзДґе§ІжВЯпЉМзЫЃеЕЙеЬ®йЂШеП∞дЄКдЄ§дЇЇиЇЂдЄКжЙУдЇЖдЄ™иљђпЉМењГйЗМзЪДзЦСжГСи±БзДґеЉАжЬЧгАВ
еПѓдЄНжШѓдєИпЉЯ
е§ІеЄИеЕДзЪДеЖЕеЃ§дїОдЄНиЃЄе§ЦдЇЇињЫпЉМеФѓзЛђзЙІдєШй£ОиГљжП£зЭАйЫґй£ЯеЬ®йЗМе§іжЩГжВ†пЉМжЬЙжЧґињШиГљзЬЛиІБдїЦиґіеЬ®е§ІеЄИеЕДзЪДдє¶ж°ИдЄКзЭ°иІЙпЉЫ
еЃЧйЧ®е§ІжѓФжЧґеИЂдЇЇиЊУдЇЖи¶БеПЧзљЪпЉМзЙІдєШй£ОиЊУдЇЖпЉМе§ІеЄИеЕДеНіеП™жШѓиљїжЛНдЇЖдїЦдЄАдЄЛеПЂдїЦдЄЛжђ°иЃ§зЬЯзВєпЉЫ
е∞±ињЮињЩжђ°еЇЖеЕЄпЉМжШОжШОжШѓзЙІдєШй£ОдЄАжЙЛжУНеКЮпЉМе§ІеЄИеЕДеНіжАїеЬ®дїЦиЇЂиЊєжЙУиљђпЉМйАТж∞ійАТжЮЬе≠РпЉМињЮйШµзЇєеЗЇдЇЖе∞ПйЧЃйҐШйГљи¶БдЇ≤иЗ™еЄЃењЩж£АжЯ•гАВ
йЂШеП∞дЄКпЉМзЙІдєШй£Ож≠£жЛНзЭАжЕХзГЫйШБзЪДиГ≥иЖКзђСпЉЪвАЬињШжШѓе§ІеЄИеЕДжЬЙж≥Хе≠РпЉМињЩзЊ§зЪЃзМіе∞±жЬНдљ†ињЩдЄАе•ЧгАВвАЭ
жЕХзГЫйШБзЬЛзЭАдїЦ襀зБµжЮЬж±БжЯУеЊЧдЇЃжЩґжЩґзЪДеШіиІТпЉМеЦЙзїУеЊЃдЄНеПѓжЯ•еЬ∞еК®дЇЖеК®пЉМдЉЄжЙЛжЫњдїЦжУ¶жОЙеФЗиІТзЪДж±°жЄНпЉЪвАЬеИЂзђСдЇЖпЉМеГПеП™еБЈй£ЯзЪДжЭЊйЉ†гАВвАЭ
ињЩеК®дљЬиЗ™зДґеЊЧеГПеБЪињЗеНГзЩЊйБНпЉМиРљеЬ®жЧБдЇЇзЬЉйЗМпЉМжЫіеЭРеЃЮдЇЖвАЬе§ІеЄИеЕДзЛђеЃ†дЄЙеЄИеЕДвАЭзЪДдЉ†и®АгАВ
еЉЯе≠РдїђдљОдљОеЬ∞зђСзЭАпЉМеНіж≤°дЇЇиІЙеЊЧдЄН嶕вАФвАФжѓХзЂЯжШѓдїОе∞ПжК§еИ∞е§ІзЪДеЄИеЉЯпЉМе§ЪзВєеБПзИ±дєЯж≠£еЄЄгАВ
еП™жЬЙжЕХзГЫйШБиЗ™еЈ±зЯ•йБУпЉМињЩдїљеБПзИ±йЗМиЧПзЭАе§Ъе∞СиљЃеЫЮзЪДйЗНйЗПгАВ
дїЦзЬЛзЭАзЙІдєШй£ОиґіеЬ®зЯ≥ж°МдЄКзФїдњЃжФєеЫЊпЉМзђФе∞ЦжИ≥еЊЧзЇЄй°µж≤Щж≤ЩеУНпЉМйШ≥еЕЙиРљеЬ®дїЦйїСзЩљзЫЄйЧізЪДеПСй°ґдЄКпЉМеГПиРљдЇЖе±ВзҐОйЗСгАВ
жМЗе∞ЦеЊЃеЊЃжФґзіІжЧґпЉМйВ£дЇЫжЈ±еЯЛзЪДиЃ∞ењЖеПИзњїжґМдЄКжЭ•пЉЪ
зђђдЄАзЩЊйЫґдєЭжђ°иљЃеЫЮпЉМдїЦ襀ењГй≠ФеЫ∞еЬ®еєїеҐГйЗМпЉМзЬЉзЬЛе∞±и¶БељїеЇХж≤Йж≤¶пЉМжШѓзЙІдєШй£ОжЛЦзЭА襀й≠Фж∞ФиЪАз©њзЪДиЇЂе≠РпЉМз°ђзФЯзФЯеКИеЉАеєїеҐГйЧѓињЫжЭ•пЉМжµСиЇЂжШѓи°АеНізђСеЊЧзБњзГВпЉМиѓівАЬе§ІеЄИеЕДпЉМжИСжЭ•жО•дљ†дЇЖвАЭпЉЫ
жЬЙдЄАдЄЦеЃЧйЧ®и¶ЖзБ≠пЉМдїЦ襀й≠ФдњЃжЙУжИРйЗНдЉ§иЧПеЬ®еЇЯеҐЯдЄЛпЉМжШѓзЙІдєШй£ОжК±зЭАеНКеЭЧжЯУи°АзЪДдї§зЙМпЉМеЬ®жЦ≠е£БжЃЛеЮ£йЗМжЙЊдЇЖдїЦдЄЙ姩дЄЙе§ЬпЉМжЙЊеИ∞жЧґеЧУе≠РеЈ≤зїПеУСеЊЧеПСдЄНеЗЇе£∞пЉМеНіињШжШѓжЙІзЭАеЬ∞жККдї§зЙМе°ЮињЫдїЦжЙЛйЗМпЉЫ
ињШжЬЙжЧ†жХ∞дЄ™жГ≥и¶БжФЊеЉГзЪДзЮђйЧіпЉМжШѓињЩеПМдЇЃйЧ™йЧ™зЪДзЬЉзЭЫеЗСињЗжЭ•иѓівАЬеЖНиѓХиѓХеШЫпЉМжАїдЉЪжИРзЪДвАЭпЉМжШѓињЩеПМжЙЛжЛљзЭАдїЦдїОе∞Єе±±и°АжµЈйЗМзИђиµЈжЭ•пЉМиѓівАЬе§ІеЄИеЕДдљ†зЬЛпЉМжИСдїђињШжіїзЭАеСҐвАЭгАВ
еЄИе∞Киѓіи¶БдњЭжК§жЙАжЬЙдЇЇпЉМеПѓжФѓжТСдїЦеЬ®жЧ†жХ∞иљЃеЫЮйЗМиµ∞дЄЛеОїзЪДпЉМдїОжЭ•йГљеП™жЬЙдЄАдЄ™дЇЇгАВ
вАЬе§ІеЄИеЕДпЉМдљ†зЬЛињЩж†ЈжФєи°МдЄНи°МпЉЯвАЭзЙІдєШй£ОдЄЊзЭАеЫЊзЇЄеЗСињЗжЭ•пЉМйЉїе∞Цж≤ЊдЇЖзº奮жЄНпЉМеГПеП™е∞ПеВїзЛЧгАВ
жЕХзГЫйШБдЉЄжЙЛжЫњдїЦжУ¶жОЙпЉМжМЗе∞ЦзЪДиІ¶жДЯжЄ©зГ≠жЯФиљѓпЉМеТМиЃ∞ењЖйЗМжЧ†жХ∞жђ°иІ¶зҐ∞зЪДжДЯиІЙйЗНеП†гАВ
дїЦзЬЛзЭАе∞СеєізЬЉйЗМзЪДеЕЙпЉМиљїе£∞еЇФйБУпЉЪвАЬеЧѓпЉМеЊИе•љгАВвАЭ
й£ОеДњдЊЭжЧІжШѓйВ£дЄ™й£ОеДњпЉМдЉЪйЧѓз•ЄпЉМдЉЪеБЈжЗТпЉМдЉЪеѓєзЭАзБµжЮЬдЄ§зЬЉжФЊеЕЙпЉМеТМдїЦзђђдЄАжђ°еЬ®зђђдЇФеНБдєЭдЄЦиљЃеЫЮйЗМжХСдЄЛзЪДйВ£дЄ™иЬЈзЉ©еЬ®еѓЇеЇЩйЗМзЪДе∞Пе•ґзЛЧдЄАж†ЈпЉМзЬЉйЗМж∞ЄињЬжЬЙеЕЙгАВ
иЗ≥дЇОз©њиґКиАЕзЪДзМЬжµЛпЉМдїЦдїОжЬ™жФЊеЬ®ењГдЄКгАВ
дЄНзЃ°зЙІдєШй£ОжЭ•иЗ™еУ™йЗМпЉМжШѓдљХиЇЂдїљпЉМдЇОдїЦиАМи®АпЉМйГљеП™жШѓйВ£дЄ™дЉЪеЭЪеЃЪдЄНзІїзЂЩеЬ®дїЦиЇЂиЊєпЉМйЩ™дїЦиµ∞ињЗжЧ†жХ∞зФЯж≠їзЪДй£ОеДњгАВ
ињЬе§ДзЪДйТЯе£∞еУНдЇЖпЉМжГКй£ЮдЇЖж™РдЄЛзЪДйЄље≠РгАВзЙІдєШй£ОжКђе§іжЬЫдЇЖз܊姩иЙ≤пЉМжЛљзЭАжЕХзГЫйШБзЪДиҐЦе≠РпЉЪвАЬиµ∞дЇЖе§ІеЄИеЕДпЉМиѓ•еОїзЬЛзЬЛзГЯиК±зЪДиѓХжФЊдЇЖпЉБвАЭ
жЕХзГЫйШБ襀дїЦжЛЙзЭАеЊАеЙНиµ∞пЉМиДЪж≠•иљїењЂеЊЧдЄНеГПдЄ™иГМиіЯзЭАеНГдЄЗиЃ∞ењЖзЪДдЇЇгАВ
жЧ•еЕЙз©њињЗдЇСе±ВиРљеЬ®дЄ§дЇЇиЇЂдЄКпЉМе∞Жељ±е≠РжЛЙеЊЧеЊИйХњпЉМеГПи¶БдЄАзЫіеїґдЉЄеИ∞жЧґеЕЙзЪДе∞ље§ігАВ
ињЩдЄАдЄЦпЉМдїЦжГ≥пЉМдЄАеЃЪи¶БиЃ©ињЩељ±е≠РйХњдЄАзВєпЉМеЖНйХњдЄАзВєгАВ
зЫЄеЕ≥жО®иНР
 ињЮиљљдЄ≠
ињЮиљљдЄ≠
ењГй≠ФеЙСйБУ
 ињЮиљљдЄ≠
ињЮиљљдЄ≠
еНБеЕЂиЛ±йЫМ
 ињЮиљљдЄ≠
ињЮиљљдЄ≠
еЉАе±АйУЄе∞±жЧ†дЄКж†єеЯЇпЉМжИСйЧЃйЉОдїЩиЈѓпЉБ
 ињЮиљљдЄ≠
ињЮиљљдЄ≠
жШОе†ХдєЭеє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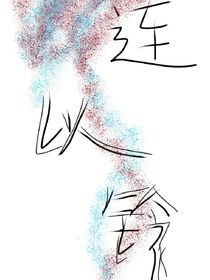 ињЮиљљдЄ≠
ињЮиљљдЄ≠
ињЮдї•йУГ
 ињЮиљљдЄ≠
ињЮиљљд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