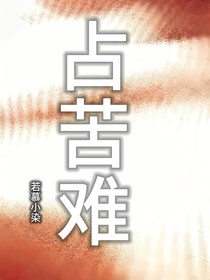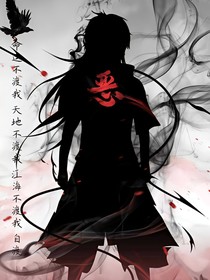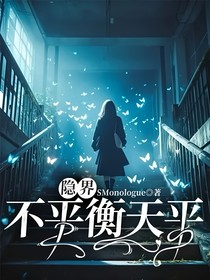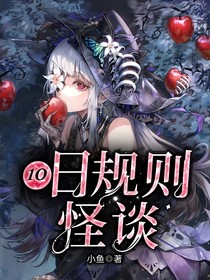第三十四章 春汛里的船影,老码头的新痕与旧诺 (2-1)
惊蛰过后的第一场雨,把槐安里的青石板洗得发亮。林深站在老码头的石阶上,望着涨潮的江水漫过脚边的青苔。码头的木桩上,不知何时被人系了串褪色的红绳,绳尾拴着片半干的兰草叶,在江风里轻轻摇晃,像在召唤着什么。
“周桂兰说,今早有人看到江面上漂着个木匣子。”沈念安踩着水洼走来,裤脚沾了些泥点,手里拎着个油纸包,里面是刚从镇上买的芝麻饼,饼香混着雨水的湿气,在空气里漫开,“她让我们去下游看看,说那匣子看着像当年陈景明船上的物件。”
码头的石阶被江水浸泡得发滑,每级台阶的缝隙里都嵌着细小的贝壳,是常年被潮水冲刷的痕迹。林深扶着斑驳的石墙往下走,墙面上刻着许多模糊的字迹,大多是“平安”“归”之类的字眼,其中一个“明”字刻得格外深,笔画边缘还留着新的凿痕,像是最近才被人加深过。
“这是陈景明当年刻的吧?”沈念安指着那个“明”字,旁边还有个小小的船锚图案,锚链的纹路清晰得能数出环数,“你看这凿痕里的泥,还带着点湿润,定是村里的老人怕它被潮水磨平,特意补刻的。”
下游的浅滩上,果然泊着个半沉的木匣子。匣子是楠木做的,表面裹着层厚厚的青苔,却在角落露出块铜制的锁扣,锁扣上刻着缠枝莲纹,和沈清沅茶罐上的纹样一模一样。林深蹚着齐膝的江水走过去,指尖触到匣子的瞬间,冰凉的木头上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像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轻轻撞击。
“小心点,别让钉子刮到。”沈念安递过把小刀,刀身裹着层油纸,是从老宅的工具箱里找到的,刀柄缠着防滑的布条,布条上绣着个极小的“沅”字,“这锁扣看着没锈死,说不定能打开。”
小刀插进锁扣缝隙的瞬间,发出“咔哒”的轻响。锁芯意外地灵活,显然是被人精心保养过。林深轻轻一旋,锁扣弹开的刹那,一股混杂着桐油、墨香和江水湿气的气息涌出来,像艘老船在水底沉睡多年,终于在春汛里苏醒。
匣子里铺着块深蓝色的帆布,帆布上绣着艘小小的帆船,船帆上用银线绣着朵兰草花,针脚被江水泡得有些松散,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精致。帆布下裹着几样物件:一本牛皮纸封面的航海日志,边角卷成了波浪形;一个铜制的指南针,指针已经锈死,却在中心刻着个“安”字;还有个巴掌大的木牌,上面刻着“归墟号”三个字,字缝里嵌着些细小的贝壳,像是特意镶嵌的。
“这日志是陈景明的。”沈念安小心地翻开日志,纸页被江水泡得有些发皱,却依旧能看清上面的字迹,“你看第一页,记着他第一次驾船去归墟的路线,旁边画着个简笔画的小人,举着朵兰草,定是沈清沅。”
日志里夹着张泛黄的船票,票面上的“归墟号”三个字已经模糊,却在边缘留着个浅浅的指印,指腹的纹路清晰得能数出,像是沈清沅捏着船票时留下的。票根处粘着根极细的红绳,绳尾系着半颗珍珠,珍珠上有道细缝,和沈清沅耳坠上的那颗一模一样。
“他们当年真的登船了。”林深指着日志里的某段记录:“四月廿八,风平浪静,清沅说兰草花开得正好,把花干收进了航海袋。”下面画着个小小的布袋,袋口露出半截兰草叶,“这木牌上的贝壳,定是她捡来镶上去的,她说归墟的贝壳能带来好运。”
木匣子的底层,藏着个意外之物:是块被海水泡得发胀的绣花绷子,绷子上还绷着块未完成的绣布,布面上绣着半只展翅的海鸥,翅膀用银线勾勒,腹尾却留着空白。沈念安认出这是沈清沅的绣工,针脚细密得像海鸥掠过水面的痕迹,“她定是在船上绣的,还没绣完就……”
话没说完,一阵春汛突然涌来,江水漫过木匣子,将绣布上的银线浸湿。奇妙的是,被水浸湿的银线竟泛起微光,在绣布上晕开,渐渐补全了海鸥的尾巴——尾巴的形状,竟和老码头石墙上的船锚图案一模一样。
槐安遗珠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占苦难
- 当你在危死之时意外穿越到了空间夹缝,这里残酷而怪诞,有无数冷血的恶人,却也存在着一群善良单纯的好人,你是如何面对的。你是否还想着要回去,尽管......
- 1.9万字9个月前
- 构思大合集
- 已经变成纯设定集了,作者我不适合写故事和人类情感大纲之类的,原来我想写个白月光、暴躁兄长、护犊子、爱兄弟、缺爱、寻死、记仇、路痴脸盲、习惯孤......
- 13.9万字3个月前
- 隐界:不平衡天平
- 异世界探险群像+慢节奏一场灾难将我带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必须选出/献祭一人,以获得逃生的机会有人自告奋勇一切都在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但事实确......
- 3.3万字3个月前
- 10日怪则怪谈
- 我叫夜林一不小心和我的朋友白杨掉入了十日怪谈世界不遵守规则就会嗄
- 0.4万字4周前
- 极北捡狼
- 主角捡到一只小狼
- 7.3万字3周前
- 火影直播剧场版传奇之旅
- 以火影忍者的世界为背景,融入直播元素,展现主角在剧场版世界中的冒险与成长。
- 3.1万字3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