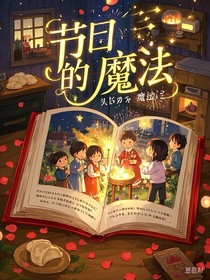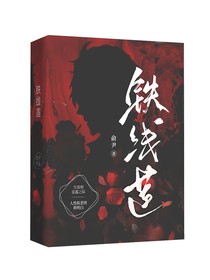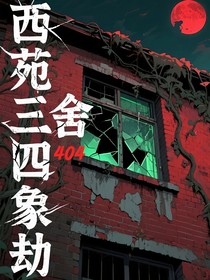第三十三章 海沟沉镜后的余波,槐安里的新绿与旧影 (2-1)
归墟的风浪平息后的第三日,林深站在沈家村码头的礁石上,望着湛蓝如洗的海面。前尘镜被沉入海沟的位置,此刻正泛着极淡的银辉,像月光洒在水面,随波轻轻晃动。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掠过脸颊,混杂着远处渔船上飘来的鱼腥,却不再有往日那股阴寒的压迫感。
“水下探测器显示,镜身周围的海水里,多出了些奇怪的浮游生物。”沈念安踩着礁石上的青苔走过来,手里拿着个平板电脑,屏幕上是水下摄像机传回的画面——漆黑的海沟深处,前尘镜被一层半透明的胶质包裹着,胶质上吸附着无数米粒大小的光点,像撒了把会发光的星子,“专家说这是从未见过的物种,能分泌净化水质的物质,就像……镜身自己养了层保护膜。”
林深的目光落在礁石的裂缝里,那里还残留着几缕黑色的絮状物,是“影”被驱散时留下的残迹,此刻正被海风一点点吹散。他想起昨夜祠堂里的情景:沈敬山的牌位在莲火中化为灰烬,黑毛燃烧时发出的不是焦糊味,而是类似陈年墨汁被点燃的清苦气,灰烬飘散在供桌上,竟在木纹里拼出个模糊的“悔”字。
“周姨说,沈家村的井水今早变清了。”沈念安收起平板,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玻璃罐,里面装着半罐井水,水中沉着片兰草叶,叶片舒展得像刚从枝头摘下,“之前被黑水污染的田地,也冒出了新芽,村民们都在田里插上了桃木牌,牌上刻着你写的‘安’字。”
林深接过玻璃罐,指尖触到冰凉的罐壁,突然注意到兰草叶的脉络里,嵌着极细的银线——不是人为缠绕的,更像是从叶片本身长出来的,在阳光下泛着微光。“这是前尘镜的净化之力渗进了土里。”他想起沈清沅嫁衣上的银线,“镜身虽被封印,却把最后的善意留在了这里。”
两人沿着海岸线往槐安里走,路过望月滩时,发现昨日裂开的沟壑已被新的泥沙填满,淤泥里钻出了成片的绿芽,叶片形状酷似兰草,却带着淡淡的银光。几个孩童正蹲在滩涂边,用树枝拨弄着绿芽,其中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突然喊道:“你们看!这草叶上有字!”
林深和沈念安凑近了看,绿芽的叶片上果然有极浅的纹路,拼凑起来是“归墟”二字,笔画柔和,像沈清沅的笔迹。更奇特的是,随着海风拂过,叶片上的字迹会微微变化,片刻后竟化作“家”字,看得孩子们拍手欢呼。
“是陈景明和沈清沅的念想在护着这片滩涂。”沈念安的眼眶有些发热,她想起那卷未显影的胶片,或许真正的影像,早已刻进了这山海草木里。
回到槐安里时,夕阳正斜斜照在17号老宅的院墙上。林深推开虚掩的木门,院子里的杂草已被清理干净,周桂兰正蹲在石榴树下,往土里埋着什么。见他们回来,老人直起身,手里捧着个布包,打开来是些兰草种子,种子外壳泛着银白的光泽。
“这是从归墟海边捡的,”周桂兰笑着把种子递给沈念安,“今早去祭拜老九,发现他坟头长了片新草,结的种子就是这样,我想着清沅妹妹最爱兰草,就采了些回来种。”
林深注意到石榴树的枝干上,挂着个小小的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平安”二字,字迹稚嫩,是村里的孩童写的。树洞里,不知何时被塞进了半块桂花糕,糕点虽已干硬,却还能看出当年的纹路——和陈景明送给沈清沅的那块一模一样。
走进堂屋,林深一眼就看到八仙桌上摆着个新物件:是用前尘镜的碎片熔铸成的小铜铃,铃身刻着缠枝莲纹,挂在红绳上,轻轻一碰就发出清越的响声。“这是老馆长让人铸的,”沈念安拿起铜铃,铃声里竟混着极轻的海浪声,“他说镜身虽沉,却该留个念想在老宅,就像清沅和景明从未离开。”
夜幕降临时,槐安里亮起了灯笼。林深和沈念安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看着周桂兰种下的兰草种子在月光下冒出细芽,芽尖顶着露珠,像缀着星星。远处传来孩童的歌谣,唱的是新编的《槐安谣》,歌词里有“兰草生,归墟宁,镜影散,故人停”,曲调婉转,像沈清沅当年哼唱的调子。
槐安遗珠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节日的魔法
- 这部小说将继续围绕顾家三兄妹的成长故事展开,讲述他们在春节的欢乐、挑战和离别中所经历的成长和变化。春节的庆祝活动将成为他们故事的起点,而他们......
- 1.4万字10个月前
- 往复的死局
- 《往复的死局》又叫《黑夜的另一个世界》张故言21岁加入组织遇到了齐川栗,在25岁时发现自己的侄子张知白也是异人,为了保护张知白自己承担了一切......
- 0.1万字9个月前
- 铁线莲
- 铁线莲--扼杀的希望危险悄然接近,究竟谁是凶手?被扼杀的希望是什么?
- 0.6万字9个月前
- 狼王梦—缘之空,圆之梦
- 逝去的时光如苦涩尘埃,缓缓坠入我的心房,花岗岩上那壮志未酬的眼神,令我难忘,再疯狂一次——缘梦……圆梦
- 1.1万字9个月前
- 恐怖合集!
- 一名隻魚的女大学生不断遇鬼的多篇故事。
- 0.4万字3个月前
- 西苑三舍:四象劫
- 这是一本有许多灵异事件所组成的一部书,书名就以第一篇短故事为名
- 5.1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