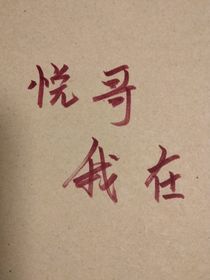第83章 初遇 (5-1)
白轲哑口无言,笑了笑没说话,她低头看向手中米黄色封皮的精装书,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诗歌集《另一个,同一个》。
其中收录的一首现代诗歌深得白轲喜爱,她反复背诵着《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的诗句,并没有要搭理谢熠城的意思。
被晾在一旁的少年闷闷不乐地站起身,他不甘心就这么被忽略,将吉他放到一边走到白轲身前,扯扯她衣袖试图引起她的注意,“别看书了白,听我给你讲故事吧?”
白轲抬眼看他,“你要讲什么故事?”
谢熠城拿过白轲手中的诗歌集,放在书柜里,微微一笑道:“讲我们的故事哦。”
闻言白轲来了兴致,“我们的故事?”
谢熠城嗯了声,“准确来说,是向你讲述第一次遇见你的那天,喜欢上你的那天。”
他牵住白轲的手,慢慢与她十指相扣,那握手的力度紧密得让白轲感到不适,她甚至分不清手指交错处,是谁的血脉在跳动。
“这是一个不算美好的故事,在我十岁那年,妈妈杀了爸爸,然后将我囚禁在了地下室……那个铁笼子里什么也没有,不像这里,那儿没有灯光没有床铺也没有食物,有的只是我爸那具白森森的骸骨。那时我真的觉得好不可思议,那么高大的一个人,妈妈竟然把他的肉全吃干净了,只剩下骨架……”
明明不是第一次听到这骇人听闻的故事,白轲却还是有种毛骨悚然的战栗感。
“我记得那天好像是我的十岁生日,不过没有蜡烛,没有蛋糕,没有礼物,只有空空如也的铁笼子,冰冷恶臭的尸体……哦对了,我记得那天的晚饭,是妈妈为我准备的——一碗来自爸爸的脑浆呢。”
“不过实在是太恶心了,我没喝……于是妈妈责怪我不听话,开始骂我打我,用皮鞭抽我……白,你恐怕永远无法体会到……当尿液不受控制从体内流出的绝望感,随后你要带着一身伤,和自己的排泄物共处一室,那里没有阳光,又臭又黑。”
“呕……简直恶心透了。”
谢熠城说着呼吸变得急促,他目呲欲裂地睁着双眼,瞳孔因极端的情绪缩得像针尖那样细。白轲感觉手心一疼,谢熠城的指甲似乎掐破了她的皮,不过白轲没敢挣脱,谢熠城的状态明显不对劲了,她用另一只空闲的手去摸谢熠城的脑袋,“没事了,已经过去了,你不用和我讲这个故事的……”
听到白轲的安抚声,谢熠城混混沌沌的目光清明了几分,他低垂下眼帘,浓密的睫羽遮挡住他那双幽光慑人的眼睛,谢熠城有些酸涩地笑了一下,“可我不讲故事的话,白就只会看书,就不会搭理我了……”
白轲呼吸一顿,心头涌上一股说不出道不明的奇异感觉。血液堵塞的右手已经开始发麻刺痛,她皱起眉头说不出话来。
“没关系的,好在过了一年后,我就遇见了你……”谢熠城微微放松抓着她手的力度,眼睛却死死锁定着两人相扣的手,“那天妈妈本来是想给我注射/毒品的,可偏偏就在那时她毒瘾发作,针管没有打到我静脉里……我趁机推开她逃了出去,我跑啊跑,一刻都不敢停歇,拼了命的跑,终于甩开了她。”
——
记得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在马路边出现了一个穿着短衣短裤的男孩,他身上的衣服都脏兮兮的,像是好久没洗过。
囚笼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悦哥,我在
- 何悦×陈成,曾诗雨×秦乐声周更3000起步
- 9.4万字4个月前
- 止与盛夏……
- 6
- 0.1万字3个月前
- 寻常—
- 普普通通的中学生活,日常但不平常,平常但不寻常。无cp,随便捡。类似于碎碎念似的短版日记,记录一些没用或者不清晰的故事。—————————-......
- 0.6万字3个月前
- 喜美:沉舟
- 夏芊妤的原创作品。禁盗禁防禁二转,被发现后果自负。喜美同人文,私设ooc致歉,请大家自行避雷。高冷规矩好学生vs张扬明艳女混混“后会无期,好......
- 0.4万字3个月前
- 女扮男装进校园
- 一个黑漆漆的夜晚,瞿家大小姐瞿雪晴无意之中惹了恶魔校草李清和,瞿家大小姐没有理他,当瞿雪晴回到家以后听到了自己爸妈的谈话。瞿母说:“我告诉你......
- 19.2万字3个月前
- 顾年和许悦之间的二三事
- 2021.09..29签约.顾年其实各个方面都没有长在许悦的择偶标准上,但在后来却是许悦借不掉的瘾,顾年可以说是凭实力和坚持不懈将许悦追到手......
- 14.0万字3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