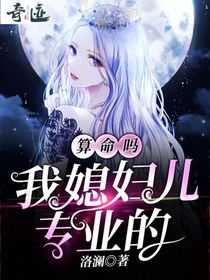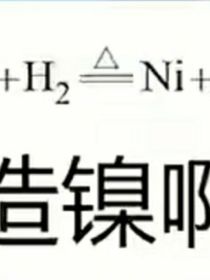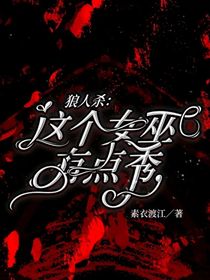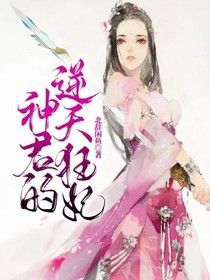类别(一) (6-3)
因此,在区分他的范畴时,康德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开始,概述了可以对任何判断进行分类的四个方面:根据其数量、质量、关系或模态。在每个方面或判断“时刻”,都存在三种可供选择的分类;因此,例如,就数量而言,判断可能是普遍的、特殊的或单一的;就其关系而言,判断可以是绝对的、假设的或析取的等等。这些亚里士多德的判断分类方法是辨别十二个相关知性概念的线索。因此,例如,通过注意到所有判断要么是普遍的(例如,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特殊的(例如,一些天鹅是白色的)或单一的(例如,Cygmund 是白色的),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相应的数量类别:统一性、多元性、整体性。通过这条路线,康德最终区分了十二个纯粹知性概念(A80/B106),分为四类,每类三类:
数量
统一
复数
整体性
质量
现实
否定
局限性
关系
固有性和存在性(实质和偶然)
因果关系和依赖性(因果关系)
社区(互惠)
模态
可能性
存在
必要性
这些类别被呈现为形成一个详尽的列表,其中四类类别将四种不同形式的统一强加于已知的对象(Paton 1936, 295-9)。因此,人们可以分别询问一个物体的数量、质量、关系和形态,在每种情况下接收三个子答案之一,从而更完整地表征该物体。
尽管这些是理解的范畴,但它们仍然保留了某种本体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普遍适用于所有可能认知的对象(A79/B105)。这样,通过描述对象认知所必需的先验概念,我们可以获得支配任何可能的认知对象的类别知识,从而获得一种描述性的本体类别集,尽管这些必须被明确地理解作为可能认知的对象的类别,而不是事物本身的类别。因此,康德能够将他的概念系统视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范畴系统,“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与他的[亚里士多德]相同,尽管在执行方式上与它大相径庭”(A80/B105 )。尽管如此,很明显,对于康德来说,这些范畴在人类理解的原则中找到了它们的原始根源,而不是在独立于心灵的现实的内在划分中,并且可以通过关注人类判断的可能形式来发现,而不是通过对世界本身的研究来发现。 ,也不是通过研究我们偶然的说话方式。
像康德这样的方法最近受到 P. F. 斯特劳森和其他追随他的人的辩护,他们承担了“描述性形而上学”的项目,该项目关注于描述“我们概念结构的最普遍的特征”(1959 [1963],xiii) ,从而提供比我们预期的语言分析更普遍、更持久的结果。
1.3 胡塞尔描述主义
埃德蒙·胡塞尔在范畴研究中引入了两种创新。首先,亚里士多德使用语言作为本体论范畴的线索,康德将概念视为通向可能认知的对象类别的途径,而胡塞尔则明确地区分了意义类别和对象类别,并试图找出意义类别与对象类别之间的类似规律的相关性。每种类型的类别(Smith 2007,139ff.)。其次,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各自提出了一个单一的范畴系统,而胡塞尔则区分了两种达到顶层本体论分类的方式:通过形式化和概括,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产生两个独立的、正交的范畴系统(参见史密斯 2004 年,第 8 章)。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算命吗?我媳妇儿专业的
- (同名有声小说已于喜马拉雅FM同步上线)顾家大少结婚了,新娘子虽然是山里来的,但长得娇软可爱,嘴甜心善,萌萌的还不错!错!大错特错!嫁人不到......
- 213.6万字3个月前
- 记录心境的奇怪
- 发疯日常而已顺便记录一下自己
- 0.6万字3个月前
- 是梦还是?我已陷入
- 一个对自己所在城市失去希望的人,因为一次偶然发现另一个世界。在这她有会遇到什么?
- 0.2万字3个月前
- 舞法天女之绚彩归来(新版)
- 混徒再次归来,天女们再次集合,这次新加入了一个天女,并且打造了一支圣天舞团,天族和混族之间的战争再次爆发
- 4.0万字3个月前
- 狼人杀:这个女巫有点秀
- 【已签约,首发话本,请勿搬运,违者必究。】【无限流,全员恶人】“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在这场游戏里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包括我。”雾音......
- 9.6万字3个月前
- 神君的逆天狂妃
- 作为华夏第五家族第三十二代族长,因族人的愚昧引来豺狼虎豹,第五汐蝶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魂穿异世。没等她高兴多久,一出生就遭雷劈,紧接着被神秘......
- 10.0万字3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