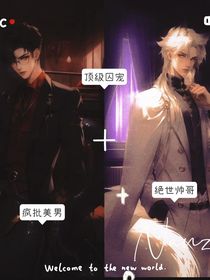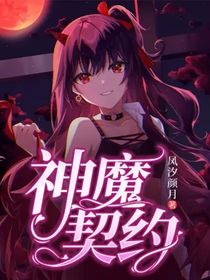类别(一) (6-4)
胡塞尔小心翼翼地将意义的范畴(通过它我们可以思考对象的最高种类或“本质”)与所指的范畴区分开来——后者是对象的范畴,或本体论范畴,被认为是最高的本质。实体可能具有:“通过‘类别’,我们一方面可以理解意义意义上的概念,但另一方面,为了更好的效果,我们还可以理解在这些意义中找到表达的形式本质本身”(1913) [1962],61-2)。尽管必须区分这两类范畴,但根据胡塞尔的说法,这两类范畴本质上是相关的(见下文),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类来了解另一类。
无论我们研究的是意义范畴还是对象范畴,胡塞尔都非常清楚,范畴的研究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先验的问题;意义和对象的类别“仅与我们不同的思维功能相关:它们的具体基础只能在可能的思维行为中找到,或者在可以在这些行为中掌握的相关性中找到”(1913) [2000],237)。正如他后来在《理念》中所说,对范畴的研究是对本质的研究,基于对意义类型和事物相关类型的本质洞察。这种对本质的研究可以通过案例的想象变化来进行,独立于任何事实,包括是否实际上存在任何区分的本体论类型(1913 [1962],5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胡塞尔的本体论范畴是可能事物的最高本质(可能属于这些本质)的描述性范畴,并不旨在提供事物实际存在的清单(作为经验事实)。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意义类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认为意义类别的差异(似乎更像句法而不是语义类别)可以通过注意到用一个术语代替另一个术语而产生的无意义来区分。例如,在“这棵树是绿色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用“椅子”——而不是“粗心”——来代替“树”,而不会将意义变成无意义,这标志着主格材料和形容词材料的含义类别之间的差异(1913 [ 2000],511-512)。胡塞尔对“废话”的理解相当严格:他只计算那些语法上不正确的词串(因此它们只是形成“词堆”,不能组合成任何统一的含义(胡塞尔 1913 [2000], 522) )完全是无意义的,因此是意义类别差异的标志。 (胡塞尔反复区分动词形式的无意义,如“a round or”(其中没有出现统一的含义)与纯粹荒谬的情况,如“a round square”,其中该表达具有统一的含义,尽管它是先验的没有对象可以对应于表达式 (1913 [2000], 516–17))。
与意义范畴相关的是本体论范畴;例如,对象、事态、单位、复数、数字和关系是对对象进行分类的(形式)类别,而不是意义(Husserl 1913 [2000], 237)。根据胡塞尔的说法,这两类范畴通过“理想法则”联系在一起。因此,例如,对象大概是主格表达的意义范畴的本体论关联,属性是形容词表达的本体论关联,事态是命题的本体论关联。因此,虽然胡塞尔(据我所知)没有明确提出一种辨别本体论范畴的方法,但我们可能可以通过从上述区分意义范畴的无意义测试开始,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相关的本体论范畴来推导出它们,因为“关于意义的纯粹真理可以转化为关于对象的纯粹真理”(1913 [1962],61)。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当星光充满夜空之时
- 时空管理员——列尔因激怒主神被惩罚在三万年内将五千个“迷路的灵魂”带回原世界。
- 0.7万字4个月前
- 顶级囚宠:被五个疯批怪物强占了!
- 温馨提示:作者灵感来自于点点穿书《顶级囚宠:被五个疯批怪物强占了!》家人们真的好喜欢这个故事啊!!!奈何作者大大一直不更新纯属娱乐,不喜勿喷......
- 0.2万字3个月前
- 似暖花开
- 【男女主一对一,专情,互宠,高洁双c】“他似暖阳,温暖着我,照亮前行的路,因为有他,无论遇到什么,我都能披荆斩棘,因他成就现在的我”一——星......
- 42.9万字3个月前
- 澄羡(创世神)
- 看评论中的通知
- 0.9万字3个月前
- 烛龙引凤,凤驭烛龙
- “他让你坠入黑暗,我就让你重见光明,不仅如此,我还要带你登上这世界的顶端,亲眼见证他从你落入过的深渊掉落,粉身碎骨、神形俱灭!”陈应龙温柔而......
- 14.6万字3个月前
- 神魔契约
- 【待更】【神作系列】地狱少女来到人类世界。
- 7.2万字3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