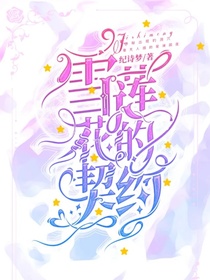形而上学(二) (6-6)
然而,大多数哲学家现在确信,奎因的“数学家单车骑手”论证已经被索尔·克里普克(1972年)、阿尔文·普兰廷加(1974年)和其他多位从物模态的辩护者所充分回答。克里普克和普兰廷加对模态的辩护在范式上是形而上学的(除了他们直接涉及奎因的语言论证)。他们都广泛使用了可能世界的概念来捍卫模态的可理解性(从物模态de re和从言模态de dicto)。莱布尼茨是第一个将“可能世界”作为艺术哲学术语的哲学家,但克里普克和普兰廷加对这个短语的使用与他的有所不同。对莱布尼茨来说,一个可能的世界就是一个可能的创造物:上帝的创造行为在于他在许多世界中,选择其中一个成为他创造的世界——即现实世界。
然而,对克里普克和普兰廷加而言,一个可能的世界就是一个可能的“现实整体”。对莱布尼茨来说,上帝和他的行为“置身于”所有可能的世界之外。对于克里普克和普兰廷加来说,没有任何存在,就算是上帝,都不能置身于整个可能世界的体系之外。一个克里普克-普兰廷加Kripke Plantinga(KP)世界是某种抽象对象。让我们假设一个KP世界是一种可能的事态(这是Plantinga的想法;Kripke没有说得那么明确)。考量任何特定的事态,比如说,巴黎是法国的首都。由于巴黎是法国的首都,这种事态成立了。相比之下,图尔作为法国首都这种事态则未成立。然而,后一种事态确实实存,因为存在这样一种事态。(因此,成立与事态的关系,正如真理与命题的关系一样:尽管图尔是法国首都的命题并不正确,但仍然存在这样一个命题。)如果事态x不可能成立而y不可能不成立,则称事态x包括事态y。如果x和y都不可能成立,则二者互相排除。一个可能的世界仅仅是一种可能的事态,对于每一种事态x,要么包括x,要么排除x,而现实世界就是这样一种事态的成立。
使用KP理论,我们可以回答奎因的挑战如下。在每一个可能的世界里,每一位骑自行车的人在该世界都是两足行走的。(假设奎因认为骑自行车的人一定是两足行走的。显然,他没有预见到可适应性的自行车。)然而,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骑车人来说,在某些可能的世界里,他(同一个人)不是两足行走的。一旦我们得出这种区别,我们就可以看出奎因的论证是无效的。更普遍地说,在KP理论中,关于从物模态本质属性的命题不必是分析性的;它们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表达了关于对象在多种可能世界中的属性的主张。
我们也可用可能世界的理念来定义许多其他模态概念。例如,一个必然真的命题,无论什么可能世界为现实,都为真。若有某个可能世界成为现实,苏格拉底则不实存,那么他是一个或然的存在;如果在每个包含他存在的可能世界,他都为人,则他本质上就具有“人”的属性。克里普克和普兰廷加(Kripke和Planting)极大地提升了模态话语(尤其是从物模态话语的)的清晰度,但代价是引入了模态本体论,即可能世界的本体论。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仙官:红尘久世故人归
- 『双男主』天涯路尽共归途,聊以相思慰红尘。喜欢君子兰的苏行?不喜红衣的谢时?“普通人”林子规?以及“千年老鬼”墨奕渊?不不不,你以为的只是你......
- 24.7万字8个月前
- 后室介绍(层群1)
- 23.1万字8个月前
- 雪莲花的契约
- 【原创勿盗】【不喜勿入】【仅在话本发布】黑蝴蝶的继承人凌思娜,又是一个拥有雪莲花契约的人。雪莲花契约现世,凌思娜根据黑蝴蝶的指引,和闺蜜洛樱......
- 12.3万字8个月前
- 失忆了那又怎样
- 世界没有纯爱是不完美的
- 14.7万字8个月前
- 快穿:反派boss太撩人啦
- 女主是一只修炼了万年的兔子精,一心想着修炼成仙,奈何遇到瓶颈期,怎么也领悟不了其中的意义,所以怎么都突破不了,不能飞升仙界.而男主是掌管万千......
- 11.1万字8个月前
- 穿越的爱没有结尾
- 【已签约】【本书连着三季,不喜勿喷】我不小心到了吸血鬼的世界,在这里我遇到了他。亏我命大,这里有我的情敌。浩然和长公主的爱情寥寥结束。魏江的......
- 5.4万字8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