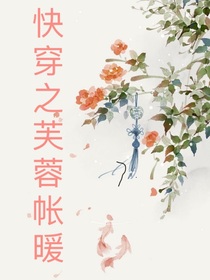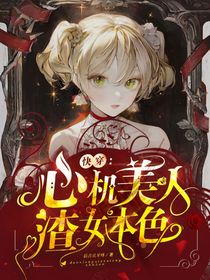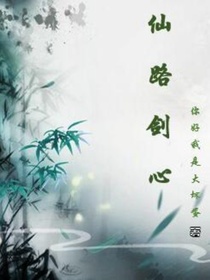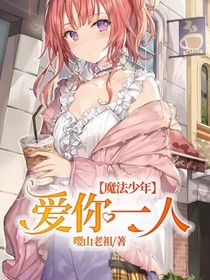哲学(二) (5-5)
这种担忧的一种形式,就是上文我们称作“道德上可赞的偏倚性”问题的另一个版本。常识观点认为,行为者偏向自己,即把他自己的规划和事情看得好象有特殊重要性似的,这是允许的(Scheffler, 1982)。(从行为者的角度看,这些当然有特殊的重要性。)进而,这种自我关切构成了一种偏倚性,而在常识的角度看,这种偏倚性是被道德认同的。后果主义不偏不倚性禁止对他人(朋友、家庭成员等等)的偏倚性,然而从常识的角度看,这种偏倚性在很多情形下同样是被认为是有道理甚至值得赞扬的(Blum 1980, Cottingham 1983, Kekes 1981, Keller 2013, Slote 1985)。此外,还有一个相关的顾虑,它关注的不是道德本身,而是关注行为者性质和个人繁荣的各种要求与条件。举例来说,詹姆斯·格里芬(James Griffin)写道,“有很多审慎的价值包括对某些特定人、机构、事业等的投入(commitments)。如果不在很大程度上是偏倚的,那么个人就没办法过上慎审意义上的好生活,也无法充分地繁荣(flourish);这种偏倚性并不是个人可以在心理上随意进出的事” (Griffin 1996, 85)。伯纳德·威廉斯认为,后果主义理论禁止行为者赋予自己的计划目标和投身的事业以更多的重要性,因此违背了行为者的完整性,并且破坏了他们为什么要有道德的一切理由(Williams 1973, 1981; cf. Hurley 2009)。(需要注意的是,威廉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反驳对康德式义务论理论也是有效的。)
对这一反驳的回应有很多。第一,后果主义者可能主张,任何真正不偏不倚的道德理论都会对行为者做出极端的要求——至少,当我们正确地理解不偏不倚性概念时。这一策略面临严峻的问题,因为至少有一些非后果主义的道德理论——比如,义务论理论——也在基础的层面包含不偏不倚的因素,但它们对道德行为者做出的要求远不如后果主义那样极端。因此,尽管有些后果主义者(如,Brink 1989)主张,“后果主义之为真”可以或多或少直接从“道德要是不偏不倚的”这一要求逻辑地得出,但这似乎是一个错误(Scheffler 1992, pp. 105-109)。当然,后果主义者可以要么否定义务论道德理论是真正不偏不倚的(Kagan 1989; Scheffler 1982, 1985),要么主张,基于恰当的理解,任何可行的道德理论提出的要求,和后果主义的要求都是差不多高的 (Brink 1989, Ashford 2000)。然而,这两种策略都面临着各种困难。正如我们将在第4节中看到的,实际上有很强的理由支持至少把有些义务论理论看作是真正不偏不倚的——但尽管如此,该理由并不禁止我们认为这些义务论理论的要求不如后果主义那样严格。
采用这种策略的后果主义者大概还需要表明,人类行为者有能力达到后果主义对我们提出的这类要求(或者论证,我们是否有能力达到并不重要)。正如格里芬所说,我们“自然的,也许是遗传的,偏倚性,它限制了我们的意志。一些行为就是超出了正常人类的动机范围。既然应当蕴涵能够,那么对于处在自然人类动机之外的东西,它们甚至不能参与到道德要求的争论中。规则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它们天生就是要适用于像我们这样的行为者” (Griffin 1990, 129)。尽管卡根(1989)代表后果主义者论证,已有经验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在得到有效信息和生动形象后,人类可以被引导得克服其天生的偏倚性倾向,但格里芬还是认为,这种证据并不充分,进而下结论说,“完全的不偏不倚性超出人类能力” (Griffin 1996, 92)。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快穿之芙蓉帐暖
- (快穿+系统+虐渣+爽文+演戏+大美人+渣女+男主碎片)渣女梨依儿快穿到各个小世界围绕在各个大佬周围。完成任务后就不甩他们了,主搞自己的事业......
- 3.2万字4个月前
- 你是我的兴奋剂
- 0.1万字4个月前
- 快穿:心机美人渣女本色
- 【万人迷+爽文+女强+沙雕+甜文+修罗场】(四)女帝在上:从此君王不早朝穿书成为正统女帝,上位就被逼婚顺其意者傀儡皇帝,逆其心者诛杀百丈太傅......
- 20.5万字4个月前
- 爱心传奇
- 遥远的宇宙中心的爱心仙境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又有什么样的精彩故事!她们都有怎样的过去?她们的爱情又会发生什么阻碍!?一切的一切又将如何?
- 11.5万字4个月前
- 仙路剑心
- 深邃宽阔的无尽森林,是两位天生剑心少年少女的相见的场所。猩红可怕的血月之下,血腥残酷的狂潮之中,他们读懂了彼此的心意,立下山盟海誓!莫小舞:......
- 15.6万字4个月前
- 魔法少年爱你一人
- 一次因为一本书发生的搞笑际遇,将小夕与少年秋沐云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 9.9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