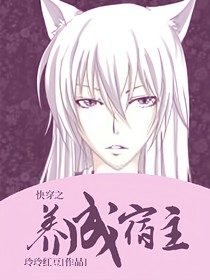思·言·字——评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二) (6-3)
后者有两种含义,其一是迟延,其二是间隔。德里达认为,法文différence遗失了这两种蕴意,所以应以新字“différance”补偿之,它使符号在差异之前和差异之外都不“在场”。或者说,语言是自己产生、创造、运动的,不再受不变的逻各斯支配。“différance”的链条与文字学其他术语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这条链中différance把自己出让给一些非同义的替代物……archiwriting,archi—trace,spacingsupplement,pharm-akon,hymen等。”〔12〕
因此,“différance”是一个在活动中融合诸成分的模糊术语,融合的诸成分是相似的。我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来概括德里达文字学诸术语之间的关系。这些相通的文字学“成员”都综合了语音和文字的要素。在文字学中,意义的传达是通过文字学要素实现的:一个要素按“痕迹”指涉另一个语音或文字的要素。语音与文字的对立,只是différance的效果。「形而上学的错误在于把意义当成文字学之外的在场,它引诱我们通向康德批判的先验幻象」。
2.“播撒”(la dissémination)。德里达是这样描述的:“播撒把自己放在开放的‘différance’的链条中……(播撒)并不意指什么,无法给它下定义……播撒产生了许多不确定的语义效果,它既不追溯某种原始的在场,也不神往将来的在场,它标志着……生衍着多样性。”〔13〕它象征着文字和动作飘忽不定,相互派生,绵延不断。德氏故意制造文字的一词多义,让文字丧失彼此间的界线,使书写和阅读变得复杂而琢磨不定,以致作者和读者都无法完全捕捉文字的跳跃。德氏的文字学书写不受语法规则的束缚,打破文法与字义的界线,使它们融为一体。德氏常把词序打乱,重新组合,就像无规则的游戏,从而在结构上动摇了西方传统的语法学理论。这样,“播撒”的文字学形成一种异样文字,它使自己处于书写与阅读的“零度”,丧失了传统的支撑点。与逻各斯传统比较,文字学不在“书”中,不在“话”中,它不出台,用传统目光见不到它,它隐不可测,黑不见掌。文字的播撒就是写。
德里达很重视弗洛伊德的“话语”——它并不源于语音文字,它来自“手迹”(script)。“手迹”和“道道”并不记录“在场”的话语,它像是梦中的书写痕迹,意在揭示一种反传统的无意识活动——德氏声称,这里接触到了解构的文字学。梦中的书写是难以言传的密码、缄默的痕迹。这种痕迹可与象形文字相提并论。弗洛伊德称:梦是写在舞台上的字,这字是象形的,绘画的,不能还原为说。梦(字)的交往在无意识之间,做梦者发明了奇怪的文法,依这文法的字具有含糊多义性:“恰当的解释只能根据不同的语境”〔14〕。弗洛伊德的“梦”对德里达很有启发:梦中的言语只是梦中的动作(象形文字)要素,思想成为梦过程的图象,绝非词的抽象,时间成为空间,译梦成为译字。
书写的非意识离开现象学。现象学式的书写是狭义的,像我们反复说过的,写出意向中要说的话,意向中的意义不是“痕迹”。德里达用“痕迹”说明已经解构了说与写界线的文字。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星座狗:破局
- 1.1万字1个月前
- 契约的血祭坛(重制版)
- 多世界✓主打西幻和科幻✓架空世界宗教有,魔法有伏笔多作者记性不好角色头像来源网络,侵权删(这个tag真的怎么打啊)
- 1.4万字1个月前
- 终极三国之你是我的
- 此书为终极三国之时空之恋续部!上部说到:五虎将等人即将动身前往全校盟总学院,那么他们在全校盟总学院又会遇到什么呢?
- 1.1万字1个月前
- 初冬白城
- 一:沈初了在兵荒马乱的十八岁遇见了她的“白月光”白骄,还一不小心标记了他…为了负责沈初了被迫长大,一个弱A怎么能担起进击者的重担。第一天:兵......
- 10.9万字1个月前
- 余生里的茶
- 他说,你一辈子都不可能离开我。可她却永远的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他二十岁遇见了一个人,心第一次跳动,却因不懂感情,结局悲惨。十年后,他遇见了她......
- 10.5万字1个月前
- 快穿之养成宿主
- 云雪昭,雪神之子,生性如雪一样淡漠,也如雪一样干净、纯净。本是高高在上的天骄,却因世人的贪欲,众神的冷眼旁观,致此陨落,却不想,还有一线生机......
- 4.4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