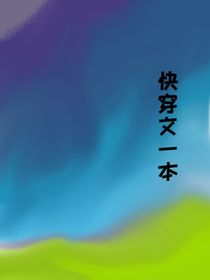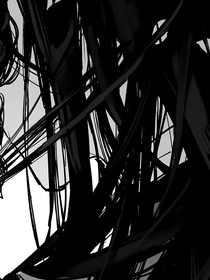哲学(二) (6-4)
如果说,人们承认科学哲学中存在这样一种“法国风格”,那么也应该选择出最能说明这种风格的作者。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风格的最初体现在了孔德的身上。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作者,例如阿贝尔·雷,他给予了这一风格制度上的基础。无疑,我们应该像福柯那样看到卡瓦耶斯或科瓦雷的工作。
我们还可以在这一风格的晚近时期看到弗朗索瓦·达戈涅(François Dagognet)或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的作品。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提到那些不是法国人的作者,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发现了这一历史认识论传统的某些方面,如伊安·哈金、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或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得是法国人才能阐明这种科学哲学中的“法国风格”,甚至我们可以说,种风格似乎在法国国外比在法国更富有生命力。
然而在此,我们将局限于巴什拉、康吉莱姆和福柯的作品,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对科学哲学中的方法问题展开了最大的关注。我们将特别强调康吉莱姆作品,这既是因为其在历史上处于另外两者之间,也如达戈涅所言,康吉莱姆在由他的老师巴什拉和他的弟子福柯所代表的“两极”之间摇摆,在制度和争论(contestation)之间,在“肯定”和“否定”之间,在“理性和尼采主义”之间。在这个意义上,康吉莱姆完美地描绘了法国科学认识论所富有的各种可能性,或者说,各种诱惑力。

哲学和科学
当代哲学对科学及其革命的冷漠令法国科学认识论感到愤慨。根据巴什拉的说法,哲学家们并不关心“科学事实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他们并未做出必要的努力来整合同特别是相对论在内的同时代的科学革命。这些革命产生了一种“新的科学精神”。同样的,巴什拉也对阿尔都塞所说的“科学家们的自发哲学”(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avants)感到失望。当科学家们给出了“哲学上的信仰声明”时,他们总是完整地复述一些并不能反映他们行为地哲学,结果“科学没有它相应的哲学”。
对哲学家而言,他们与科学的距离可以有两种形式。要么是因为他们单纯对科学不感兴趣——在康吉莱姆看来,这无疑可以说明萨特的作品。要么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围绕着科学,阐述一种“清晰、快速、简单的哲学,但却仍旧是哲学家的哲学”。在后一种情况在,问题便是先天(a priori)地说明科学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对实际存在的科学感到任何困惑。
因此,笛卡尔是巴什拉、康吉莱姆还有福柯的一致目标,因为他满足于用“我思”(je pense/cogito)来奠定科学——“在我思中,精神的同一性是如此清晰,以至于这种清晰意识的科学立即成为一种科学的意识,成为了奠定知识哲学的确定性”。
这种态度被巴什拉和康吉莱姆批评为试图“奠基”科学的企图:哲学家“总是试图能一劳永逸地奠定”。哲学试图通过绝对的方式“奠定”科学,以此取消科学的原创性。这种错误的典型乃是埃米尔·梅耶松(Émile Meyerson),而巴什拉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评。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