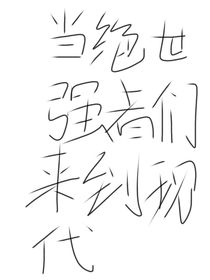哲学(三) (6-4)
康吉莱姆同样还谴责了寻找“先驱”(précurseur)这一广为流传的错误。这种“先驱病毒”将是“没有能力面对科学认识论式批判的最明确的症状”。这种寻找先驱的做法使人无法把握历史上真正的新奇事物。“如果存在着先驱,那么科学史将会失去所有意义。若非如此,科学本身将只在外观上具有历史维度”。这将阻止我们理解一个概念在特定系统或时期之中的含义——当我们把拉马克视作达尔文的“先驱”时,我们将既无法理解达尔文的原创性,也无法理解拉马克的一致性。
这种“先驱”概念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先驱“将是一位身处好几个时代中的思想家,这个思想家既处于自己的时代中,也处在那些被认为是其后继者的时代之中”。这一概念也假设了历史是线性的。它是一种独特的“竞赛”:“一位先驱将是一位思想家、一位研究者,这位先驱曾经跑过了另一个人在新进跑过的一段赛道”。然而,我们绝对无法确定这是同一条赛道。
巴什拉意识到了这一困难,并指出,“需要一种真正的策略来处理这些可能的复现”。然而,当他在科学史中看到“知识的理性联系进步”史或“非理性主义的失败史”时,巴什拉可能并没有完全摆脱与“科学家的历史”相伴生的进步意识形态。对于“复现”这一概念的风险,康吉莱姆可能比巴什拉更为敏感。他承认自己对机械地运用复现理论有所保留,并宣称一种“复现的善用”——“认识论复现的历史方法不应被视作万灵药”。根据康吉莱姆的说法,复现概念无疑与巴什拉所处理的领域,即数学物理学领域和计算合成化学(chimie des synthèses calculées)领域密切相关。
这种复现的历史所产生的第二个困难是,它使任何科学史都是绝对暂时的。巴什拉认识到了这种“毁灭的要素”,并认为其来自于“科学的现代性的短暂的特性”。每一种新的重要发现都会使科学史必须被重写。巴什拉坦率地假设了这种“相对主义”的后果:“科学的每一次成功都会纠正其历史的视角”。
然而,按照他的说法,却也存在着一种“已经过时的历史和由现在仍旧活跃的科学所许可的历史之间的辩证法”:某些理论(例如燃素说)绝对是已经过时了的,因为它们立足于一些“基本错误”,而其他一些理论,例如约瑟夫·布莱克的热质说,“即使它们包含需要重新加工的部分,也是在测定比热的实证实验中出现的”。
康吉莱姆也接受了这样的结果,他所写的反射概念的历史包括了“反射概念沿革史的历史(histoire de l’historique du réflexe)”这一基本要素。而在其他地方,康吉莱姆则欣然承认,他自己关于生机论的工作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现而部分失效,他也许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重新写作。
复现概念带来的第三个困难是“过去”这一词本身的定义问题。这段历史本身似乎是被重构的,而不能被认为是给定的。康吉莱姆指出,“绝对地看,‘一种科学的过去’(passé d'une science)的概念是一个俗常的概念。过去是回溯性质询的各种大杂烩”。在这个意义上,一种科学的过去指的是编年史以外的其他某种东西。科学史的节奏因不同时期的强度或其所研究的领域的丰饶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可执行幻想
- 短篇合集:《幼时小鸟》『连载中』(芙雨篇)关于哥哥超爱我这件事
- 0.1万字1年前
- 当绝世强者们来到现代
- 如果那些封号级别的强者在某天早上有了手机,最后却来了现代,怎么办捏
- 0.7万字1年前
- 镜月关
- 随笔,风无边X历元,双洁,he狱中,501号牢房,躺在一角的风无边道:“历元人?”坐在对角的历元斜眼看他:“你认识我?”风无边:“不认识!”......
- 0.2万字1年前
- 新葫之镜子的背后
- 镜子的里面,会是什么样的呢?
- 5.2万字1年前
- 穿越之我在异世横行无阻
- 重生这种不科学的事件居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想想真是好笑,曾经的暗杀之王,这一世居然是个小王子虽然体质废材,但是有一块儿小封地,倒也生活富足可为......
- 12.8万字1年前
- 有女应龙
- 嗯…怎么说呢,本来想是攒够实力就去完成任务然后去征服星辰大海,但有了实力后就想养老了,觉得累了
- 3.8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