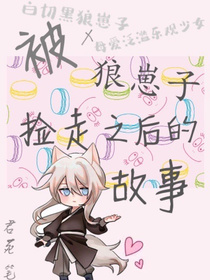起源问题 (4-4)
德勒兹不得不忽视这个符号伪深度:在他的身体和意义二分法中没有它的位置。当然,在这里展示的是对德勒兹进行的拉康式批评的可能性:作为微分结构的能指不正是这样一个实体,严格说来它既不属于身体深度也不属于意义-事件的表而?具体说到莫扎特的《女人心》:哲学家阿尔凡索所信赖的“机械”和自动作用,不就是帕斯卡《思想录》的重大主题即符号机器、符号“惯例”的“自动作用”吗?德勒兹辨别了严格意义上的身体因果性与自相矛盾的“男根”环节,这是能指系列与所指系列的交叉口,是作为伪原因的谬论,也就是内在于意义自身的表面之流的意义的去中心原因。这里他没有考虑到的,是能指系列对于所指系列而言的完全异质的特性,以及微分结构的同步性相对于意义-事件之流历时性的完全异质的特性。也许在这里比较明显的是德鲁兹的局限性,他最后仍然是个现象学家——正是这个局限性最终导致他向“反俄狄浦斯”的理论“退缩”,“退缩”到对符号界的反抗。在这个精确的意义上,人们可以说禁欲主义者、胡塞尔等人不是性反常者,而是精神病患者:正是对正常象征标准的精神病式的排斥才引起了意义与现实之间悖反性的短路(“当你说‘马车’时,一辆马车就从你的嘴边穿过”,等等)。
如果我们要阐明身体深度与符号伪深度之间的关键区别—后者决定了主体的地位,我们就不得不转而提到或许是现代欧洲意识形态最令人讨厌的要点,提到这么一个作者,他把反女权运动的逻辑学推到了无法超越的极点,他便是奥托·魏宁格。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有时不珍惜
- 这本小说主要写的是一个叫莱茵的女孩在自己的竹马眼里是但小怕事还恶毒的人,当莱茵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竹马却又回心转意的事
- 0.2万字12个月前
- 吾帝言君
- 上古之时六界划分严明,创世之神预言‘火凤迎升者,乃六界之主’。三百万年过去了,就在六界都已认为世上没有火凤迎升者时,冥王与花神之女‘花言’降......
- 68.3万字12个月前
- 被狼崽子捡走之后的故事
- 【已完结】作为一个网文太太的苏芄兰没想到自己会穿越到自己的小说里。还成了一笔带过被献祭给反派的炮灰少女。可是自家反派儿子好像还没觉醒黑化因素......
- 7.9万字12个月前
- 魏氏小红娘
- 魏苻不小心掉下井盖,还和一个古里古怪的东西签订了契约,从此成为一名穿越古今中外的红娘。但是,魏苻逐渐在任务中抓狂,我说各位大人物们,你们能不......
- 29.4万字12个月前
- 齐天龙的附身逆袭之路
- 在升龙大赛上,齐天龙燃烧血脉,修为大降,被天龙逐出师门,在仆从的提醒下,他将开启一条新的道路。齐天龙:等着吧,我会变得更加强大,让你后悔你做......
- 0.4万字12个月前
- 灯火阑珊夜未央(晚间合集)
- 甜番,日常向,没什么阴谋诡计(逻辑死),he练笔文一.完成任务式莫得感情事业流女主✘高冷傲娇死要面子师兄(已完结)二.老年人心态温温柔柔穿越......
- 9.1万字1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