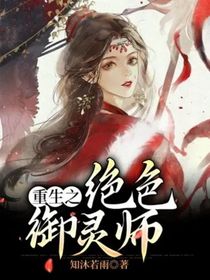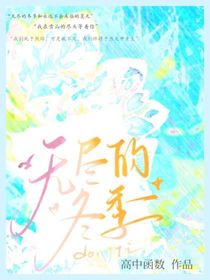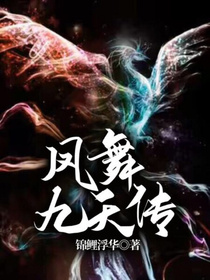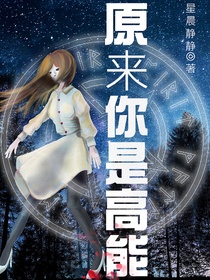德勒兹数法,科学与哲学(二) (5-3)
让我们将此种象征方法运用在人类身上。关于人类境况的思想——也即它的内涵——将思想界定为与其本质相分离的存在。然而,认为一般而言人的本质和存在是相互分离的,这也就是说存在着好几个人(广延)。这是因为“如果,比如说,在自然中存在着二十个人,那么去探寻一般的人类本质的原因就是不充分的。”(斯宾诺莎[8])也即,每个存在都发现其自身的本质是外在的,位于他者之中。这也就是说,从根本上看,人不仅终有一死:他还是“与生俱来”。如果说父母将他们的存在赋予了孩子,以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生存,那么反过来说,孩子是否也在他的父母身上看到了他的理解力、他自身的本质的特有原则呢?既然人的内涵是由存在和本质的分离来界定,那么与之相关(乃至相同一)的广延则可归结为性:“男人和女人分别存在于两个身体之中,每一个都在自己的身体之中拥有着对方的身体”。我们现在看到,正是通过人,作为广延和内涵的同一体的概念才得以出现于世界之中。换言之,性才是作为感觉性质的基础;马尔法蒂援引希波克拉底的话:“人是双重的,如果不是如此,那他就不会拥有感觉。”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感觉指向三个维度:由此,与其说是性的二元性,还不如说是爱的三重特征更值得我们关注。“缺乏自爱,个体生命会变成什么?通过将个体生命在种群之中复制为永恒的、无限的存在,自爱仅靠自身就能将它引向种群的生命。二元论无法涵盖真实的生命。性爱协调了另外的两方,即利己主义和英雄主义。”此外,世界中的生命在三元符号的作用之下被确立起来:通过增加来生成,也即,出生;绵延,作为繁衍生息,正是通过它生成的活动才得以保存;以及毁灭和减少。
那么,最为典型的人的概念应该是什么呢?上帝,本质和存在的统一体,被概念化为圆形:均等与静止,所有焦点间域(interfocal zone)的等价性,以及pregenesthetic的生命。然而,在椭圆形(或毋宁说是始终处于运动中的椭圆体)之中,我们将发现分离,二元性,以及焦点间的性征对立。空间就是从无限的圆形向有限的椭圆形的过渡,而时间则是从中心的统一性向焦点的二元性的过渡:三维由此诞生。我们可能会将此种过渡界定为含混多义的诞生,并将椭圆形界定为一个含混多义的圆形。我们还记得数法的特有对象如何在生命和复杂体的问题之中被发现:“正是在这个时刻,”马尔法蒂说,“当个体即刻将他自己置身于自然的场所中之时,他才得以将自己的生命回归于自然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性爱同时既是自爱又是种群之爱,同时既是“人-生成-内在”又是“人-生成-外在”。另一方面,这让我们回想到支配着生物/普遍生命、以及普遍生命的种群/神性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联的那种对应性。因此,我们将看到马尔法蒂坚持这样一个事实,即genesthetic和pregenesthetic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一方以倒置的方式对另一方做出描述:“之前我是圆形的。现在我扩展为一个蛋的形状。”通过生育,人类追求着他自身的不朽,将时间构成为永恒的动态形象,并在圆形之中探寻着椭圆形的完美形式。准确地说,出神狂喜(ecstasy)无非就是个体将自身提升至种群高度的行为。因为种群只有在圆形的边际之处才能被思索——在堕落之前,亚当是作为人类(humanitas)而存在的。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灿若江湖,不羁星辰
- 早在千百万年前,神妖人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战。在这场战争中,三方都死伤惨重,后来他们决定和平相处,于是签订了《三界和平文书》人生活在地面之......
- 0.8万字9个月前
- 重生之绝色御灵师
- 社畜若南汐在做饭时被自己炸死重生到异世。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发现自己重生成一个婴儿还被追杀。未来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在等着她去探寻……
- 29.5万字9个月前
- 无尽的冬季
- “无尽的冬季,永远不会来临的夏天”“冬九,我会带你走进夏天”“我在雪山的尽头等着你”“我们死于烈焰,可灵魂不灭,我们终将烈火重生”“浑浊腐烂......
- 1.1万字9个月前
- 凤舞九天传
- 《原创!已完结撒花,放心入坑,爱你们呦!》六万年前魔君——擎苍带领妖魔两界讨伐天宫,只为挣得一袭之地!奈何妖魔横行乡里不服管教,天宫数百仙尊......
- 26.9万字9个月前
- 原来你是高能
- 他忘情绝义取了富家女,从此过上奢华的人生,荣华富贵的生活,豪车洋楼金屡楼兰。而方颜曦长叹一声差点晕了过去,恍惚的别了一脚高跟,趴在地上。太难......
- 33.8万字9个月前
- 鱼人小姐没法儿辞职
- “( ̄y▽ ̄)~*,你听说了吗?”路人甲问道“Σ(ŎдŎ|||)ノノ,是最近的大新闻吗?就是女王下岗的事情?”“(͡°͜ʖ͡°)✧是呀,这次......
- 7.2万字9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