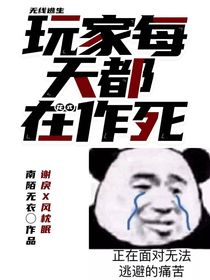知识的终结:学术学科应该有目的和 (5-3)
当然,知识生产不只在象牙塔内进行。正是在启蒙运动时期,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等作家呼吁将哲学“从壁橱和图书馆、中学和大学中搬到俱乐部和集会、茶桌上和咖啡馆中”。“改良”社团在这一时期兴起,这些社团最初专注于改进农业和公共基础设施,但很快扩展到更广泛的艺术和科学领域。其中一些组织仍然是缩小大学与公众之间持续差距的重要机构,如英国皇家学会(原为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
但其他学术之外的努力则专注于和大学断绝联系,而非反之。泰尔奖学金(The Thiel Fellowship)由右翼风险投资家彼得·泰尔(Peter Thiel)创立,为获奖者提供两年期十万美元的资助,条件是从大学辍学或直接不读大学,以“创造新事物而不是在教室里浪费光阴”。对很多人来说,学术组织似乎已是垂死的,想持续改进则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而废除一项制度常常以开启新事物为名义。
一旦我们开始寻找知识的目的,我们就会注意到,关于目的和完成度的问题是很多学术项目的核心。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失败在所难免的知识项目:例如,炼金术、颅相学和占星学现在被公认为人们所遗弃的伪科学(虽然占星术在21世纪文化中重新焕发了生机)。其他学科的消亡也有所报道,尽管可能还为时过早。2008年,克利福德·西斯金(Clifford Siskin)和威廉·华纳(William Warner)就主张是时候“将文化研究写入终结史了”。在一篇题为“分析哲学的终结”(2021年)的博文中,利亚姆·科菲·布莱特(Liam Kofi Bright)认为分析哲学是“衰落中的研究项目”。今年早些时候,彼得·沃特(Peter Woit)在接受艺术与思想研究所采访时,用类似的话描述了弦理论。他称其为“衰落项目”,其实现大一统的目标“一败涂地”。本·施密特(Ben Schmidt)在他的博客中指出,鉴于学术工作岗位数量不断减少,“历史专业有一种终结性衰退的感觉”。所有这些领域虽然生产了很多真知灼见,但是(根据这些作者的说法)它们可能已穷途末路。
我们并非只关注单一领域,而是调查了大学内外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者,让其回答同一个问题:你所在学科的终点是什么?虽然我们鼓励他们思考各种终点,但我们没有对终点下定义,我们也认识到有些人会否认“终结”这个前提本身。我们并不期望达成共识,但我们确实找到了一些共性。这种综合方法揭示了理解“终点”的四种关键方式,这些理解分别为:目的(telos)、终点(terminus)、终止(termination)和启示(apocalypse)。
前两个定义与单一学科或个别学者的工作最直接相关:进展中的知识项目是什么,其完成意味着什么?大多数学者更愿意回答前一个问题,即使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他们要么从未考虑过后一个问题,要么就是认为知识生产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回答一个问题必然意味着回答新的问题。我们认为,即使如此,且某个特定项目永远无法在个人的一生中完成,但有一个明确的终点还是有意义的。第三个含义——终止——指的是许多学科面临的制度压力:研究中心及院系甚至整个学校的倒闭、政治压力和公众敌意。
如果我们连自己想去哪里都说不清楚,又怎么能抵达目的地呢?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星座群星飞
- 5.9万字4周前
- 无限逃生:玩家每天都在花式作死
- 来番茄看看'作者新书无限流,笔名临河三千斯文败类双标非人马甲多多守夜人谢戾大BOSSx一心求死清奇脑回路不服就干孤寡好勇一女的玩家风枕眠❤️......
- 36.5万字4周前
- 乱花飞尽红颜劫
- 一曲年华引,编制各种乱世情。无端动了红鸾星劫,只因一场相遇,他自上泉碧落下黄泉,六百年苦苦追寻,再见,她却已心系他人。她,本因好心相救,却成......
- 19.5万字4周前
- 看见罪恶的眼睛
- 她有一双看见罪恶的眼睛。
- 14.1万字4周前
- 永无归途之天地劫
- 亿万年前,圣神推翻腐朽的天庭,创立新天界,却从此各族分裂!大劫将至,人族一统,各族纷纷利用,阴谋算计,没有可以信赖的!宿命由天不由人,然而众......
- 32.6万字4周前
- 命轮不离,墨晚缘定
- 轮回破灭,圣天分九,冰火双陨,强者何归双神出,天地动,惊世间,天机泄知圣界,忆分别,起源归,创世现天之变,地之幻,双凤现,强者归往事浮现,八......
- 8.0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