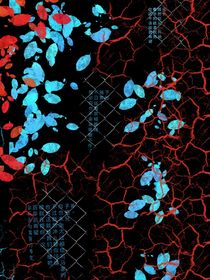言与文:哲学与心理学、哲学与真理(三) (5-4)
让·伊波利特:我觉得巴迪欧在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要处理它们俩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认为哲学是一个时代经验整体化后的中心(我大体上同意这一点)和认为哲学就是同以往所有哲学的对话,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中,哲学完全可能在某一时刻催生出了一系列对新生事物的看法,诞生了一些新颖的论点,而这也并不意味着它和过往哲学家的对话消失了;这种新颖的要素完全可能出现在哲学的诞生之前,我们在那时就已经有了提出哲学问题和存在问题的一些方式;而到了科学得以独立自主发展的时代,一个牛顿和爱因斯坦式的科学家都不复存在的时代,哲学依然需要通过另外的一些方式来提出自身的问题,它同过去的对话也未曾中断过;但是,这种新颖性对于思考一个时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阿兰·巴迪欧:是的,我同意这点。而在我看来,如果哲学在其计划的核心内必须要透过其历史来调解自身,这是由于哲学在其自身历史中发现了一种逐步形成的工具,它通过这种工具就制造出了整体性的范畴。
换言之,我认为正是整体性的范畴奠定了哲学的连续性质;也正是基于各种历史上的哲学在跨越历史这点上的同一性制造出了我们与之对话的可能。
保罗·利科:是这样。我对伊波利特谈到的新颖性深有感触。不过我们也时常对新颖性有所误解,我们不妨看看有多少时代的人们认为他们已经和之前的时代决裂,但实际情况却往往是这种对新颖性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仿古,仿佛不这么做的话我们又会回到这个所谓进步的时代,这个我们确信不属于哲学的时代。
让·伊波利特:您说的有道理。我想要避免的是一种特定的哲学问题概念,这源自于我根本不相信有什么“永恒的哲学”;我相信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和哲学对自身的调解都是有意义的,但我更加相信哲学式的思想;我不相信那些以哲学家为分类标准划分出的、彼此独立的哲学问题史。
乔治·康吉勒姆:我同意巴迪欧把哲学的功能定义为对一个时代经验的整体化。但是这么做并非没有困难。如果我们认为哲学对一个时代经验确实进行了整体化,如果我们也能确认哲学在这一点上从未改变而且这些经验包含了科学、艺术或者技术等等模式的话,那这些模式(至少对于科学和技术而言)就是一个不断否定和淘汰自身过往的运动;诸如希尔伯特的数学、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亦或是毕加索的绘画等等诸多经验模式发生了各种整合,正因为其中很多整合涉及到真实的演进,所以即便哲学本身的整体化功能保持不变,这些整合也不可能从始至终都以相同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不同哲学在试图整合这些要素的程序、风格和成果上并不具备同一性。
因此,从真理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对这些整合进行孰高孰低的比较;哲学和哲学之间有着各种差别,这并不是因为有的哲学比其他哲学更符合真理,而是因为它比其他哲学更加伟大。
蒂娜·德雷福斯:那我们该如何在这一点上对诸哲学进行辨别?如何区分它们是伟大还是狭隘?
乔治·康吉勒姆:严格来说我不觉得有什么固定标准,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符号和迹象来判别一种哲学是伟大还是狭隘;如伊波利特所言,哲学应该走向一种非庸俗含义上的大众化,这是一种科学在其构建自身过程所采用的所有标准的大众化,也是特定时期所有文化活动的大众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哲学在其根本上有着它朴素的一面,我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往往被我们所忽视的、哲学相当通俗的一面:伟大的哲学或许就是在通俗语境中留下了形容词的哲学;换句话说,这些形容词(例如柏拉图式的、笛卡尔式的、康德主义的或者绝对命令的,等等)表明了该哲学不仅有效总结了一个时代的经验,它还成功地将这些认识播散到了非哲学领域,引入到了一系列文化模式当中(同时,这种文化模式往往又必须由另一种哲学来总结),并且在这些意义上对我们称之为日常生活和实存的事物产生了直接影响。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诗韵千古
- 女主竹诗灵,无cp,修真文,微群像。竹诗灵,竹家主家三小姐,上品阴阳双灵根,剑符双修,朋友遍天下。主线:秘境打怪,再交亿个好朋友!唔,也顺便......
- 4.3万字1个月前
- 快穿:宿主是个精分女
- (已签约,无cp,女主独自美丽,正文完结会出cp番外,与正文无关!)她穿梭3000世界只是为了寻一位“故人”……,分成要100块才可以完结,......
- 43.5万字1个月前
- 空间无限快穿
- 快穿各个世界,体验不同的生活,体会完成的快乐。
- 4.6万字4周前
- 愿远离红尘飞遁离俗而不得
- 丕植明洛既然莫不关系就不要责问,既然毫不在乎又何须关注,既然你不爱我又何必在乎我是否还爱着你。误会总会在无意间诞生
- 28.6万字4周前
- 斗龙战士之天才少女
- 0.6万字4周前
- 倾世红颜:惊鸿照影来
- 【绝宠,小虐怡情】片段一:#上官绝尘你什么时候能恢复记忆呢,我都等不及了##夏苏颜什么等不及了,胡说什么呢#上官绝尘现在的你只是夏姬玖的一部......
- 3.2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