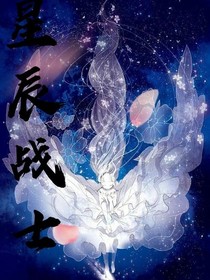言与文:哲学与心理学、哲学与真理(三) (5-3)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以为康吉勒姆想要谈什么如何构建科学主义的真理,例如所谓“科学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这无疑是对他真实想法的一种误读。他的意思恰恰与之相反:科学的真理是存在的,真理的本质以及所有科学项目的存在性都在此萌发。然而,哲学却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我们再也没法像亚里士多德或者笛卡尔那样去重构本体论了。我们可以说自康德以来的很多变化即让哲学思想变得愈发不可或缺,又让哲学回到某些过往立场成为了不可能。
保罗·利科:与此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过去那些哲学是关于什么的,从而也可以理解那些哲学家在探寻着什么。用你们的话来说,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搞清楚这些哲学从何而来又往何处而去,那些地方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片禁足或封闭的领域。
这也是为何哲学史和科学史完全不同。您说过,哲学中不存在谬误,您也可以说哲学中不存在过时或者被淘汰的问题或疑问;而在科学史或者技术史中,则确实存在一些过时或者被摒弃的事物。
在我看来,我们不仅可以从过往那些哲学家身上认识到一些未曾过时的问题,而且还能在不诉诸真理准则的情况下去评判一个哲学体系的广度、力度和分量。就如同您刚才所说的,我们有荒诞透顶的哲学,也有狭隘不堪的哲学;哲学史在编撰上具备相当的选择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心目中最有分量的哲学家,也都会去区分界定这段历史中的主要时刻和次要时刻。
阿兰·巴迪欧:那么您是否会同意,简单来说,哲学是一个时代的经验整体化后的中心?我个人认为,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这么模糊不清,可能是因为哲学的这种整体性的工作是在一种特定的准则或语言框架内运作的,而这种准则和语言往往从科学中引进了其严谨的、甚至是一致性的标准。
我们从这里开始就有了哲学项目这个概念,而且我相信我们可以独立于严格意义上的真理概念之外来认识这类项目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会对该项目明确一系列准则和目的,使它具备其自身的意义和分量;并且,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分析哲学和科学的对立中各种困难以及模糊不清的地方。某种程度上,在过去的不同时期中,或许还包括现在,哲学相信它可以对一个时代普遍经验的整体化可以用一种严谨的、和科学模式或范式相关联的类比语言来描述。
以笛卡尔为例,他提出了“方法论”这么个中介概念;在我看来,我们要保留在这种情况下哲学项目在构成上的原创性,我们既会说明这种哲学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和一些科学项目同处一个时代,同时,也会去解释一些我们看来相当基础的伟大哲学概念。如果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撤除真理的准则,那就需要引入另外的准则来让我们能够评价哲学话语。
保罗·利科:嗯。我认为不能让这些哲学沦为简单的文化量级,或者把它们当成单纯的历史集中点,这样我们不仅会丢掉这些哲学的关键部分,还会让哲学史丧失掉在哲学问题上的连续性和推动这些问题的空间认识;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搞出某种哲学的文化史,而不是哲学性的哲学史。
对哲学史进行编撰不是历史学家的工作,而是哲学家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在如今对这一古老问题的探求必须要在某种交互的空间中进行,这或许就是我们称为“存在的真理”或“实存的真理”的事物。
这种认识有着两个层面:首先,它确保了我们同所有时代的每个哲学家对话的能力,这是哲学史的范畴;然后就是巴迪欧刚才讲的对时代经验的整体化。
通过回应那些伟大哲学家连续的话语来把握我们所处时代的问题,这或许就是哲学的历史性以及恒久性所在。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修仙无尽
- 大女主没有男主是一个修仙的女主是出生一个中等大宗门里突然有一天他们被灭只有女主活来了下来的女主,为了复仇,所以走上了修仙道路,而遇到了一群朋......
- 0.2万字1个月前
- 未来人类的征途
- 在庞大的时间机器里,一个微小的齿轮有可能使未来面目全非
- 0.0万字1个月前
- 某天成为公主:归来
- 诡异的梦境,奇异的国度。明明是因为漫画而来到这个世界,可脑海中不属于自己的一些记忆是怎么回事?
- 4.7万字1个月前
- 军:娇妻是控?
- 一见钟情?还是冤家路窄??缘分只要一来,你想错过或者是当不曾发生。那都不可能,你想忘记就有人让你想起。大叔,你到底想干嘛?我们老大对你有兴趣......
- 55.8万字4周前
- 上神修仙录
- [已完结]失落已久的魔族公主,意外成为上仙云锦的徒弟,她爱慕他、念他,甚至愿意为了他付出生命。云锦:“我喜欢你,生生世世,我只有你一个人,只......
- 12.9万字4周前
- 星辰战士之星辰归来
- 来自遥远宇宙深处万星族的芊滢,本是一个幸福的公主,但是,有一天,突然万星族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灾难,她被不明能量攻击,来到了地球,有神秘人一直在......
- 4.1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