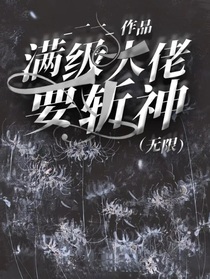科学实在论(五) (3-3)
在一些关于实用主义、安静主义的论述中,把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冲突放在一边的观点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关于第一种,皮尔士([1992]1998,载于《如何使我们的思想变得清晰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例如,最初发表于1878年)认为,对一个命题的内容的理解,应从(其中)其对人类经验的 “实际后果”,如对观察或解决问题的影响来理解。对 James ([1907] 1979)来说,以这些术语衡量的积极效用正是真理的标志(在这里,真理是指在科学探究的理想极限中会被同意的任何东西whatever will be agreed in the ideal limit of scientific inquiry)。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所争论的许多观点–例如,基于可观察性对科学实体的认识论承诺的差异–在这个观点上实际上是不存在问题的(Almeder 2007;Misak 2010)。然而,在对皮尔斯和詹姆斯的传统解读上,它却是一种反实在论的形式,因为两者都认为实用主义意义上的真理穷尽了我们对现实的概念,从而违背了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维度。寂静主义quietism 的概念常常与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回应联系在一起,他坚持认为,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任何明智的说法。这并不是说参与这样的问题不符合自己的口味,而是说,与一个人的兴趣与否完全无关,争议本身涉及的是一个伪问题。Blackburn(2002)认为,关于实在论的争议可能具有这种特征。
最后一个关于实在论辩论的所谓不可解决性的观点,集中在对话者所采取的某些元哲学承诺上。例如,Wylie(1986:287)声称:
现在,双方最复杂的立场都包含了对哲学目的和判断科学哲学理论的适当标准的自圆其说的概念。
关于什么样的推论是合法的,什么样的证据合理地支持信仰,是否真正需要用基本的现实性来解释可观察到的现象,等等,不同的假设从一开始就可能使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之间的一些争论产生问题。范-弗拉森(1989: 170-176, 1994: 182)暗示,无论是实在论还是反实在论(在他的例子中,经验主义)都没有被合理的理性规范所排除;每一种都是由不同的概念来支撑的,即一个人在根据自己的证据形成信念时应该承担多大的认识论风险each is sustained by a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how much epistemic risk one should take in forming beliefs on the basis of one’s evidence。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出现了,即围绕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议是否在原则上可以解决,或者说,最终,这些立场的内部一致和连贯的表述是否应该被视为不可调和但却允许的对科学知识的解释(Chakravartty,2017;Forbes即将出版)。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来自平行宇宙的大(敌)家(人)
- 刀子会很重,但是请记住揪出捣蛋鬼永远是主角团
- 0.7万字1个月前
- 妖精传记
- 妖精们穿越来到了异世界。
- 0.3万字1个月前
- 满级大佬要斩神(无限)
- 文笔致歉诡异预备员✖️恶趣催眠师人们向神明许下愿望,而神明回应他的信徒
- 6.9万字4周前
- 做个狐狸,惑乱你心
- 蓝星因为一次意外附身到了弟弟酋蓝的身体上,如果当时没有附身上去自己便会消失,也是因为弟弟拼尽全力自己才能附身上去,不过只有变回蓝星的时候,才......
- 12.2万字4周前
- 魏氏小红娘
- 魏苻不小心掉下井盖,还和一个古里古怪的东西签订了契约,从此成为一名穿越古今中外的红娘。但是,魏苻逐渐在任务中抓狂,我说各位大人物们,你们能不......
- 29.4万字4周前
- 缘来心系你
- “呼,你过分!”上官媛大口喘着气,本来是生气的话,但因为气虚硬生生地变成了娇嗔。话一出口上官媛都没想到会这样,连忙背过身去,太丢人了!而慕容......
- 17.0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