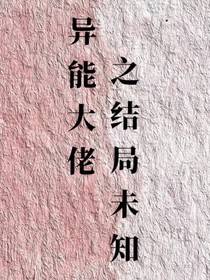【SEP】分歧(二) (5-5)
四方院的院长。假设你和我正站在窗边望着外面的院子。我们认为我们有相似的愿景,我们知道彼此是诚实的。我似乎看到了站在广场中央的院长。(假设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他经常出现在那里。)我相信院长正站在院子里。与此同时,你在那里似乎什么也没看到。你认为没有人,也就没有院长站在广场中央。我们不一致。在我们说话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合理地相信。然后我说院长在院子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情况了。(2007,207–208.)
Feldman认为,在这个案件中,双方都应该显著地和解,尽管很明显,双方都拥有私人证据。虽然双方都可以报告自己的经验,但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对方。双方所拥有的经验证据是私人的。所以,如果还需要调解,我们有理由质疑私人证据的重要性。
第二,“挫败”因为它专注于事物在主体看来是怎样的被否定。Plantinga(2000a)认为,有一种正当性(justification)的感觉,那就是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Plantinga注意到,尽管所有的控制变量,一个重要的不对称仍然存在,即使在同级分歧的情况下。在我相信P而我发现我的同级不相信P的情况下,通常P对我来说仍然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现象学差异——不同的事物对他们来说似乎是真实的。Plantinga认为,既然我们是不可靠的认知生物,那么一定程度的认识风险是不可避免的,鉴于此,我们只能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去相信。所以,在同级分歧的情况下,即使我的同级不相信P,只要P对我来说仍然是真实的,我继续相信P是合理的。任何对分歧的反应都会包含一些认识风险,所以我不妨按照事情在我看来的样子去做。在Henderson et al. 2017中也发现了对坚定观点的类似辩护,强调主体的现象学。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作者的十六个幻想—第一个
- 原名“梦境十六转”,别名“oc设定集”作者小学生文笔,不喜勿喷,谢谢
- 0.2万字1个月前
- 借一颗小颗果
- 又名我白月光的白月光不是我,中药味的Omega钰锦樊生无可恋的爱上了一个奶油蛋糕味的alpha
- 1.3万字1个月前
- 摄政王的蠢萌狐妻
- (每日1~3更,点亮会员、打赏金币加更)一次穿越,让欧阳狐和风逸轩相遇。这是场热与冷的碰撞。传说中的摄政王大人,冷酷无情,何曾想有朝一日,他......
- 69.3万字4周前
- 异能大佬之结局未知1
- 简介正在更新
- 26.2万字4周前
- 甜宠兽世:快把兽夫带回家
- 段夏月因被组织追杀,意外来到了兽世,兽世虽然穷,这资源还是不错的,还别说,这帅哥真多啊。霸道兽王来相争,各路兽王都拜倒在段夏月的石榴裙下还有......
- 9.6万字4周前
- 快穿之闲神游三千
- 人生在世,全靠演技!风灵表示,哦!不,如今化名落十七,看我怎么玩转三千!澪,出发!
- 23.8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