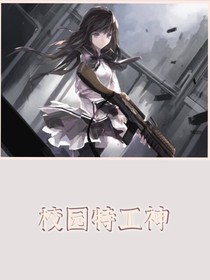弗朗茨·封·巴德尔的神智学:观念论(二) (6-3)
但巴德尔的神智学不是单纯的讲故事。宗教象征和神秘与理性话语相互作用,该话语作为观念论的语言被用来组织象征并思辨其形而上学的内容。神秘并不代表不可逾越的真理,而只是被遮蔽的真理,它们不是绝对的,而只是有条件的深不可测。巴德尔的一个主要问题实际上是他的半概念性。象征与被象征化的东西从来没有明确的区别,而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澄清经验的手段,与辨证思维处于同等地位。神秘主义的数字学说根本不是自由联想的产物,而是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其中数字十是“统一的理智形式”(如果这看起来很任性,那不是因为数字本身的空虚,而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是封闭的,我们只在应该“数”(zahlen, nombrer)的地方“算”(rechnen, comiter) 。虽然他试图根据象征所具体化的理念对其进行解释,但巴德尔保留了象征本身作为哲学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接受了圣事、象征和神秘主义的独立性。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对它们进行思辨,寻找它们的理想意义。
通过他的思辨,自我定义的神秘主义者与天主教教义建立了一种悖论性的关系。在巴德尔对一种老生常谈的辩证美学的改编中,教义对应于宗教中的被给定的古典主义,而思辨性的神秘主义则对应于自由演化新形式的浪漫主义天才。因此,神秘主义并不反对宗教权威。它的功能类似于诗歌创作和有机自然的“亲切性”,并从同样的神圣灵感中活动,这两者都不矛盾,而是使之前的东西充满活力。就像有机体有它的原型,它的成长与之相适应,神秘主义在教义中也有它的原始图像。就像活生生的自然界一样,神秘主义的天才只是把已经存在但在原始形式中没有发展起来的东西更充分地表达出来。教义的概念实际上是有机体的概念,它不是通过增加新的部分而成长,而是通过比例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整体的加强。进化发生在各个部分,而宗教机构通过允许个人神秘主义和科学的定义自由来获得其统一性和活力,以便将教义内化并阐明整体规律的所有潜在变化。因此,当他阐释波墨的形而上学时,巴德尔是在发展天主教的思想,而不是提出替代教义,就像他曾经提出要创建一个新的教会一样。思辨甚至是一种神圣的戒律,因为启示,就像所有其他从上帝那里来的人一样,既是一种礼物,也是一种责任,一种探究和加强的责任,因为“信仰只产生于理智的自由活动”。当他肩负着“思辨的十字架”时,巴德尔发现基要的奥秘是“深不可测的”,并把这种发现本身当作“深不可测的东西”。当神秘性被如此承认时,信仰就允许理智真正自由,因为它为思辨提供了一个肯定的基础。
宗教象征能够揭示“一种视角,在这种视角中,异质的实在可以被衔接在一起,甚至被整合成一个体系”,它 “允许人类发现世界中的某种统一性,同时意识到他自己的命运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宗教象征主义的多面性和它的存在价值对巴德尔来说并不亚于对现代深度心理学或宗教比较研究的影响——但他对他所采用或重新创造的体系的态度却明显地不现代。象征主义很少是“审美的”,而类比也从来不是游戏性的。哲学家并不把他的形而上学的象征性结构看作是纯粹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当他得出神圣自然的概念(作为“这个”自然 的原初),或精神-身体的类比概念(作为原初和未来的人类形式)时,这些都成为解释自然和人的现实状况的基础。拟人化地从自然界的模式(作为有机体的上帝)中派生出来,神智学的神性建构为三位一体的自然和神化的人提供了模型,从亚当中解释人类,从有机体中解释无机物,只是从上帝中解释万物的程序的特殊应用。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奇眠者
- 写步临笺发现学校里的人一个一个的都失踪了,而他们的父母都没有他们的记忆,直到轮到自己也消失了,她发现自己被困在梦境里。无法走出来,有一天遇到......
- 1.3万字4周前
- 阿妧杂货铺
- 长评+cos
- 0.1万字4周前
- 校园特工神
- 重生前她为特工重生后她复活归来他遇见了她,前世今生,定将厮守。【女主云笺,男主斯泽,1v1绝对身心健康】
- 3.7万字4周前
- 辞渊之光
- “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已完结)“要做只属于你的月亮”“你喜欢我,就不要打我好不好?”“那你不听话怎么办”“口头教育一下就行……”“口头教......
- 8.0万字4周前
- 三世轮回为君倾
- 第一世,他是独断专行的星空之下最强者她是凡人散修养大的少年妖神,一场意外的相遇是生生世世纠缠不休的开端,一个误会成了他的催命符,囚禁、逃婚、......
- 31.5万字4周前
- 仙域世界
- 陆思瑶是一个极限运动爱好者,蹦极,低空跳伞,跳伞,徒手攀岩,高空跑酷和泅渡长江,一次机缘巧合或者说是祸不单行在太平洋百慕大附近进行跳伞并根据......
- 31.1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