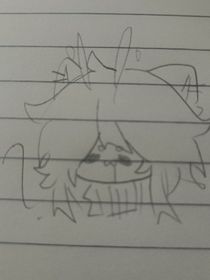弗朗茨·封·巴德尔的神智学:观念论(二) (6-1)
巴德尔把神智学思想描述为对“中心直观”的参与,描述为“光辉的感知”、“魔法”和“狂喜”。不管用什么名字,所声称的洞察的来源就是康德所说的“理智直观”,即产生其自身对象的“神圣思维”。根据定义,这种假想的神奇能力的本体性对象是不可认识的,人类的知识被束缚在感性直观上。它们的作用是作为理想或“边界概念”,在思辨理性中只是形式上的,没有内容。但康德所提供的——作为实践理性公设的“目的王国”——对巴德尔来说,不足以取代被夺走的东西:理想的客观知识。然而,他觉得有必要考虑康德所说的,以及人们正在说的他所说的。神智学家的反应是把知识的缺陷归咎于堕落。正如他在混乱的《Ueber Kants Deduktion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und die absolute Blindheit der letzteren》一书中解释说,理性不是原初盲目的,认识论必须由基督教的“唤醒失落的视见或逻各斯”的教义来补充。当他进行合并时,巴德尔将本体与 现象之间的关键区别转化为天堂与尘世之间的神秘区别,然后利用他的结论,即神圣-本体是不可知的,完全是由于堕落的人类能力无法领会它或“界定其概念”。然后,他可能会说,在信仰的活动中要认识到本体。但这将使他与雅各比“分离”,而他想要知识和信仰。然而,在他所针对的理论中,知识只是可能的感觉经验。除了说感性也是堕落的,并肯定一种天赋的超越感性直观的能力——一种“内在的”但又是客观的 “感性”——甚至可以在“这个”生命中发展起来,还有什么呢?巴德尔同意知识是经验的要求,他回答说,当哲学家说经验总是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时,他们对经验的定义过于狭隘,而且——与他的同道灵物学(pneumatologist)荣格·斯蒂林(Jung-Stilling)一样——他把时间和空间的批判理论作为通向神秘主义的桥梁,作为吸收对传统神秘主义理论的理性攻击的手段。空间和时间是堕落的,如果理性不知道它可以有一个理念,那是因为理性在这个尘世的感官实存中“不在家”。但正如每一个自然哲学家所知道的,还有另一种体验,与“磁性狂喜”同义,而超验的知识正是适用于这种体验。受试者报告了时间和空间的暂停,但仍有令人难忘的经验,这一切都可以在荣格·斯蒂林的超感视觉故事或贾斯蒂纽斯·克纳(Justinius Kerner)著名的梦游状态研究中读到。正如巴德尔在一系列基于这些经验和他自己的实验的文章中所论述的那样,梦游状态是对前世和未来永恒的感官实存的短暂一瞥,在那里我们自然会“更在家”。尽管对日常来说是奇迹,但它只是在生命对无机物来说是奇迹的程度上如此。理性是“超物质”或超时空的,但它不是“超自然的”或超感性的。梦游状态代表了一种超越自然的直观——也许就像做梦的人觉得自己被穿上的精神-身体一样,但无论如何,这种直观最终是可以被认识的——因此,有理由认为灵视经验可以产生哲学中所谓的知识。为了使不可思的事情变得更加熟悉,巴德尔提议用“魔幻的”和实在的1来代替观念和实在之间的区别。我们称之为观念的东西是实在的,但对我们来说是魔幻的,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感知它的感官。当这些感官恢复时,我们将知道我们的魔幻世界是实在的,而那曾经是实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将显示为魔幻的。 现在,如果看起来仍然不可能想象一门超验的科学,那么这只是由于哲学上的二元论将精神和自然分开,对哲学家来说,这与观念和实在之间的错误分离是一样的,而这又与本体和现象之间的分离以及只能相信的东西和可以知道的东西的分离是一样的。对于超物质的科学理论,他转向了前康德的波墨的形而上学,波墨在理智上取得了胜利,因此他没有分离,而是重新认识到每个观念都有其相应的实在,像上帝一样的灵魂有其身体,每个精神都有其自然,所有可以相信的东西也可以被知道。在恩典的模式上,巴德尔的基督教教导感官和理智与意志的重生,以及在“此”生中逐步澄清现在只被魔幻地知道的最高实在。因为不存在一个思辨理性和一个实践理性,而只有一个理性,而且它不是固有的上帝的盲目。它可以以康德片面地、然后半心半意地允许其道德计划的同样的确定性来实现其认识目标,它不仅可以继承一个目的王国,而且可以继承一个绝对知识的王国。针对他所认为的人类理性被谴责为无休止地努力实现理想的知识的卑微观点,巴德尔为苏醒的精神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智慧的神智学前景:本体性的如其所是的存在只是宗教所说的“昔在,今在,永在”。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屠羊游戏
- 一群受够了校园高压生活的学生,一边抱怨一边幻想着自己成为无限流小说的主角。以夏蔓为首的一群人,竟真的在这一声声哀声载道中卷入了一场游戏。他们......
- 2.2万字1个月前
- 穿越成了大魔王
- 天界女战神在与魔渊邪魔一战后,魂魄消散了一万年,连带着消失了一节跟她征战多年的玉骨笛…年时莫名其妙被人召唤到了魔界,非说她是什么魔界的主君!......
- 10.0万字4周前
- 牛奶的小号废品站
- 画渣,但是小号
- 0.3万字4周前
- 驯服(abo)
- 小王子得到了一只独属于他的白狮,他想要驯服他的桀骜,但狮子天生就是自由的,又有谁能锢住他,一切顺从只是狮子营造的假象……除非是狮子自愿带上⛓......
- 1.1万字4周前
- Bless
- 一场游戏,一场盛宴,在这个世界里祈福吧,bless!
- 7.9万字4周前
- 平行于否
- 一部科幻小说,场景设定与一个外太空的神秘星球,那里的世界叫神域,子民都是仙,记录了女主从小到大的生活。特别记住:神域和地球相连
- 3.8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