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дәҢеҚҒдә”з«
е”°дёҖеЈ°е“ҚпјҢй•ҝеү‘еӣһйһҳпјҢеқ зҝҺзҡ„и§Ҷзәҝд»ҺжҹіеҜ»йёўж¶ҲеӨұзҡ„ж–№еҗ‘еӣһеҲ°жҳҸиҝ·дёҚйҶ’зҡ„жІҲжһ«иә«дёҠпјҢжңҖеҗҺе®ҡж јеңЁзңјеүҚз ҙиҙҘиҚ’иҠңзҡ„еәҹеўҹд№Ӣй—ҙгҖӮ
жҹіеҜ»йёўи·‘еҫ—еӨӘеҝ«пјҢдёҚ然他д№ҹи®ёдјҡи·ҹд»–и®ІпјҢеҮәеҸ‘жқҘжІҗе·һзҡ„еүҚдёҖжҷҡпјҢеҖҡеҪұеҚ«жӣҫжӢҝдәҶдёҖжң¬еҺҡеҺҡзҡ„з°ҝеӯҗжқҘеӣһд»–гҖӮ
вҖңе°‘зҲ·пјҢдҪ и®°еҫ—дёҚй”ҷгҖӮжІҗе·һеӣһйҫҷжқ‘ж—©еңЁдәҢеҚҒе№ҙеүҚдҫҝжҜҒдәҺдёҖеңәз–«з—…пјҢе…Ёжқ‘дёҠдёӢж— дәәе№ёе…ҚпјҢжқ‘ж°‘е°ёдҪ“е Ҷз§ҜеҰӮеұұпјҢзҒ«зғ§дёүж—ҘжңӘеҒңпјҢйӘЁзҒ°ж®ӢиәҜзҡҶжҠӣе…Ҙй”ҰйіһжІідёӯгҖӮжӯӨеҗҺеҶҚж— дәәзғҹпјҢж—©жҲҗеәҹеўҹгҖӮвҖқ
вҖңзҹҘйҒ“дәҶгҖӮвҖқ
вҖңиҝҳжҳҜиҰҒеҺ»пјҹвҖқ
вҖңж—ўеә”дәҶйӮЈеҰ–жҖӘпјҢиҮӘ然иҰҒеҺ»гҖӮвҖқ
вҖңдёҮдәӢе°ҸеҝғгҖӮвҖқ
вҖңеҘҪгҖӮвҖқ
жӯӨеҲ»пјҢйЈҺйӣӘи¶ҠеҸ‘иӮҶиҷҗпјҢеқ зҝҺиҮӘиЁҖиҮӘиҜӯйҒ“пјҡвҖңи¶ёйұјвҖҰвҖҰжңүж„ҸжҖқгҖӮвҖқ
иҜҙзҪўпјҢд»–е°ҶжІҲжһ«жҠұеҲ°еӢүејәеҸҜйҒҝйЈҺйӣӘзҡ„ең°ж–№д№ӢеҗҺпјҢдҫҝеӨ§жӯҘеҫҖй”ҰйіһжІіиҖҢеҺ»гҖӮ
йӮЈдёӘеҺЁеӯҗдёҺе№іеёёеӨ§дёәдёҚеҗҢпјҢиҖҢдё”жҖ»и®©д»–и§үеҫ—зңјзҶҹпјҢд»–д№ҹжғізңӢзңӢд»–зҡ„жҲҸе‘ўгҖӮ
вҖҰвҖҰ
дёүдёӨйӣӘиҠұжӮ жӮ иҖҢдёӢзҡ„еҶ¬еӨ©пјҢйҖӮеҗҲжё©й…’иөҸжў…пјҢиҜҙе°ҪеӨ©дёӢжөӘжј«дәӢпјҢиҖҢеӨ©дҪҺдә‘жҡ—е‘јж°”жҲҗеҶ°пјҢжј«еӨ©д№ұйӣӘдёӯеҸӘеү©е°Ҷдәәжҙ»еҹӢзҡ„зӢӮжөӘж—¶пјҢжңҖеҢ№й…Қзҡ„дәӢпјҢе”ҜжңүеҸ–ж•ҢжҖ§е‘ҪгҖӮ
жҹіеҜ»йёўдёҚиҝҮеңЁй”ҰйіһжІіз•”з«ҷз«ӢзүҮеҲ»пјҢе·ІжҳҜж»ЎеӨҙзҡ„йӣӘж°ҙпјҢиҝһиЎЈжңҚйғҪдёҚиғҪе№ёе…ҚпјҢеҶҚдёҚеҠЁдёҖеҠЁпјҢж•ҙдёӘдәәжҖ•йғҪиҰҒжҲҗдёҖеә§зҖ‘еёғдәҶгҖӮ
иҝҷз§ҚеӨ©ж°”пјҢе…үеҠЁеҳҙзҡ®еӯҗеҸҜдёҚиЎҢгҖӮ
дҪҶеҒҸеҒҸе°ұжңүдёӨдёӘ家дјҷпјҢдёҖдёӘдёҚдёӢжІіпјҢдёҖдёӘдёҚдёҠеІёпјҢеҗөжһ¶гҖӮ
вҖңжҲ‘еҗ¬еҲ°дҪ зҡ„иӣҮеҚ°пјҢдҪ жғіжқҖжҲ‘пјҒвҖқз»“еҶ°зҡ„жІійқўдёҠпјҢйӮЈе°ҸиҖҢеңҶиғ–зҡ„и¶ёйұјз«ҷеңЁдёҖйҒ“йҡҗйҡҗзҡ„иЈӮзјқеүҚпјҢд»°жңӣзқҖжІіеІёдёҠзҡ„жҹіеҜ»йёўпјҢе®іжҖ•жҳҜеҫҲе®іжҖ•зҡ„пјҢдҪҶеӨҡе°‘иҝҳжңүйӮЈд№ҲдёҖзӮ№еһӮжӯ»жҢЈжүҺзҡ„еӢҮж°”гҖӮ
вҖңж—ўзҹҘжҲ‘жқҘеҺҶпјҢиҝҳдёҚиҖҒиҖҒе®һе®һдёҠеІёжқҘи®Өй”ҷеҸ—жӯ»пјҒвҖқжҹіеҜ»йёўжҖ’йҒ“пјҢи§ҶзәҝеҸҲеҒ·еҒ·еҫҖи„ҡдёӢзһҹдәҶзһҹпјҢе…¶й—ҙд»–жғіиҝҮеҘҪеҮ ж¬Ўи·іеҲ°жІійқўдёҠпјҢдҪҶвҖҰвҖҰдёҮдёҖеҶ°иЈӮдәҶпјҢдёҚе°ұжҺүж°ҙйҮҢдәҶеҗ—пјҢиҝҷдёӘеӨ©ж°”иҗҪдёӢеҺ»пјҢе…ҲеҶ»жӯ»дәҶпјҢе°ұз®—дјҡжёёжііеҸҲжҖҺж ·гҖӮ
еҘҪеңЁйӮЈи¶ёйұјжҡӮж—¶жІЎжңүзңӢз©ҝд»–зҡ„зҠ№иұ«пјҢе“Ҷе“Ҷе—Ұе—Ұең°еӣһд»–пјҡвҖңдёәдҪ•иҰҒжҲ‘еҸ—жӯ»пјҹпјҒвҖқ
жӣҙеҸҜжҒЁдәҶпјҢжӯ»еҲ°дёҙеӨҙиҝҳдёҚзҹҘиҮӘе·ұзҠҜдәҶжҖҺж ·зҪӘиҝҮгҖӮ
вҖңеҰ–жңҜжғ‘дәәпјҢдјӨеҸҠж— иҫңпјҢдҪ дёҚиҜҘжӯ»и°ҒиҜҘжӯ»пјҒвҖқжҹіеҜ»йёўиҫ№йӘӮиҫ№жҖқзҙўе“Әз§ҚжҜ’жӣҙеҗҲйҖӮпјҢдҪҶеҘҪеғҸзӣ®еүҚеёҰжқҘзҡ„иҮҙе‘ҪжҜ’йғҪеҸӘйҖӮеҗҲиҝ‘и·қзҰ»дҪҝз”ЁпјҢиҷҪ然еҰӮжһңеҘ№ж„ҝж„ҸпјҢиғҪе°Ҷж•ҙжқЎй”ҰйіһжІіеҸҳжҲҗжҜ’ж¶ІпјҢдҪҶжІідёӯе…¶д»–з”ҹзҒөеҸҲдҪ•е…¶ж— иҫңпјҢи·ҜиҝҮзҡ„йӣҖйёҹе°Ҹе…ҪиӢҘйҘ®дәҶжІіж°ҙпјҢд№ҹж— з”ҹжңәпјҢдёӢиҝҷиҲ¬жүӢж®өе®һеңЁдёҚеҰҘпјҢдҪ•еҶөиӢҘиў«зҷҫиҲёеұұйӮЈдҪҚж•…дәәзҹҘйҒ“пјҢиҮӘе·ұдёҚд№ҹжҳҜдёҖжқЎвҖңдјӨеҸҠж— иҫңвҖқзҡ„еӨ§зҪӘвҖҰвҖҰеҘҪж°”пјҢе Ӯе ӮжҹіеҜ»йёўеұ…然被дёҖжқЎжІійҡҫдҪҸдәҶгҖӮ
вҖңжҲ‘е“ӘйҮҢдјӨеҸҠж— иҫңпјҒвҖқи¶ёйұјдёҚжңҚпјҢвҖңжҲ‘дёҚдҪҶжІЎжңүдјӨдәәпјҢиҝҳеё®дәәпјҒвҖқ
вҖңдҪ иҝҷжқЎйұјзҡ„и„ёзҡ®е’ӢжҜ”дҪ зҡ„иӮҡзҡ®иҝҳеҺҡпјҹвҖқжҹіеҜ»йёўжҖ’йҒ“пјҢвҖңжІҲжһ«дёҚе°ұиў«дҪ зҘёе®іеҫ—е‘ҪдёҚд№…зҹЈпјҒжҲ‘дёҚз”Ёи„‘еӯҗжғійғҪзҹҘйҒ“пјҢдҪ иҝҷеҰ–еӯҪе®ҡжҳҜиҮӘй”ҰйіһжІідёӯиҖҢз”ҹпјҢй”ҰйіһжІіж°ҙдёҚжһҜпјҢдҪ ж–№жңүе‘ҪеңЁпјҢжүҖд»ҘдҪ еҰ–иЁҖиҝ·жғ‘жІҲжһ«пјҢеҲ©з”ЁеҘ№жһ«з”ҹзҡ„иә«д»Ҫеё®дҪ дҝқдҪҸжІіж°ҙдҝқдҪҸжҖ§е‘ҪпјҒвҖқ
вҖңдҪ жғ…жҲ‘ж„ҝпјҢе“ӘйҮҢз®—еҫ—дёҠзҘёе®іпјҒвҖқи¶ёйұјдҫқ然дёҚжңҚпјҢз”ҡиҮіиҝҳи·әдәҶи·әи„ҡпјҢвҖңйӮЈи ўдё«еӨҙжӣҝжҲ‘дҝқдҪҸжІіж°ҙжҳҜжІЎй”ҷпјҢдҪҶжҲ‘д№ҹжІЎжңүзҷҪзҷҪеҸ—еҘ№иҝҷд»ҪжҒ©жғ пјҢиҰҒвҖҳеӨҚжҙ»вҖҷж•ҙдёӘеӣһйҫҷжқ‘пјҢе°Өе…¶иҰҒиҝҳз»ҷеҘ№дёҖж•ҙдёӘжІҲ家пјҢдҪ д»ҘдёәжҲ‘е°ұдёҚжҚҹиҖ—иә«еӯҗеҗ—пјҹдәҢеҚҒе№ҙе“ӘпјҒжҲ‘и·ҹеҘ№еҗ„еҸ–жүҖйңҖпјҢе…¬е№ідәӨжҳ“пјҢзәө然дҪ жҳҜзҷҫиҲёеұұйӮЈдёӘдәәдёҚеҸҜиҝ‘зҡ„еӨңиҷәпјҢеҰӮжӯӨејәиҜҚеӨәзҗҶпјҢд№ҹжҳҜеҸҜ笑пјҒвҖқ
иҝҷдёҖз•ӘеӨ§дёҚ敬еҠ дёҚжҖ•жӯ»зҡ„еҸҚй©іпјҢеҗ¬еҫ—жҹіеҜ»йёўжҖ’зҒ«дёҠеӨҙпјҢиҝһи„ёйғҪж°”еҫ—еҝ«и·ҹзңүжҜӣдёҖж ·зҷҪдәҶгҖӮ
вҖңеҗ„еҸ–жүҖйңҖе…¬е№ідәӨжҳ“пјҹвҖқжҹіеҜ»йёўд№ҹи·әи„ҡпјҢвҖңеҘ№жӢјжӯ»дҝқдҪҸзҡ„жҳҜдҪ зҡ„жҖ§е‘ҪпјҢдҪ з»ҷеҘ№зҡ„жҳҜд»Җд№ҲпјҹдёҚиҝҮжҳҜз»Ҳ究иҰҒз ҙзҒӯзҡ„еҒҮеёҢжңӣпјҒдҪ з«ҹиғҪеҺҡйўңж— иҖ»ең°е°ҶдёӨиҖ…зӣёжҸҗ并и®әпјҒвҖқ
вҖңеҒҮеёҢжңӣеҘҪиҝҮжІЎеёҢжңӣгҖӮвҖқи¶ёйұјжҖ•жҳҜиұҒеҮәеҺ»дәҶпјҢвҖңдҪ дёҚжҳҜеҘ№пјҢз„үзҹҘеҘ№жІЎжңүд№җеңЁе…¶дёӯпјҒиҝҷдәӣе№ҙиӢҘйқһжңүжҲ‘пјҢеҘ№ж—©е°ұжһҜжӯ»дәҶгҖӮвҖқ
еҒҮеёҢжңӣвҖҰвҖҰжҳҜзҡ„пјҢй•ңиҠұж°ҙжңҲпјҢжө·еёӮиңғжҘјпјҢйғҪжҳҜиҝ‘еңЁзңјеүҚеҸҲж°ёдёҚеҸҜеҫ—зҡ„еҒҮеёҢжңӣпјҢеҒҮиҷҪжҳҜеҒҮпјҢдҪҶдәәй—ҙз№ҒеҚҺйҳ–家зҫҺж»Ўзҡ„е№ёзҰҸеҒҮиұЎжҖ»иғҪеӢҫдҪҸз»қжңӣзҡ„зҒөйӯӮпјҢеҘ№вҖңд№җеңЁе…¶дёӯвҖқпјҢдёҚиҝҮжҳҜеӣ дёәеҘ№иҝҳд»ҺжңӘйўҶз•ҘиҝҮвҖңд»Ҙдёәеҫ—еҲ°дёҖеҲҮпјҢеҚҙзңЁзңјзҒ°йЈһзғҹзҒӯгҖӮвҖқзҡ„з ҙзҒӯгҖӮ
жҹіеҜ»йёўжІЎжңүиҜҙиҜқпјҢзүҷйҪҝеҚҙе’Ҝе’ҜдҪңе“ҚпјҢеҶ·еҖ’дёҚи§үеҫ—дәҶпјҢе°ұжҳҜдёҚж–ӯеҚҮзә§зҡ„ж„ӨжҖ’пјҢз»ҲдәҺеҶІз ҙдәҶжһҒйҷҗгҖӮ
еҜ’еҶ°еңЁеүҚеҸҲеҰӮдҪ•пјҢеӨ©еҜ’дҪ“ејұеҸҲеҰӮдҪ•пјҢд»–иҰҒжқҖзҡ„еҰ–жҖӘпјҢжҖҺд№ҲйғҪдёҚиғҪжҙ»пјҒ
д»–зәөиә«дёҖи·ғпјҢиҗҪеҲ°жІійқўдёҠзҡ„жңҖеҗҺдёҖдёӘеҝөеӨҙжҳҜд»ҠеӨ©е’ҢжҳЁеӨ©йғҪжІЎжқҘеҫ—еҸҠеҗғйҘӯпјҢдҪ“йҮҚиҜҙдёҚе®ҡдјҡиҪ»дёҚе°‘пјҢйӮЈд№ҲвҖҰвҖҰжІійқўд№ҹи®ёдёҚдјҡиЈӮпјҢиҮіе°‘еңЁд»–е№ІжҺүйӮЈдёӘеҰ–жҖӘд№ӢеүҚдёҚиҰҒиЈӮпјҢдёҚиҰҒиЈӮпјҒ
и§Ғд»–иұҒеҮәе‘Ҫең°и·ідёӢжқҘпјҢи¶ёйұјж…ҢдәҶжүӢи„ҡпјҢйҖғжҳҜйҖғдёҚиҝҮдәҶпјҢи…ҝеӨӘзҹӯпјҢиғҪжҡӮйҒҝеҲ°еҶ°йқўдёӢзҡ„иЈӮжҙһеҸҲиў«иҝҷеңәиҜҘжӯ»зҡ„йЈҺйӣӘе°ҒдҪҸдәҶпјҢйғҪиҜҙзҷҫиҲёеұұзҡ„жҹіеҜ»йёўжқҖеҰ–дёҚзңЁзңјпјҢиҷҪ然е®ғеҲ°жӯӨеҲ»дҫқ然и®Өе®ҡиҮӘе·ұзҪӘдёҚиҮіжӯ»пјҢдҪҶж—ўжғ№жқҘдәҶиҝҷдёӘйӯ”еӨҙпјҢжЁӘз«–йғҪиҰҒдәӨеҮәдёҖжқЎе‘ҪпјҢиҰҒдёҚвҖҰвҖҰеҗҢеҪ’дәҺе°Ҫеҗ§пјҢе®ғж·ұеҗёдәҶдёҖеҸЈж°”пјҢиә«дҪ“жӣҙеҠ йј“иғҖиө·жқҘгҖӮ
иҷҪ然ж„ӨжҖ’пјҢдҪҶд»–дҫқ然жӢҝеҮәдәҶеҪ“еҲқдёүдёӨдёӢеҲ¶жңҚжҪӢж»ҹзҡ„жң¬дәӢпјҢеғҸдёҖеҸӘжІЎжңүйҮҚйҮҸзҡ„е…”еӯҗеңЁеҶ°йқўдёҠиҪ»жҚ·ең°и·іи·ғпјҢзӣҙеҘ”жІідёӯй—ҙзҡ„зӣ®ж ҮиҖҢеҺ»гҖӮ
з®—е®ғиҜҶзӣёеҗ§пјҢд№ҹдёҚи·‘дәҶпјҢйӮЈе°ұеҘҪеҘҪеҫ…еңЁеҺҹең°еҸ—жӯ»еҗ§пјҢдёҚиҝҮдёҙжӯ»еүҚиҝҳжҠҠиҮӘе·ұеј„еҫ—еғҸдёӘеҝ«иҰҒж¶Ёз ҙзҡ„зҗғпјҢжҳҜиў«йӮЈеҸЈжҖЁж°”жҶӢзҡ„еҗ§пјҢе‘өе‘өпјҢзңҹжҳҜдёӘдё‘йҷӢзҡ„еҰ–жҖӘгҖӮ
зңји§Ғи¶ёйұје°ұеңЁдёҖдёҲејҖеӨ–зҡ„ең°ж–№пјҢе°ұеңЁд»–жңҖеҗҺдёҖи·ғзҡ„еҗҢж—¶пјҢи¶ёйұјеұ…然д№ҹй«ҳй«ҳи·ғиө·пјҢеҮҶзЎ®иҜҙжҳҜеј№иө·жқҘзҡ„пјҢдё”е…Ёиә«зӘҒ然被дёҖиӮЎиҮӘе®ғеҳҙйҮҢеҗҗеҮәзҡ„й»‘ж°”еҢ…иЈ№иө·жқҘпјҢеҸӘи§ҒдёҖеҜ№еҸҳеҫ—зәўеҪӨеҪӨзҡ„е°ҸзңјзқӣеңЁй»‘ж°”йҮҢй—ӘеҮәжҖЁжҜ’дё”еӯӨжіЁдёҖжҺ·зҡ„е…үпјҢ然еҗҺдҫҝж•ҙдёӘд»ҺеҚҠз©әдёӯзӢ зӢ иҗҪеҗ‘ең°йқўгҖӮ
еҸӘеҗ¬вҖңе’”еҡ“е’”еҡ“вҖқеҮ еЈ°и„Ҷе“ҚпјҢеҠЁйқҷеӨӘеӨ§пјҢдё–з•Ңд»ҝдҪӣиЈӮдәҶгҖӮ
жҹіеҜ»йёўиҗҪең°пјҢи„ҡдёӢдёҖз©әвҖҰвҖҰ
зіҹдәҶпјҢиҗҪж°ҙгҖӮ
жҹіеҜ»йёўдёӢж„ҸиҜҶең°еҗёж°”пјҢеҚҙеҸ‘и§үеҗёиҝӣжқҘзҡ„дёҚжҳҜж°ҙпјҢиҖҢжҳҜвҖҰвҖҰзҒ°зғ¬гҖӮ
зӯүзӯүпјҢйӮЈдёӘжӯ»иғ–йұјдёҚжҳҜи·іиө·жқҘжҠҠжІійқўзҡ„еҶ°йғҪз ёеһ®дәҶеҗ—пјҢйӮЈзҒ°зғ¬жҳҜд»Җд№Ҳпјҹ
д»–з”ЁеҠӣжҷғдәҶжҷғи„‘иўӢпјҢжүҚеҸ‘зҺ°иҮӘе·ұиәәеңЁдёҖзүҮзЎ¬ең°дёҠпјҢд№ҹдёҚзҹҘиҝҷеқ—ең°зјәдәҶеӨҡд№…зҡ„ж°ҙпјҢйҫҹиЈӮеҫ—еҝ«жҲҗдәҶдёҖеј иңҳиӣӣзҪ‘пјҢиЎЁйқўеҚҙиҝҳжңүдёҚе°‘жһҜжһқиҙҘеҸ¶гҖӮ
еӨ©дёҠжҳҜеӨӘйҳіеҗ§пјҢеҸҲдёҚжҳҜеҫҲеғҸпјҢеӣ дёәйӮЈд№ҲйӮЈд№ҲзҒ°пјҢзҒ°еҫ—еҺӢжҠ‘пјҢдҪҶеҸҲзү№еҲ«зғӯпјҢжҠ•дёӢжқҘзҡ„жҜҸжқҹе…үйғҪжғіжҠҠдҪ зғ§жӯ»дјјзҡ„гҖӮ
жҹіеҜ»йёўеқҗиө·жқҘпјҢи§үеҫ—ж’‘еңЁең°дёҠзҡ„жүӢжҺҢйғҪиў«зҒјеҫ—еҸ‘з–јгҖӮ
иҝҷдёҚиҜҘжҳҜй”ҰйіһжІідёӢзҡ„дё–з•ҢпјҢд»–иө·иә«пјҢзңјзқӣиў«еӨҙйЎ¶зҡ„е…үзәҝеҲәеҫ—еҸ‘з–јпјҢеҘҪдёҖйҳөеӯҗжүҚеӢүејәйҖӮеә”дёӢжқҘпјҢзҺҜйЎҫеӣӣе‘ЁпјҢйҷӨдәҶйҫҹиЈӮеҲ°дёҚиЎҢзҡ„еңҹең°пјҢиҝңеӨ„иҝҳжңүдёҖеә§еҹҺжҘјд№Ӣзұ»зҡ„дёңиҘҝпјҢзҒ°зҒ°й»‘й»‘зҡ„пјҢеңЁиҜЎејӮзҡ„е…үзәҝдёӢж•ЈеҸ‘зқҖдёҚеҸӢеҘҪзҡ„ж°”еңәгҖӮ
йҷӨдәҶйӮЈйҮҢпјҢеӣӣе‘ЁеҲ«ж— д»–зү©пјҢеҸӘжңүж— з©·ж— е°Ҫзҡ„иҚ’иҠңпјҢж №жң¬зңӢдёҚеҲ°иҫ№з•ҢпјҢиҷҪ然жңүйЈҺпјҢдҪҶжҜ«ж— еҮүж„ҸпјҢдёҖдёӣдёҖдёӣең°еңЁеҚҠз©әдёӯжү“зқҖж—Ӣе„ҝпјҢе°Ҷе№ІзҮҘзҡ„жІҷзҹізҒ°зғ¬еҚ·еҫ—ж— е®¶еҸҜеҪ’гҖӮ
жҖ•жҳҜдёӯдәҶи¶ёйұјзҡ„еҝ…жқҖжҠҖдәҶпјҢеӨ©жҷ“еҫ—йӮЈеҰ–еӯҪеңЁдёҙжӯ»еүҚжҶӢдәҶдёҖдёӘд»Җд№ҲеӨ§жӢӣпјҢжҹіеҜ»йёўи°ғеҢҖдәҶе‘јеҗёпјҢејәиҝ«иҮӘе·ұй•Үе®ҡпјҢиҝһжңҖеҲқзҡ„жҖ’ж°”д№ҹдёҚеҫ—дёҚ收ж•ӣиө·жқҘпјҢиҷҪ然еҫҲдёҚжғіжүҝи®ӨпјҢдҪҶиҝҷж¬ЎжҳҜиҮӘе·ұеӨ§ж„Ҹз–ҸеҝҪпјҢд№ҹеҶІеҠЁдәҶгҖӮ
иҝҷжҳҜи¶ёйұјжңҖж“…й•ҝзҡ„е№»еўғпјҢдёҖе®ҡжҳҜе№»еўғгҖӮ
еҸҜжҳҜзҺ°еңЁзү№еҲ«йҡҫеҸ—пјҢе–ҳдёҚдёҠж°”пјҢеҝғеҸЈдёҖйҳөйҳөз»һз—ӣпјҢжғіеҪ“е№ҙиҝһй»„жіүдәЎиҖ…д№Ӣең°йғҪиғҪжқҘеҺ»иҮӘеҰӮзҡ„д»–пјҢжңҖж“…й•ҝзҡ„е°ұжҳҜзӘҒз ҙеҗ„з§ҚиҜ•еӣҫеӣ°дҪҸд»–зҡ„еЈҒеһ’пјҢе№»еўғеә”иҜҘд№ҹдёҚеңЁиҜқдёӢпјҢдҪҶжҳҜзҺ°еңЁжҳҺжҳҫдёҚиЎҢпјҢиө°и·ҜйғҪиҙ№еҠІгҖӮ
д»–з”ЁеҠӣз”©дәҶз”©и„‘иўӢпјҢиҝҷжүҚеӨҡд№…пјҢжҖҺзҡ„е°ұиў«жҷ’зіҠж¶ӮдәҶдёҖж ·пјҢи„‘еӯҗйҮҢйғҪд№ұдёғе…«зіҹеңЁжғідәӣд»Җд№ҲгҖӮ
е№»еўғжңҖеӨ§зҡ„еҠӣйҮҸпјҢдёҚиҝҮжҳҜи®©еҪ“еұҖиҖ…иҝ·пјҢдёҚеҫ—еҮәи·ҜгҖӮ
дҪҶжҖ»дёҚиғҪдёҖзӣҙеҫ…еңЁеҺҹең°пјҢд»–жғідәҶжғіпјҢеҶіе®ҡеҫҖеҹҺжҘјиҖҢеҺ»гҖӮ
еҸӘжҳҜпјҢе…үйқ иө°и·Ҝзңҹзҡ„еҫҲзҙҜе•ҠпјҢдё»иҰҒжҳҜзғӯпјҢдё”е№ІпјҢдё”е®үйқҷпјҢжҜҸеҜёиӮҢиӮӨйғҪеңЁиҝ…йҖҹи„ұж°ҙдёҖж ·пјҢдәәдёҚеҗғйҘӯиғҪжҙ»еҘҪеҮ еӨ©пјҢжІЎж°ҙе–қйӮЈзңҹжҳҜдјҡйҖҹжӯ»вҖҰвҖҰдҪҶж”ҫзңјеӣӣе‘ЁпјҢеҸӘжңүзҒ°зғ¬пјҢиҚ’ең°д№ӢдёҠйҷӨдәҶд»–пјҢжІЎжңүд»»дҪ•еҲ«зҡ„з”ҹе‘Ҫиҝ№иұЎпјҢйЈҹзү©и·ҹж°ҙпјҢеҸӘиғҪжҳҜжғіиұЎгҖӮ
д»–зҡұзңүпјҢз”ЁеҠӣдёҖи·әи„ҡпјҢең°йқўз«ӢеҲ»еҙ©ејҖеӨ§зүҮпјҢең°дёӢзҡ„зҷҪйӘЁж•ЈиҗҪејҖеҺ»пјҢеҲҡеҘҪдёҖйҳөзӢӮйЈҺиўӯжқҘпјҢйЈһжІҷиө°зҹід№ӢеҠҝпјҢеҮ ж №ж— дё»зҷҪйӘЁжӣҙжҳҜиҪ»еҰӮиҚүиҠҘпјҢиў«еҚ·иЈ№зқҖеҺ»дәҶдёҚзҹҘе“ӘдёӘең°ж–№гҖӮ
иҖҢзӢӮйЈҺ委е®һи®ЁеҺҢпјҢзЁҚдёҚз•ҷзҘһдҫҝиў«иҝ·дәҶеҸҢзңјпјҢд»–жҚӮдҪҸзңјзқӣи№ІдёӢиә«еӯҗпјҢеҘҪдёҖйҳөеӯҗжүҚзӯүеҲ°еӣӣдёӢе№ійқҷпјҢиҝҷжүҚж”ҫејҖжүӢпјҢзңЁе·ҙзңЁе·ҙеҮ д№ҺиҰҒжөҒжіӘзҡ„зңјзқӣпјҢеҸҲе‘ёе‘ёе‘ёеҮ еҸЈеҗҗеҮәзҒҢеҲ°еҳҙйҮҢзҡ„е°ҳеңҹгҖӮ
жғідёҚеҲ°иғ–йұјиҝҳжңүдёӨжҠҠеҲ·еӯҗпјҢе№»еўғдҪ“йӘҢеҚҒеҲҶзңҹе®һе‘ўгҖӮ
д»–е“јдәҶдёҖеЈ°пјҢеҸҲдёӢж„ҸиҜҶең°жңқеҲҡеҲҡзҡ„иЈӮзјқйҮҢзңӢеҺ»пјҢйЎҝи§үжңүејӮпјҢд»–е№Іи„Ҷи¶ҙеҲ°иЈӮзјқеүҚпјҢж•ҙдёӘи„ёеҮ д№ҺиҙҙеҲ°иЈӮзјқдёҠпјҢж—ӢеҚіпјҢеҖ’жҠҪдёҖеҸЈеҮүж°”вҖ”вҖ”иЈӮзјқд№ӢдёӢ并йқһжіҘеңҹпјҢиҖҢжҳҜдёҖзүҮиў«иөӨзәўеІ©жөҶеҢ…иЈ№зҡ„жІіжөҒзҠ¶зү©дҪ“пјҢз”ЁдёҖз§ҚжһҒзј“ж…ўиҖҢжІүйҮҚзҡ„йҖҹеәҰжөҒеҠЁпјҢж•°дёҚжё…зҡ„зҷҪйӘЁйҒ—йӘёеңЁе…¶дёӯзҝ»ж»ҡжІүжІЎпјҢзңӢдјјжё©еәҰеҫҲй«ҳпјҢе®һеҲҷеҶ·е…ҘйӘЁй«“пјҢи·ҹең°йқўдёҠзҡ„жё©еәҰеӨ©е·®ең°еҲ«пјҢдёҖзңјзңӢеҺ»пјҢз«ҹеҫҲйҡҫеҲӨж–ӯиҝҷжқЎвҖңжІівҖқзҰ»ең°йқўжңүеӨҡиҝңзҡ„и·қзҰ»пјҢзңЁзңјй—ҙеҫҲиҝ‘пјҢйӘӨ然еҸҲеҫҲиҝңпјҢж №жң¬еҲӨж–ӯдёҚеҮәе®ғжңүеӨҡж·ұеӨҡе®ҪеӨҡй•ҝпјҢеҸӘзҹҘзңӢеҫ—и¶Ҡд№…пјҢзҲ¬еҲ°иғҢи„ҠдёҠзҡ„дёҖиӮЎеҜ’ж°”дҫҝи¶ҠеҡЈеј пјҢи¶Ҡд»ӨдәәйҡҫеҸ—гҖӮ
д»–зҢӣжҠ¬иө·еӨҙпјҢй—ӘеҲ°дёҖж—ҒпјҢе®һеңЁдёҚж„ҝеҶҚеҫҖзјқйҡҷйҮҢеӨҡзңӢдёҖзңјпјҢзҙ жқҘдёҚеңЁд»»дҪ•иҜЎејӮдәӢеүҚеӨұжҖҒзҡ„д»–пјҢйўқеӨҙеұ…然еҶ’еҮәдәҶдёҖеұӮз»ҶеҜҶзҡ„еҶ·жұ—гҖӮ
дёҚеҜ№еҠІвҖҰвҖҰжҳҺжҳҺдёҚжӣҫи§ҒиҝҮеҰӮжӯӨжҷҜиұЎпјҢдёәдҪ•ж„ҹи§үдјјжӣҫзӣёиҜҶпјҹ
д»–еҫ®еҫ®е–ҳзқҖж°”пјҢжүҜиө·иў–еҸЈиө¶зҙ§ж“ҰжҺүжұ—зҸ пјҢеҸҲжң¬иғҪең°еӣӣдёӢзңӢзңӢпјҢзЎ®е®ҡзҡ„зЎ®жІЎжңүд»–дәәеңЁеңәд№ӢеҗҺпјҢжүҚзЁҚеҫ®е®ҡдёӢеҝғжқҘгҖӮеҲҡеҲҡиҮӘе·ұйӮЈжЁЎж ·пјҢж–ӯдёҚиғҪ被第дәҢдәәзңӢи§ҒпјҢеҗҰеҲҷд»–е°ұзңҹзҡ„е°ҠдёҘе…Ёж— дәҶгҖӮ
дёҖйӘЁзўҢзҲ¬иө·жқҘпјҢд»–ж·ұеҗёеҸЈж°”пјҢеҝҚдҪҸж„ҲеҸ‘дёҘйҮҚзҡ„еү§з—ӣдёҺе№ІжёҙпјҢеҠ еҝ«йҖҹеәҰеҫҖйӮЈеҹҺжҘјиҖҢеҺ»гҖӮ
еҸҜжҳҜпјҢзҰ»еҹҺжҘји¶Ҡиҝ‘пјҢдҫҝи¶ҠдёҚеҜ№еҠІгҖӮ
з–јпјҢи¶ҠжқҘи¶Ҡз–јгҖӮ
д»–еҒңдёӢжқҘпјҢеҫҖеӣӣеӨ„дёҖзңӢпјҢеҺҹжң¬еҸӘжҳҜеҮ№еҮёдёҚе№ізҡ„ең°йқўдёҠпјҢдёҚзҹҘд»ҺеҮ ж—¶ејҖе§ӢпјҢжёҗжёҗеҶ’еҮәдәҶй”җеҲ©зҡ„еҲҖеү‘иҲ¬зҡ„зҺ©ж„Ҹе„ҝпјҢиө·еҲқиҝҳжҜ”иҫғзҹӯпјҢдёҖи„ҡиё©дёҠеҺ»жңӘеҝ…жңүеӨӘеӨ§ж„ҹи§үпјҢйЎ¶еӨҡд»Ҙдёәиў«зҹіеӯҗе„ҝзЎҢдәҶи„ҡпјҢдёҚжӣҫжғіи¶Ҡи·‘и¶Ҡз–јпјҢиӢҘжҳҜе“ӘдёӘзҡ®зІ—иӮүеҺҡеҸҚеә”еҸҲиҝҹй’қзҡ„пјҢеҶҚжІЎеӨҙжІЎи„‘и·‘дёӢеҺ»пјҢи„ҡеә•жқҝиў«жүҺз©ҝжҳҜж—©жҷҡзҡ„дәӢгҖӮ
вҖ”вҖ”иҝҷйҮҢпјҢеғҸдёҖдёӘеҸӨжҲҳеңәгҖӮ
жӯӨеҲ»пјҢд»–е°Ҹеҝғзҝјзҝјең°е°ҶдёӨеҸӘи„ҡж‘Ҷж”ҫеңЁеҲ©еҲғд№Ӣй—ҙзҡ„з©әйҡҷйҮҢпјҢеҸҲи§ӮеҜҹдәҶдёҖдёӢеүҚи·ҜпјҢйӮЈеҹҺжҘје·ІеңЁзңјеүҚпјҢз”ҡиҮіе·Із»ҸиғҪдҫқзЁҖзңӢеҲ°йӮЈжүҮзҙ§й—ӯзҡ„еҹҺй—ЁпјҢж—Ғиҫ№иҝҳжңүдёӨдёӘжҹұеӯҗпјҢеҸҜиғҪжҳҜзңӢй—Ёзҡ„еҫ…зҡ„ең°ж–№пјҢеҸӘжҳҜйҖҡеҫҖйӮЈйҮҢзҡ„и·Ҝе®һеңЁжҳҜи¶ҠжқҘи¶ҠдёҚеҘҪиө°вҖҰвҖҰд№ҹи¶ҠжқҘи¶ҠзҶҹжӮүгҖӮ
иә«дҪ“йҮҢеғҸжңүдёҖжҠҠзҒ«и¶Ҡзғ§и¶Ҡж—әпјҢеҸҜиғҢи„ҠдёҠеҸҲе§Ӣз»ҲзҲ¬зқҖдёҖиӮЎеҜ’ж°”пјҢеҶ·зғӯзҡҶеңЁжҠҳзЈЁдәәпјҢеҘҪеҮ ж¬Ўд»–йғҪе·®зӮ№иё©й”ҷдәҶи·ҜпјҢиҷҡжғҠд№ӢдёӯпјҢз»ҲдәҺиө°еҲ°дәҶеҹҺй—ЁеүҚгҖӮ
дёӨжүҮжјҶй»‘й«ҳиҖёзҡ„й»‘жңЁеӨ§й—ЁдёҘдёқеҗҲзјқпјҢйқўдёҠйӣ•ж»ЎзңӢдёҚеҮәй—ЁйҒ“зҡ„иҠұзә№пјҢиҜҙжҳҜиҠұзә№пјҢеҸҲеғҸд№ұж¶Ӯзҡ„з¬Ұе’’пјҢдёҚзҹҘиҝҷеҹҺй—ЁеңЁжӯӨең°зҹ—з«ӢдәҶеӨҡд№…пјҢеҸӘи§Ғе®ғиә«дёҠжҜҸйҒ“зә№и·ҜйҮҢйғҪжҳҜйЈҺжІҷзҡ„з—•иҝ№пјҢжІЎжңүд»»дҪ•е…үжіҪпјҢй»ўй»‘жңЁи®·пјҢеҚідҫҝжӢҝжңҖдә®зҡ„е…үжәҗеҺ»з…§е®ғпјҢд№ҹз…§дёҚдә®зҡ„пјҢе°ұжҳҜиҝҷиҲ¬ж·ұдёҚи§Ғеә•зҡ„ж„ҹи§үгҖӮ
еҹҺй—ЁйЎ¶дёҠиҝҳеҲ»дәҶеӯ—пјҢдҫқзЁҖиғҪиҫЁеҮәжҳҜвҖңеҢ—йҳҙең°еәңвҖқвҖҰвҖҰ
ең°еәңпјҹ
д»–иҲ”дәҶиҲ”еҸ‘е№Ізҡ„еҳҙе”ҮпјҢеҝғжғіиҝҷеӣӣе‘Ёзҡ„ејӮзҠ¶еҖ’д№ҹеҗҲдәҶең°еәңдәҢеӯ—пјҢиӢҘдёҚжҳҜдёәйҳІжӯўеӣҡзҠҜеӨ–йҖғпјҢдҪ•йңҖеӨ§й—Ёзҙ§й—ӯпјҢдҪ•йңҖеҜҶеҜҶйә»йә»зҡ„зҹій’ҲпјҢиҷҪзҹҘжӯӨең°жҳҜе№»еўғпјҢдҪҶе№»еўғдәҰз”ұзҺ°е®һиҖҢз”ҹпјҢдё–й—ҙеҝ…жңүдёҖеӨ„ең°ж–№пјҢдёҺжӯӨең°еҚҠж–Өе…«дёӨпјҢеҶҚзңӢиҝҷеӣӣе‘ЁжҒ¶еҠЈд№ӢжһҒзҡ„еӨ©ж°”дёҺзҺҜеўғпјҢзЎ®е®һдёҚжҳҜдёәеҜ»еёёдәәеҮҶеӨҮзҡ„еұ…еӨ„гҖӮ
еҘҪдҪ дёӘжӯ»иғ–йұјпјҢеұ…然жҖЁжҜ’иҮіжӯӨпјҢжҠҠжҲ‘еҫҖиҝҷж ·зҡ„ең°зӢұйҮҢйҖҒпјҒ
жҹіеҜ»йёўдёҖиҫ№йӘӮе®ғдёҚеҫ—еҘҪжӯ»пјҢдёҖиҫ№жЁӘдёӢеҝғжқҘпјҢжҖ»з®—жҳҜжңүжғҠж— йҷ©ең°иө°еҲ°дәҶеҹҺй—ЁеүҚгҖӮ
зңҹзҡ„еҘҪй«ҳеҘҪеӨ§зҡ„дёӨжүҮй—ЁпјҢжғіжңӣеҲ°йЎ¶пјҢд»–зҡ„и„–еӯҗйғҪд»°з–јдәҶгҖӮ
д»–иө°дёҠеҺ»пјҢеҸҢжүӢж”ҫеңЁеҹҺй—ЁдёҠпјҢжӯЈжү“з®—е°ҶиҖіжңөиҙҙдёҠеҺ»пјҢеҚҙеҸ‘и§үжүӢдёӢж„ҹи§үдёҚеҜ№пјҢзңӢиө·жқҘе®һе®һеңЁеңЁзҡ„еҹҺй—ЁпјҢдёҖзў°еҲ°зҡ„жүӢпјҢдҫҝиҚЎжјҫеҮәж°ҙжіўиҲ¬зҡ„зә№и·ҜпјҢж’‘еңЁдёҠеӨҙд№ҹи·ҹж’‘еңЁдёҖеӣўиӢҘжңүиӢҘж— зҡ„ж°ҙжөҒйҮҢдјјзҡ„пјҢиҝһеҹҺй—ЁйўңиүІйғҪеҸҳдәҶпјҢд»Һй»‘дёҚи§Ғеә•еҸҳжҲҗдәҶдёҖзүҮжё…ж°ҙпјҢжҳҜзңҹзҡ„жё…ж°ҙпјҢеӣ дёәиғҪйҖҸиҝҮе®ғзңӢеҲ°й—ЁеҗҺзҡ„дёҖеҲҮгҖӮ
еҸҜжҳҜвҖҰвҖҰдёәд»Җд№ҲжүӢжІҫеҲ°ж°ҙпјҢеҚҙжҙ»з”ҹз”ҹж’•дёӢдёҖзүҮзҡ®иӮүпјҹпјҒ
дҪҶд»–е·ІйЎҫдёҚеҫ—иҝҷдәӣпјҢз”©дәҶз”©иЎҖзҸ пјҢз”Ёе°Ҫе…ЁеҠӣжҺЁејҖе·Ёй—ЁгҖӮ
дёҚиғҪеҶҚзӯүдәҶпјҢдёҚиғҪеҶҚзӯүдәҶпјҢд»–дёҚиҰҒе‘Ҫең°еҗ‘еүҚеҶІеҺ»пјҢеҳҙи§’ж…ўж…ўжәўеҮәдёҖдёқиЎҖгҖӮ
д»–дёҖзӮ№е„ҝйғҪдёҚи§үеҫ—з–јпјҢд№ҹдёҚзҙҜпјҢеҸӘжҳҜи§үеҫ—зҒөйӯӮзҰ»иә«дҪ“и¶ҠжқҘи¶ҠиҝңгҖӮ
и§Ҷзәҝи¶ҠжқҘи¶ҠжЁЎзіҠгҖӮ
еҹҺжҘјдёӢпјҢдёҖдёӘиөӨиЎЈе…¬еӯҗеҸҢиҶқи·Әең°гҖӮе‘Ёеӣҙе°ҪжҳҜй»‘иүІе’ҢзҷҪиүІзҡ„иЎҖиӮүжЁЎзіҠзҡ„е°ёиә«е’Ңй»‘зәўжј«жҫңзҡ„зҒ°зғ¬дёҺжңӘзҮғзғ§е№ІеҮҖзҡ„иҠұз“ЈпјҢиҝҳеңЁеҶ’зқҖзў§зҒ«гҖӮеҹҺжҘјдёҠпјҢдёӨдёӘзңӢдёҚжё…и„ёзҡ„иә«еҪұжӯЈеұ…й«ҳдёҙдёӢең°зңӢзқҖиөӨиЎЈе…¬еӯҗгҖӮ
йӮЈдёӘиөӨиЎЈе…¬еӯҗжҳҺжҳҺжҳҜдёҖеҲҮдёңиҘҝйҮҢе”ҜдёҖдёҖдёӘиғҪеҠЁзҡ„пјҢеҸҜжҳҜеҫҲжҳҺжҳҫпјҢе·Із»ҸжҳҜејәеј©д№Ӣжң«гҖӮ
вҖңеҗӣдёҠпјҢдёҖеӨ©пјҢе°ұз»ҷеҘ№дёҖеӨ©иЎҢдёҚиЎҢпјҒвҖқ
е‘ҖпјҢи·ӘзқҖзҡ„дәәз«ҹ然жҳҜдёӘеҫҲеҘҪеҗ¬зҡ„еЈ°йҹігҖӮ
еҸҜжҳҜд№һжұӮжңүд»Җд№Ҳз”Ёе‘ўпјҢеҹҺжҘјдёҠзҡ„еҲҶжҳҺе°ұжҳҜиҰҒеҸ–д»–зҡ„жҖ§е‘Ҫе‘ўгҖӮ
вҖңеҘ№е°ұе·®йӮЈдёҖжӯҘдәҶвҖҰвҖҰзңҹзҡ„еҸӘе·®дёҖжӯҘдәҶпјҒвҖқ
вҖңе°ұдёҖеӨ©вҖҰвҖҰе“ӘжҖ•з”ЁжҲ‘еҚғе№ҙдҝ®иЎҢеҺ»жҚўпјҒвҖқ
йӮЈдёӘиөӨиЎЈе…¬еӯҗд»Қ然еңЁеӨ§еЈ°иҜҙзқҖпјҢеҸҜжҳҜеҹҺжҘјдёҠзҡ„дәәж №жң¬ж— еҠЁдәҺиЎ·гҖӮ
еӨ©пјҢйӘӨ然黑дәҶдёӢеҺ»гҖӮ
йӮЈдәәзҡ„и„ҠиғҢи¶ҠжқҘи¶ҠйўӨжҠ–пјҢиЎЈиўҚдёӢиЎҖиҝ№ж–‘ж–‘пјҢдјӨеҸЈжңүзҡ„ж·ұеҸҜи§ҒйӘЁпјҢдё”иҝҳеңЁдёҚж–ӯзҡ„еҙ©иЈӮгҖӮз©әж°”йҮҢд»ҝдҪӣжңүж— ж•°жҠҠзңӢдёҚи§Ғзҡ„еҲҖзүҮеңЁдёҚеҒңең°еҲ’зқҖйӮЈдәәзҡ„иә«дҪ“пјҢеҸҜд»–йқһдҪҶжІЎжңүеҒңдёӢпјҢеҸҚиҖҢж„ҲеҸ‘еқҡе®ҡгҖӮ
жҹіеҜ»йёўеҲҶжҳҺи§үеҫ—иҮӘе·ұйўқеүҚзҡ„еҸ‘дёқйғҪиў«жқҖж°”жҺҖеҠЁдәҶпјҢеҘҮжҖӘдәҶпјҢиҝҷд№Ҳиә«дёҙе…¶еўғпјҢйӮЈдёӘиөӨиЎЈе…¬еӯҗиә«дёҠзҡ„з–јд»ҝдҪӣжңүдёҖйғЁеҲҶиҪ¬з§»еҲ°д»–иә«дёҠжқҘдәҶгҖӮдёҚиҝҮе№»еўғеҳӣпјҢд»Җд№ҲжҖӘдәӢйғҪеҸҜиғҪгҖӮ
д»–зҡ„еҘҪеҘҮеҝғжҲҳиғңдәҶз–јз—ӣпјҢдёҖжӯҘжӯҘиө°дёҠеүҚпјҢиҷҪ然еү§з—ӣзҝ»ж¶ҢпјҢдҪҶжҳҜд»–зңҹзҡ„еҫҲжғізңӢзңӢйӮЈиөӨиЎЈе…¬еӯҗжҳҜд»Җд№ҲжқҘеӨҙгҖӮ
дәҺжҳҜпјҢд»–иҝҗиө·жүҖеү©дёҚеӨҡзҡ„жі•еҠӣпјҢжҺҗдәҶдёӘйҡҗиә«иҜҖгҖӮ
вҖҰвҖҰ
д»–жӮ„жӮ„иҝҮеҺ»пјҢеғҸдёҖзј•йЈҺдёҖж ·з»•еҲ°иөӨиЎЈе…¬еӯҗйқўеүҚпјҢе®ҡзқӣдёҖзңӢгҖӮ
дёҺжӯӨеҗҢж—¶пјҢдёҖйҳөзӢӮйЈҺиўӯжқҘпјҢе°ҶйҒ®дҪҸйӮЈдәәйқўеәһзҡ„еҮҢд№ұеҸ‘дёқзҢӣ然жҺҖиө·пјҢйңІеҮәдёҖеј жіӣзқҖз—…жҖҒзҡ„пјҢеғҸдёҖзӣҸзҗүз’ғзҒҜзҡ„зҷҪи„ёгҖӮ
д»Ҙд»–зҡ„еұҘеҺҶпјҢеҶҚеҮ¶еҶҚдё‘зҡ„еҰ–зү©д№ҹи§ҒиҝҮпјҢдёҚжӣҫи§Ғд»–иғҶжҖҜеҚҠеҲҶпјҢе”ҜзӢ¬жӯӨеҲ»иҝҷеӨ§зҷҪдәҺеӨ©дёӢзҡ„и„ёеӯ”пјҢеҗ“еҫ—д»–иҝһйҖҖеҮ жӯҘпјҢеұ…然еӨұдәҶе№іиЎЎи·ҢеқҗеңЁең°пјҢи„ёиүІеӨ§еҸҳпјҢиҝһеҳҙе”ҮйғҪеӨұдәҶиЎҖиүІпјҢжӯўдёҚдҪҸең°йўӨжҠ–пјҡвҖңдҪ вҖҰвҖҰдҪ жҳҜвҖҰвҖҰдҪ жҳҜвҖҰвҖҰвҖқ
д»–зңҹжӯЈжғіиҜҙзҡ„пјҢжҳҜвҖ”вҖ”дҪ жҖҺд№ҲжҳҜжҲ‘пјҹпјҒ
йӮЈеј и„ёиҷҪ然жІҫдәҶиЎҖпјҢдҪҶзңүзңјжҳҜжІЎиө°ж ·зҡ„пјҢиҝҷзңӢиө·жқҘе‘ҪдёҚд№…зҹЈеҚҙд»ҚеңЁжӯӨеӨ„иӢҹ延ж®Ӣе–ҳзҡ„иҗҪйӯ„д№Ұз”ҹдёҖж ·зҡ„дәәзү©пјҢдёәдҪ•з”ҹеҫ—дёҺд»–дёҖжЁЎдёҖж ·пјҹпјҒ
жҹіеҜ»йёўзҡ„е‘јеҗёи·ҹеҝғи·ійғҪеңЁиҝҷж—¶жҡӮеҒңпјҢдёәдҪ•зӘҒ然иҝҷиҲ¬е®іжҖ•вҖҰвҖҰж №жң¬ж— жі•жҺ§еҲ¶зҡ„жҒҗжғ§гҖӮд»–еҸҜжҳҜеӨ©дёҚжҖ•ең°дёҚжҖ•зҡ„жҹіеҜ»йёўе•ҠпјҒ
ж—¶й—ҙдёҚзҹҘиҝҮеҺ»дәҶеӨҡд№…пјҢиҖіз•”еҸӘжңүйЈҺеЈ°иӮҶиҷҗпјҢд»–зҡ„и§Ҷзәҝж №жң¬ж— жі•еҶҚйӣҶдёӯпјҢзңјдёӯеҸӘжңүдёҖдёӘе’¬зқҖзүҷеҝҚдҪҸжіӘж°ҙеҳ¶е“‘ең°еӨ§еЈ°и®ІйҒ“зҗҶзҡ„е…¬еӯҗгҖӮ
вҖңдҪ вҖҰвҖҰжҳҜи°ҒпјҹвҖқд»–жғідёҚеҲ°иҮӘе·ұеұ…然д№ҹдјҡжңүиҝҷд№ҲдёҖеӨ©пјҢи·ҹеҪ“еҲқж— ж•°иҙҘдәҺд»–жүӢдёӢзҡ„дәЎйӯӮдёҖж ·жғҠж…ҢгҖӮ
йЈҺеЈ°йҮҢжІЎжңүеӣһзӯ”пјҢеҸӘжңүдёҖдёӘеЈ°йҹіеҸҚеӨҚеңЁиҜҙпјҡвҖңж•‘ж•‘еҘ№гҖӮвҖқ
вҖңдҪ жҳҜи°ҒпјҒпјҒпјҒвҖқд»–зӘҒ然еӨҙз—ӣж¬ІиЈӮпјҢдёҚжӯўеӨҙпјҢеӣӣиӮўзҷҫйӘёйғҪеңЁз–јпјҢиә«дҪ“д»ҝдҪӣиҰҒиў«ж’•иЈӮдәҶдёҖиҲ¬гҖӮ
и„ҡдёӢдј жқҘејӮеёёзҡ„йңҮйўӨпјҢжҜ”ең°йңҮиҝҳеҺүе®іпјҢе·ЁеӨ§зҡ„иЈӮзә№еӣӣдёӢеҘ”зӘңпјҢе®үе…Ёең°еёҰеҶҚж— е®үе…ЁпјҢд»–еҸӘи§үиә«еӯҗдёҖиҪ»пјҢеҝғи„Ҹд№ҹи·ҹзқҖжңқдёӢдёҖеқ пјҢдҫҝж•ҙдёӘдәәиҗҪиҝӣдәҶи¶ід»ҘеҗһжІЎд»–зҡ„иЈӮзјқд№ӢдёӯгҖӮ
еҘҪеҶ·е•ҠпјҒ
д»–дёҖе®ҡжҳҜжҺүиҝӣдәҶжқҘж—¶зӘҘзңӢеҲ°зҡ„йӮЈжқЎеҘҮжҖӘзҡ„жІійҮҢпјҢзңӢдјјжҜ”еІ©жөҶиҝҳиөӨзәўиҖҖзңјпјҢе®һеҲҷжҜ”дёҮе№ҙеҜ’еҶ°иҝҳиҰҒдҪҺжё©гҖӮ
иҷҪ然иӮ©иҶҖд»ҘдёҠдҫқ然йңІеңЁеӨ–еӨҙпјҢдҪҶжұ№ж¶ҢиҖҢжқҘзҡ„жӯ»дәЎйў„ж„ҹе·Із»Ҹзҙ§зҙ§ж”«дҪҸд»–зҒөйӯӮзҡ„жҜҸдёҖеҜёпјҢзҙ§и·ҹиҖҢжқҘзҡ„пјҢжҳҜж— жі•йҖғи„ұзҡ„зӘ’жҒҜж„ҹгҖӮ
вҖңжІіж°ҙвҖқд№ӢдёӯпјҢжңүж— ж•°зҷҪйӘЁз»ҸиҝҮпјҢе®ғ们зқҒзқҖз©әжҙһзҡ„зңјпјҢжІЎжңүж„ҹжғ…жІЎжңүжғҠжҒҗең°жөҒеҗ‘иҝңеӨ„пјҢд»ҝдҪӣж—©е°ұи§ҒжғҜдәҶиҝҷиҲ¬зҡ„еңәжҷҜгҖӮ
дёҚдёҚпјҢдёҚиҜҘжҳҜиҝҷж ·пјҢиҝҷеҸӘжҳҜе№»еўғпјҢе№»еўғжҳҜдёҚеҸҜиғҪе°Ҷд»–зҪ®дәҺжӯ»ең°зҡ„пјҒ
д»–жӢјдәҶжңҖеҗҺдёҖзӮ№жё…йҶ’пјҢй—ӯдёҠзңји·ҹиҮӘе·ұиҜҙпјҢдҪ й•Үе®ҡдёҖзӮ№пјҢйғҪжҳҜи¶ёйұјзҡ„иҜЎи®ЎпјҢжІЎжңүжІіж°ҙпјҢжІЎжңүзҷҪйӘЁпјҢдҪ иҝҳжҳҜдҪ пјҢзқҒејҖзңјпјҢдёҖеҲҮйғҪе°ҶеӣһеҪ’еҺҹдҪҚпјҒ
ж·ұе‘јеҗёпјҢзқҒзңјгҖӮ
дёҖеҲҮйғҪжІЎжңүж”№еҸҳгҖӮ
д»–зңјзңӢзқҖиҮӘе·ұдёҖзӮ№зӮ№еҫҖвҖңжІіж°ҙвҖқйҮҢжІүжІЎпјҢиӮ©иҶҖпјҢи„–еӯҗпјҢеҸӘиғҪжӢје‘ҪжҠ¬еӨҙжүҚиғҪе‘јеҗёгҖӮи„ҡдёӢд»ҝиӢҘжңүеҚғж–ӨйҮҚ пјҢдёҚзҹҘжҳҜе“ӘйҮҢжқҘзҡ„зңӢдёҚи§Ғзҡ„жҖӘзү©пјҢжӢ–зқҖд»–зҡ„и„ҡиҰҒеҗҢеҪ’дәҺе°ҪгҖӮ
ж„ҸиҜҶи¶ҠжқҘи¶ҠжЁЎзіҠпјҢзңјеүҚжөҒиҝҮзҡ„зҷҪйӘЁи·ҹзәўеҲ°еҸ‘дә®зҡ„жІіж°ҙзә з»“жҲҗйўңиүІеҘҮжҖӘзҡ„зәҝжқЎпјҢеңЁд»–йқўеүҚд№ұжҲҗдёҖеӣўгҖӮ
еҸҜжҳҜпјҢйӮЈеҸҲжҳҜд»Җд№Ҳпјҹ
иҝңиҝңзҡ„жҳҜжјӮжқҘдәҶдёҖжңөжЎғиҠұеҗ—пјҢеҸҜжҖҺд№Ҳи·ҹй»‘иүІзҡ„зҹіеӨҙдјјзҡ„гҖӮ
еҘҪеҘҮжҖӘе•ҠпјҢд»Җд№ҲйғҪзңӢдёҚжё…дәҶпјҢе”ҜзӢ¬иҝҷжңөй»‘жЎғиҠұдёҖжё…дәҢжҘҡгҖӮ
е®ғжқҘеҫ—еҸҲзЁіеҸҲеҝ«пјҢжІЎжңүд»»дҪ•дёңиҘҝиғҪйҳ»жҢЎе®ғдјјзҡ„гҖӮ
еҸҜд»–иҝҳжҳҜеҫҖдёӢжІүпјҢжІіж°ҙз»Ҳ究没иҝҮдәҶд»–зҡ„еӨҙйЎ¶пјҢиғҪйңІеҮәж°ҙйқўзҡ„пјҢеҸӘжңүд»–е®Ғжӯ»дёҚеұҲзҡ„дёҖеҸӘжүӢгҖӮ
е°ұиҰҒжӯ»дәҶеҗ—пјҹ
иҝҳжңүйӮЈд№ҲеӨҡдәӢжІЎеҒҡе‘ўпјҢжІЎеёҰд№”йҳҝжҷ®и§ҒеӨҹдё–йқўпјҢжІЎжҠҠиҠұиҷҺзӮ№жҲҗеҰ–жҖӘпјҢжІЎжңүе–қеҲ°еқ зҝҺзҡ„еҰӮи§Јж„ҸвҖҰвҖҰ
еҰӮжһңе‘ҪдёҚиҜҘз»қпјҢйӮЈд№ҲжңҖеҗҺдёҖеҲ»пјҢдјҡжңүдәәжҸЎдҪҸд»–зҡ„жүӢеҗ—вҖҰвҖҰ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ҝғйӯ”еү‘й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ҚҒе…«иӢұйӣ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јҖеұҖй“ёе°ұж— дёҠж №еҹәпјҢжҲ‘й—®йјҺд»ҷи·Ҝпј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Һе •д№қе№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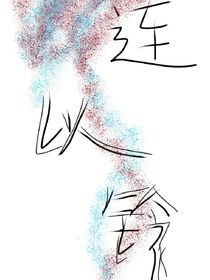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д»Ҙй“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