еӣӣеҖјеҠҹжӣ№еҮЎе°ҳеҗҚд»ҷйҳҷжғ‘
жҳҹеҸ°зҡ„зғӣзҒ«ж‘ҮжӣіпјҢе°ҶеӣӣеҖјеҠҹжӣ№зҡ„еҪұеӯҗжҠ•еңЁеҶ°еҶ·зҡ„зҺүеЈҒдёҠпјҢеғҸеӣӣе°Ҡиў«й’үеңЁеӨ©и§„йҮҢзҡ„зҹіеғҸгҖӮжҺҢиҫ°еҠҹжӣ№пјҲеҺҹеҙ”й’°пјүжҢҮе°–еҸҚеӨҚж‘©жҢІзқҖиў–дёӯйӮЈеҚҠжҲӘеҮЎй—ҙеўЁжқЎпјҢеўЁйҰҷж—©е·Іж·ЎеҺ»пјҢеҸҜд»–жҖ»и§үеҫ—пјҢйӮЈеўЁйҮҢиҝҳиЈ№зқҖй•ҝе®үй©ҝйҰҶзҡ„зғҹзҒ«ж°”вҖ”вҖ”йӮЈж—¶д»–еҸ«еҙ”й’°пјҢдёҚжҳҜвҖңжҺҢиҫ°еҠҹжӣ№вҖқпјҢеј еҚғдјҡе–Ҡд»–вҖңеҙ”е…„вҖқпјҢжқҺдёҮдјҡйҖ’жқҘеҲҡжё©еҘҪзҡ„зІ—иҢ¶пјҢеҲҳжҙӘдјҡеңЁд»–еҶҷгҖҠдәәй—ҙзҷҫдәӢеҪ•гҖӢж—¶пјҢй»ҳй»ҳж·»дёҖзӣҸзҒҜгҖӮ
вҖңзңҹзҡ„дёҚиғҪеҶҚеҸ«еҙ”й’°дәҶеҗ—пјҹвҖқжҺҢж—ҘеҠҹжӣ№пјҲеҺҹеј еҚғпјүзӘҒ然жү“з ҙжІүй»ҳпјҢеЈ°йҹіеҺӢеҫ—еҫҲдҪҺпјҢеғҸжҳҜжҖ•иў«жҳҹеҸ°еӨ–зҡ„йЈҺеҗ¬еҺ»гҖӮд»–ж”ҘзқҖиў–еҸЈзҡ„ж—§еёғиЎҘдёҒпјҢйӮЈжҳҜеҪ“е№ҙеңЁжҪје…іжҺЁиҪҰж—¶зЈЁз ҙзҡ„пјҢд»–еҒ·еҒ·зјқдәҶеқ—й©ҝйҰҶзҡ„ж—§еёғпјҢеҰӮд»ҠжҲҗдәҶд»–и—ҸеңЁй”ҰиўҚдёӢзҡ„вҖңзҪӘиҜҒвҖқвҖ”вҖ”зҺүеёқиҜҙиҰҒеҝҳеҺ»еҮЎе°ҳпјҢеҸҜиҝҷиЎҘдёҒдёҠзҡ„й’Ҳи„ҡпјҢжҜҸдёҖй’ҲйғҪи®°зқҖвҖңеј еҚғвҖқжҳҜи°ҒгҖӮ
жҺҢжңҲеҠҹжӣ№пјҲеҺҹжқҺдёҮпјүеһӮзңёзңӢзқҖжЎҲдёҠзҡ„вҖңиҫ°е…үз°ҝвҖқпјҢз°ҝеӯҗдёҠвҖңжҺҢжңҲеҠҹжӣ№вҖқеӣӣдёӘеӯ—е·Ҙж•ҙеҶ°еҶ·пјҢжҜ”д»–еҪ“е№ҙеңЁеҮЎй—ҙи®°е®ўдәәдёўеҸ‘з°Әж—¶зҡ„еӯ—иҝ№пјҢе°‘дәҶеӨӘеӨҡжё©еәҰгҖӮвҖңйҷӣдёӢиҜҙпјҢеҗҚеӯ—е°ұжҳҜиҒҢдҪҚпјҢеҮЎе°ҳеҗҚжҳҜвҖҳжү§еҝөвҖҷгҖӮвҖқд»–еЈ°йҹіеҸ‘涩пјҢвҖңеҸҜжҲ‘们еҪ“е№ҙеңЁдәәй—ҙпјҢи®°гҖҠдәәй—ҙзҷҫдәӢеҪ•гҖӢпјҢеё®е®ўдәәеҜ»зү©пјҢиө¶иҪҰйҖҒзІ®иҚүпјҢдёҚжҳҜдёәдәҶжҠӣдәҶвҖҳжқҺдёҮвҖҷиҝҷдёӘеҗҚеӯ—жқҘеҒҡд»ҷзҡ„гҖӮвҖқ
жҺҢж—¶еҠҹжӣ№пјҲеҺҹеҲҳжҙӘпјүз»ҲдәҺејҖеҸЈпјҢеЈ°йҹідҫқж—§жІҷе“‘пјҢеҚҙеёҰзқҖд»ҺжңӘжңүиҝҮзҡ„иҝ·иҢ«пјҡвҖңд»ҘеӨ©и§„дёәйҮҚпјҢжҠӣдәҶдәІжғ…еҸӢжғ…вҖҰвҖҰйӮЈжҲ‘们дёҠжқҘеҒҡзҘһпјҢеӣҫд»Җд№ҲпјҹвҖқ
иҝҷиҜқеғҸдёҖеқ—зҹіеӨҙпјҢз ёеңЁеҸҰеӨ–дёүдәәеҝғйҮҢгҖӮжҳҜе•ҠпјҢеҪ“е№ҙ他们еңЁдәәй—ҙпјҢдёҚиҝҮжҳҜеӣӣдёӘжү“зҗҶй©ҝйҰҶзҡ„вҖңеӣӣж–№е®ўвҖқпјҢжІЎжұӮиҝҮд»ҷпјҢжІЎзӮјиҝҮдё№пјҢеҸӘеӣ и®°ж»ЎдәҶгҖҠдәәй—ҙзҷҫдәӢеҪ•гҖӢпјҢжӮҹдәҶвҖңж—¶дёҺжғ…вҖқпјҢжүҚиў«ж–ҮжӣІжҳҹеҗӣзӮ№еҢ–еҪ’дҪҚгҖӮйӮЈж—¶д»–们д»ҘдёәпјҢеҒҡзҘһжҳҜиғҪжӣҙеҘҪең°жҠӨзқҖдәәй—ҙзҡ„зғҹзҒ«пјҢеғҸеҪ“е№ҙйҖҒзІ®иҚүж•‘жҪје…іе°ҶеЈ«йӮЈж ·пјҢеҸҜеҰӮд»ҠпјҢзҺүеёқиҰҒ他们еҝҳеҮЎе°ҳгҖҒж–ӯжғ…ж„ҹпјҢеҒҡдёӘеҸӘи®ӨеӨ©и§„зҡ„вҖңз®—зӯ№вҖқгҖӮ
вҖңд»ҘеүҚжҳҜдәәж—¶пјҢжІЎдҝ®дёәпјҢжІЎжғізқҖеҒҡзҘһгҖӮвҖқжҺҢиҫ°еҠҹжӣ№пјҲеҺҹеҙ”й’°пјүиҪ»иҪ»еҸ№дәҶеҸЈж°”пјҢе°ҶеўЁжқЎжҢүеңЁвҖңиҫ°е…үз°ҝвҖқзҡ„з©әзҷҪеӨ„пјҢеўЁз—•жҷ•ејҖпјҢеғҸдёҖж»ҙи—ҸдёҚдҪҸзҡ„жіӘпјҢвҖңйӮЈж—¶еҙ”й’°гҖҒеј еҚғгҖҒжқҺдёҮгҖҒеҲҳжҙӘпјҢдёҚиҝҮжҳҜжғіжҠҠдәәй—ҙзҡ„ж•…дәӢи®°е…ЁпјҢжғіи®©иө¶и·Ҝзҡ„дәәе–қеҸЈзғӯжұӨпјҢжғіи®©дёўдәҶдёңиҘҝзҡ„е®ўдәәе°‘дәӣйҡҫиҝҮгҖӮжҲ‘们д»ҘдёәпјҢжҲҗдәҶзҘһпјҢиғҪи®©иҝҷдәӣвҖҳеҘҪвҖҷеӨҡдәӣпјҢжІЎжғіеҲ°вҖҰвҖҰвҖқ
д»–жІЎиҜҙдёӢеҺ»пјҢеҸҜеҸҰеӨ–дёүдәәйғҪжҮӮгҖӮжІЎжғіеҲ°зҘһзҡ„дё–з•ҢйҮҢпјҢвҖңжғ…вҖқжҳҜзҪӘпјҢвҖңеҮЎе°ҳеҗҚвҖқжҳҜй”ҷпјҢиҝһ他们еҪ“е№ҙеј•д»ҘдёәеӮІзҡ„вҖңи®°дәәй—ҙдәӢвҖқпјҢеҰӮд»Ҡд№ҹжҲҗдәҶвҖңи®°д»ҷдҪӣй”ҷеӨ„вҖқзҡ„е·®дәӢгҖӮжҺҢжңҲеҠҹжӣ№пјҲеҺҹжқҺдёҮпјүжғіиө·еҪ“е№ҙиҖҒйҒ“еЈ«иҜҙвҖңдҪ 们жң¬е°ұдёҚжҳҜеҮЎдәәпјҢеҸӘжҳҜеҝҳдәҶжқҘи·ҜвҖқпјҢзҺ°еңЁд»–们жүҫзқҖдәҶвҖңжқҘи·ҜвҖқпјҢеҚҙдёўдәҶвҖңеҪ’йҖ”вҖқвҖ”вҖ”йӮЈеҪ’йҖ”дёҚжҳҜеӨ©еәӯзҡ„жҳҹеҸ°пјҢжҳҜй•ҝе®үзҡ„еӣӣж–№й©ҝйҰҶпјҢжҳҜе…«д»ҷжЎҢдёҠзҡ„зІ—иҢ¶пјҢжҳҜгҖҠдәәй—ҙзҷҫдәӢеҪ•гҖӢйҮҢзҡ„жӮІж¬ўзҰ»еҗҲгҖӮ
вҖңд»ҘеүҚжҳҜдәәж—¶пјҢжІЎиҖғиҷ‘иҝҮеҒҡзҘһиҰҒж–ӯжғ…гҖӮвҖқжҺҢж—ҘеҠҹжӣ№пјҲеҺҹеј еҚғпјүиӢҰ笑зқҖж‘ҮеӨҙпјҢвҖңйӮЈж—¶и§үеҫ—пјҢзҘһд»ҷиҜҘжҳҜжҠӨзқҖдәәзҡ„пјҢеғҸжҲҸж–ҮйҮҢиҜҙзҡ„пјҢдјҡеё®з©·дәәйҷҚйӣЁпјҢдјҡж•‘иӢҰдәәи„ұзҰ»еҚұйҡҫгҖӮеҸҜзҺ°еңЁжҲ‘们иҮӘе·ұжҲҗдәҶзҘһпјҢеҚҙиҝһеҸ«иҮӘе·ұеҗҚеӯ—зҡ„жқғеҲ©йғҪжІЎжңүпјҢиҝһжғіи®°зқҖдәәй—ҙзҡ„жңӢеҸӢйғҪз®—вҖҳзҠҜзҰҒвҖҷгҖӮвҖқ
жҺҢж—¶еҠҹжӣ№пјҲеҺҹеҲҳжҙӘпјүжҠ¬еӨҙжңӣеҗ‘еҮЎй—ҙзҡ„ж–№еҗ‘пјҢйӮЈйҮҢзҡ„зҒҜзҒ«еғҸжҳҹжҳҹпјҢжҜ”еӨ©еәӯзҡ„жҳҹиҫ°жҡ–еҫ—еӨҡгҖӮвҖңиӢҘжҳҜзҘһиҰҒж— жғ…пјҢйӮЈеҒҡзҘһиҝҳдёҚеҰӮеҒҡдәәгҖӮвҖқд»–иҪ»еЈ°иҜҙпјҢвҖңеҪ“е№ҙеңЁдәәй—ҙпјҢжҲ‘们没дҝ®дёәпјҢеҚҙиғҪеё®дәәпјӣзҺ°еңЁжңүдәҶд»ҷйӘЁпјҢеҚҙеҸӘиғҪе®ҲзқҖеӨ©и§„пјҢз®—зқҖж—¶иҫ°пјҢи®°зқҖй”ҷеӨ„вҖҰвҖҰиҝҷд»ҷпјҢеҪ“еҫ—жІЎж„ҸжҖқгҖӮвҖқ
зғӣзҒ«зӘҒ然вҖңеҷје•ӘвҖқдёҖеЈ°пјҢзғ§ж–ӯдәҶзҒҜиҠҜгҖӮжҺҢиҫ°еҠҹжӣ№пјҲеҺҹеҙ”й’°пјүиө¶зҙ§йҮҚж–°зӮ№зҮғпјҢзҒ«е…үжҳ еңЁд»–и„ёдёҠпјҢз«ҹжңүдәҶеҮ еҲҶеҮЎдәәзҡ„жҖ…然гҖӮд»–жӢҝиө·зӢјжҜ«пјҢеҚҙжІЎеңЁвҖңиҫ°е…үз°ҝвҖқдёҠеҶҷеҸ–з»ҸиҝӣеәҰпјҢиҖҢжҳҜеңЁеҝғйҮҢй»ҳеҝөдәҶдёҖйҒҚвҖңеҙ”й’°гҖҒеј еҚғгҖҒжқҺдёҮгҖҒеҲҳжҙӘвҖқвҖ”вҖ”зҺүеёқиғҪзҰҒ他们еңЁеҳҙдёҠиҜҙпјҢеҚҙзҰҒдёҚдәҶ他们еңЁеҝғйҮҢи®°гҖӮ
жҳҹеҸ°зҡ„йЈҺжӣҙеҮүдәҶпјҢеҗ№еҫ—вҖңиҫ°е…үз°ҝвҖқе“—е“—дҪңе“ҚпјҢеғҸжҳҜеңЁеӮ¬дҝғ他们иө¶зҙ§и®°е®Ңд»Ҡж—Ҙзҡ„е·®дәӢгҖӮеҸҜеӣӣдәәйғҪжІЎеҠЁпјҢеҸӘжҳҜжңӣзқҖеҮЎй—ҙзҡ„ж–№еҗ‘пјҢеҝғйҮҢзҝ»жқҘиҰҶеҺ»ең°жғіпјҡиӢҘжҳҜж—©зҹҘйҒ“еҒҡзҘһиҰҒеҝҳе°ҳж–ӯжғ…пјҢеҪ“е№ҙеңЁй•ҝе®үпјҢ他们жҲ–и®ёиҝҳдјҡе®ҲзқҖеӣӣж–№й©ҝйҰҶпјҢе°ұзқҖзІ—иҢ¶пјҢи®°зқҖдәәй—ҙзҡ„ж•…дәӢпјҢеҒҡеӣӣдёӘжҷ®йҖҡзҡ„вҖңеӣӣж–№е®ўвҖқ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еҰӮд»ҠиҝҷеӣӣдёӘиҝһиҮӘе·ұеҗҚеӯ—йғҪеҝ«дёҚж•ўи®Өзҡ„еӣӣеҖјеҠҹжӣ№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ө¶е°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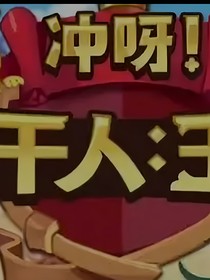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йҘје№ІдәӢи®°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еңЁејӮз•Ңзә№д№қйҫҷжӢүжЈә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Ҫ’е°ҳеҲӣдё–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家з”өи§ҶжңәиғҪз©ҝи¶ҠдёҮз•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