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з« пјҡжҷәж–—жҺўеӯҗпјҡз”»иҲ«жҡ—еҸ·дј дҝЎ
зҒ°зҫҪйёҪжҢҜзҝ…йЈһиө·зҡ„зһ¬й—ҙпјҢеҮӨжҳӯе·ІиҪ¬иә«иө°е…Ҙе··е°ҫжҡ—еӨ„гҖӮеҘ№и§ЈдёӢи’ҷзңјеёғе·ҫеЎһиҝӣиў–иўӢпјҢжҚўдёҠйқ’иЎ«е№ҝиў–зҡ„ејӮеҹҹиЈ…жқҹпјҢзңүеҝғдёҖзӮ№жңұз Ӯжҳ зқҖжҷЁе…үеҫ®й—ӘгҖӮзғ¬еҝғзҒ«еңЁдҪ“еҶ…жөҒиҪ¬пјҢе°Ҷж–№жүҚиҢ¶жҘјйҮҢйӮЈдәӣзӘҘжҺўзҡ„зӣ®е…үе°Ҫж•°еҗһе…Ҙж— еҪўгҖӮ
з”»иҲ«еҒңеңЁзӮҺжҙІжІіж№ҫпјҢйҮ‘жјҶйӣ•ж Ҹжҳ зқҖж°ҙжіўиҪ»жҷғгҖӮеҘ№жҸҗеҚ·иҖҢдёҠпјҢе®ҲеҚ«еҸӘжү«дәҶдёҖзңјеҘ№зҡ„з”»еёҲи…°зүҢдҫҝж”ҫиЎҢвҖ”вҖ”йӮЈжҳҜжҳЁеӨңд»ҺдёҖеҗҚйҶүеҖ’зҡ„йҡҸиЎҢж–ҮеҗҸиә«дёҠйЎәжқҘзҡ„гҖӮ
иҲұеҶ…дёқз«№жңӘжӯҮпјҢе®ҫе®ўдёүдёүдёӨдёӨеҖҡж ҸйҘ®й…’гҖӮеҘ№еҜ»дәҶи§’иҗҪеёӯдҪҚеұ•ејҖй•ҝеҚ·пјҢ笔й”ӢиҪ»иҗҪпјҢеўЁиүІжёҗжҹ“гҖӮ
йЈһжӘҗйҮҚйҳҒпјҢйҮ‘иҺІй“әең°пјҢе®«еЁҘжү§зҒҜз©ҝиЎҢдәҺеӣһе»Ҡд№Ӣй—ҙгҖӮеҘ№з”»зҡ„жҳҜгҖҠеҮӨе®«жҳҘе®ҙеӣҫгҖӢпјҢжҜҸдёҖеӨ„йӣ•жўҒж–—жӢұйғҪдёҺи®°еҝҶдёӯеҲҶжҜ«дёҚе·®гҖӮиҝҷжҳҜиҚҜеёҲж•ҷеҘ№иғҢиҜөеҚҒе№ҙзҡ„ж—§жҷҜпјҢд№ҹжҳҜеҮӨж—ҸиҰҶзҒӯеүҚжңҖеҗҺдёҖеңәзӣӣе…ёгҖӮ
дәәзҫӨжёҗжёҗиҒҡжӢўгҖӮжңүдәәдҪҺиҜӯпјҡвҖңиҝҷз”»еҫ—еҖ’жҳҜзғӯй—№гҖӮвҖқд№ҹжңүдәәе—Ө笑пјҡвҖңејӮеҹҹдәәжҮӮд»Җд№ҲдёӯеҺҹйЈҺзү©гҖӮвҖқ
еҘ№дёҚзӯ”пјҢеҸӘжҢҮе°–еҫ®йЎҝпјҢеңЁз”»еҚ·еҸідёӢи§’еӢҫеҮәдёҖйҒ“з»Ҷзә№вҖ”вҖ”йӮЈжҳҜиҘҝж®ҝе»ҠжҹұдёҠзҡ„иЈӮз—•пјҢе”ҜжңүдәІиҝ‘д№Ӣдәәж–№зҹҘе…¶еӯҳеңЁгҖӮ
дёҖеҗҚиҖҒиҖ…з«ҷеңЁдәәзҫӨеҗҺж–№пјҢжүӢжү¶жңЁжқ–пјҢжҢҮиҠӮжіӣзҷҪгҖӮд»–з©ҝзқҖдҪҝеӣўйЎҫй—®зҡ„ж·ұиӨҗй•ҝиўҚпјҢйқўе®№жһҜж§ҒпјҢзңјзҘһеҚҙйӘӨ然еҮқдҪҸгҖӮ
вҖңиҝҷвҖҰвҖҰдёҚеҸҜиғҪгҖӮвҖқд»–е–ғе–ғеҮәеҸЈпјҢеҸҲжҖҘеҝҷй—ӯеҳҙгҖӮ
еҮӨжҳӯд»ҚдҪҺеӨҙдҪңз”»пјҢе”Үи§’еҫ®еҠЁгҖӮзғ¬еҝғзҒ«жӮ„然ж„ҹзҹҘеҲ°йӮЈиӮЎжү‘йқўиҖҢжқҘзҡ„жғҠз—ӣпјҢеҰӮжҪ®ж°ҙиҲ¬ж¶ҢжқҘеҸҲйҖҖеҺ»гҖӮеҘ№зҹҘйҒ“пјҢйұје’¬й’©дәҶгҖӮ
еҘ№зј“зј“жҠ¬з¬”пјҢеңЁз”»еҚ·иҫ№зјҳиҪ»иҪ»дёҖзӮ№пјҢйҡҸеҚіеҺӢдҪҺеЈ°йҹіпјҢд»…и®©йӮЈдәәеҗ¬и§ҒпјҡвҖңдёүж—ҘеҗҺпјҢеҹҺдёңз ҙеәҷи§ҒгҖӮеёҰдҪ зҹҘйҒ“зҡ„жқҘгҖӮвҖқ
иҜқйҹіиҗҪпјҢиў–дёӯ银й’Ҳз–ҫе°„иҖҢеҮәпјҢй’үе…ҘеӨҙйЎ¶жЁӘжўҒгҖӮй’Ҳе°ҫиҪ»йўӨпјҢе—ЎйёЈдёҚжӯўпјҢдјјиӯҰй’ҹдҪҷе“ҚгҖӮ
иҖҒиҖ…зҢӣең°жҠ¬еӨҙпјҢзӣ®е…үиҝҪзқҖйӮЈж №з»Ҷй’ҲпјҢи„ёиүІеҸ‘зҒ°гҖӮд»–еј дәҶеј еҸЈпјҢз»ҲжңӘеҮәеЈ°пјҢиҪ¬иә«еҢҶеҢҶзҰ»иҲ№гҖӮ
еҮӨжҳӯ收笔еҚ·з”»пјҢзҘһжғ…е№ійқҷеҰӮеҲқгҖӮ
***
еӨңиүІеҲқйҷҚпјҢз ҙеәҷж®ӢеһЈйҡҗеңЁиҚ’иҚүж·ұеӨ„гҖӮеҘ№жҜ”зәҰе®ҡж—¶й—ҙж—©еҲ°еҚҠдёӘж—¶иҫ°пјҢи№ІеңЁеҖҫеЎҢзҡ„йҰҷзӮүеҗҺпјҢе°ҶдёҖж’®ж·ЎзІүиүІиҚҜзІүж’’е…ҘзӮүеә•зҒ°зғ¬дёӯгҖӮжӯӨиҚҜж— е‘іпјҢйҒҮзғӯеҲҷж•Јиҝ·йӣҫпјҢеҸҜдҪҝдәәжҳҸжІүзүҮеҲ»пјҢи¶іеӨҹеә”еҜ№зӘҒеҸ‘еҹӢдјҸгҖӮ
зғ¬еҝғзҒ«еңЁиғёдёӯзј“иЎҢпјҢж„ҹзҹҘзқҖеӣӣе‘Ёж°”жҒҜгҖӮеәҷеӨ–дёңеҚ—гҖҒиҘҝеҢ—гҖҒжӯЈеҚ—дёүеӨ„пјҢе‘јеҗёиҠӮеҘҸзҙҠд№ұпјҢи—ҸеҢҝд№ӢдәәжӯЈеңЁејәеҺӢеҠЁйқҷгҖӮжҳҜжҺўеӯҗпјҢдёҚжҳҜжқҖжүӢпјҢдҪҶи¶ід»ҘйҖҡйЈҺжҠҘдҝЎгҖӮ
еҘ№йҖҖеӣһдё»ж®ҝйҳҙеҪұпјҢйқ еўҷйқҷеқҗпјҢжүӢдёӯж‘©жҢІзқҖдёҖж”ҜзҺүз°ӘгҖӮй»‘иҺІзә№и·ҜеҲ»еҫ—жһҒж·ұпјҢи§ҰжүӢеҫ®еҮүгҖӮиҝҷжҳҜиҚҜеёҲдёҙеҲ«жүҖиө пјҢиҜҙжҳҜеҪ“е№ҙеҮӨеҗҺжңҖиҙҙиә«д№Ӣзү©пјҢе”ҜжңүиЎҖи„үзӣёжүҝиҖ…иғҪеј•е…¶е…ұйёЈгҖӮ
еӯҗж—¶еҲҡиҝҮпјҢжңЁй—Ёеҗұе‘ҖжҺЁејҖгҖӮ
иҖҒиҮЈиёүи·„жӯҘе…ҘпјҢиЎЈиҘҹжІҫе°ҳпјҢйўқи§’еҶ’жұ—гҖӮд»–зҺҜйЎҫеӣӣе‘ЁпјҢеЈ°йҹіеҸ‘жҠ–пјҡвҖңжІЎдәәи·ҹиёӘжҲ‘вҖҰвҖҰеә”иҜҘжІЎжңүгҖӮвҖқ
еҮӨжҳӯжңӘеҠЁпјҢеҸӘе°ҶзҺүз°ӘиҪ»иҪ»жҗҒеңЁжңҲе…үз…§еҸҠзҡ„зҹіеҸ°дёҠгҖӮжё…иҫүиҗҪдёӢпјҢз°Әиә«еҝҪ然жіӣиө·дёҖеұӮе№Ҫе…үпјҢеҰӮеҗҢжңүзҒ«иҮӘеҶ…зҮғиө·гҖӮ
иҖҒиҮЈзһіеӯ”йӘӨзј©пјҢиҶқзӣ–дёҖиҪҜпјҢи·ӘеҖ’еңЁең°гҖӮ
вҖңиҝҷз°ӘеӯҗвҖҰвҖҰвҖқд»–дјёжүӢж¬Іи§ҰеҸҲжӯўпјҢвҖңеҮӨеҗҺйқўеүҚпјҢе®ғд»ҺдёҚзҰ»иә«гҖӮжӮЁвҖҰвҖҰжӮЁзңҹжҳҜвҖҰвҖҰвҖқ
вҖңдҪ иҝҳи®°еҫ—еҘ№пјҹвҖқеҮӨжҳӯз»ҲдәҺејҖеҸЈпјҢиҜӯи°ғе№ізЁіпјҢвҖңи®°еҫ—еҘ№еңЁе“ӘдёҖеӨ©жӯ»зҡ„пјҹвҖқ
вҖңи…ҠжңҲеҲқдёғгҖӮвҖқд»–еЈ°йҹіз ҙзўҺпјҢвҖңйӮЈдёҖеӨңпјҢеңЈеҹҹзҰҒеҶӣзӘҒе…ҘеҮӨе®«пјҢиҜҙеҘ№з§ҒйҖҡдә”еҹҹпјҢж„ҸеӣҫзҜЎжқғгҖӮеҸҜеҘ№ж №жң¬жІЎеҸҚжҠ—вҖҰвҖҰеҘ№и®©жҲ‘们жҠӨдҪҸе©ҙеӯ©пјҢиҮӘе·ұиө°иҝӣзҒ«жө·гҖӮвҖқ
еҮӨжҳӯжҢҮе°–еҫ®иң·гҖӮзғ¬еҝғзҒ«иҪ»иҪ»дёҖи·іпјҢе°ҶйӮЈиӮЎжӮІжҖҶеҗёе°ҪпјҢеҸҚе“әдёәжё…жҳҺгҖӮ
вҖңи°ҒдёӢзҡ„д»ӨпјҹвҖқ
вҖңзҡҮеёқгҖӮвҖқиҖҒиҮЈе’¬зүҷпјҢвҖңдҪҶд»–дёҚж•ўдәІдёҙпјҢжҙҫдәҶеӣӣеӨ§еҹҹдё»иҒ”жүӢеӣҙе®«гҖӮдёңеўғйңңеҺҹеҹҺдё»зҺҮй“ҒйӘ‘иёҸзўҺе®«й—ЁпјҢеҚ—еІӯеӨ§зҘӯеҸёд»ҘжҜ’зғҹе°ҒдҪҸеҮәеҸЈпјҢиҘҝжј жІҷеәӯз»ҹйўҶзәөзҒ«зғ§еӨ©пјҢеҢ—жёҠе№Ҫең°е°ҶеҶӣж–©ж–ӯжүҖжңүйҖҖи·ҜвҖҰвҖҰ他们жӯғиЎҖдёәзӣҹпјҢеҸӘдёәйҷӨдҪ еҮӨж—ҸгҖӮвҖқ
еҮӨжҳӯеһӮзңёгҖӮеҗҚеҚ•дёҠзҡ„еҗҚеӯ—пјҢдёҖдёӘйғҪжІЎе°‘гҖӮ
вҖңйҒ—иҜҸе‘ўпјҹвҖқ
вҖңиў«зғ§дәҶгҖӮвҖқиҖҒиҮЈдҪҺдёӢеӨҙпјҢвҖңжҳҜжҲ‘дәІжүӢз„ҡжҜҒзҡ„гҖӮзҡҮеёқйҖјжҲ‘еҶҷдёӢеҒҮиҜҸпјҢз§°еҮӨеҗҺи°ӢйҖҶпјҢж Әиҝһд№қж—ҸгҖӮжҲ‘дёҚж•ўдёҚд»ҺвҖҰвҖҰиӢҘжҲ‘дёҚеҶҷпјҢ全家еҚіеҲ»й—®ж–©гҖӮвҖқ
вҖңжүҖд»ҘдҪ жҙ»дәҶдёӢжқҘгҖӮвҖқеҘ№зј“зј“иө·иә«пјҢиө°еҲ°д»–йқўеүҚпјҢдҝҜи§ҶзқҖд»–пјҢвҖңеҒҡдәҶдҪҝеӣўйЎҫй—®пјҢжӣҝ他们清зҗҶж—§иҙҰпјҢжҺ©зӣ–з—•иҝ№гҖӮвҖқ
вҖңжҲ‘еҸӘжҳҜжғіжҙ»зқҖпјҒвҖқд»–зӘҒ然жҠ¬еӨҙпјҢзңјдёӯеҗ«жіӘпјҢвҖңжҲ‘зҹҘйҒ“й”ҷдәҶпјҒиҝҷдәӣе№ҙжҲ‘еӨңеӨңжўҰи§ҒйӮЈеңәзҒ«пјҢжўҰи§ҒеҘ№зңӢзқҖжҲ‘зҡ„зңјзҘһвҖҰвҖҰе…¬дё»пјҢжҲ‘иҝҳз•ҷзқҖдёҖд»ҪжҠ„жң¬пјҒдёҚжҳҜйҒ—иҜҸпјҢжҳҜеҪ“ж—Ҙе®«еҸҳеҗҺпјҢжҲ‘еҒ·еҒ·и®°дёӢзҡ„дәӢз”ұжё…еҚ•пјҒдёҠйқўеҶҷзқҖи°ҒиҝӣдәҶеҮӨе®«пјҢи°ҒзӯҫдәҶеұ д»ӨпјҢи°ҒжӢҝдәҶеҜҶжЎЈпјҒвҖқ
еҮӨжҳӯзӣҜзқҖд»–иүҜд№…пјҢзғ¬еҝғзҒ«еңЁдҪ“еҶ…зј“зј“ж—ӢиҪ¬пјҢз”„еҲ«жҜҸдёҖеҸҘиҜқзҡ„зңҹдјӘгҖӮи°ҺиЁҖдјҡжҝҖиө·зҒјж„ҸпјҢиҖҢжӯӨеҲ»пјҢеҸӘжңүеҶ°еҶ·зҡ„зңҹе®һеңЁжөҒеҠЁгҖӮ
вҖңжӢҝеҮәжқҘгҖӮвҖқ
вҖңеңЁжҲ‘жҲҝдёӯпјҢдҪҝеӣўй©ҝйҰҶиҘҝеҺўз¬¬дёүй—ҙпјҢеәҠжқҝдёӢеӨ№еұӮгҖӮвҖқд»–йўӨжҠ–зқҖиҜҙпјҢвҖңдҪҶжҲ‘дёҚиғҪзҺ°еңЁз»ҷдҪ пјҒжқҺеҙҮд»Ҡж—ҘеҜҹи§үжҲ‘еңЁз”»иҲ«еӨұжҖҒпјҢе·ІжҙҫдәәзӣҜжҲ‘пјҒиӢҘжҲ‘д»ҠжҷҡдёҚеҪ’пјҢжҳҺж—Ҙе°ұдјҡжңүдәәжҗңжҹҘжҲҝй—ҙпјҒвҖқ
еҮӨжҳӯжІүй»ҳзүҮеҲ»пјҢеҝҪиҖҢдјёжүӢжүЈдҪҸд»–жүӢи…•гҖӮи„үжҗҸжҖҘдҝғпјҢеҚҙдёҚиҷҡжө®пјҢзЎ®зі»жғ§е®һжғ…гҖӮ
вҖңеҘҪгҖӮвҖқеҘ№иҜҙпјҢвҖңдҪ еӣһеҺ»гҖӮжҳҺж—ҘеҚҲж—¶пјҢдҪ еңЁйӣҶеёӮеҚ–ж—§д№Ұж‘ҠеүҚй©»и¶ідёүжҒҜпјҢжҲ‘дјҡеҸ–иө°дёңиҘҝгҖӮиӢҘдҪ йӘ—жҲ‘вҖ”вҖ”вҖқ
еҘ№жқҫејҖжүӢпјҢжҢҮе°–еҲ’иҝҮд»–е–үй—ҙпјҢдёҚз•ҷз—•иҝ№гҖӮ
вҖңе…ЁеҹҺйғҪдјҡзҹҘйҒ“пјҢжҳҜи°ҒеңЁи…ҠжңҲеҲқдёғйӮЈеӨңпјҢдәІжүӢзғ§дәҶеҮӨж—ҸжңҖеҗҺзҡ„иҜҒиЁҖгҖӮвҖқ
иҖҒиҮЈдјҸең°йўӨжҠ–пјҢдёҚж•ўжҠ¬еӨҙгҖӮ
еәҷеӨ–йЈҺеЈ°жёҗзҙ§пјҢиҝңеӨ„дј жқҘзҠ¬еҗ гҖӮи—ҸеңЁеӨ–йқўзҡ„жҺўеӯҗејҖе§Ӣ移еҠЁдҪҚзҪ®пјҢи„ҡжӯҘиҪ»еҫ®пјҢеҚҙйҖғдёҚиҝҮеҘ№зҡ„ж„ҹзҹҘгҖӮ
еҘ№жІЎжңүз«ӢеҲ»зҰ»ејҖпјҢиҖҢжҳҜејҜи…°жӢҫиө·зҺүз°ӘпјҢйҮҚж–°жҸ’еӣһеҸ‘й—ҙгҖӮжңҲе…үдёӢпјҢйӮЈжҠ№е№Ҫе…үд»ҚжңӘж•ЈеҺ»гҖӮ
зғ¬еҝғзҒ«еңЁдҪ“еҶ…дҪҺйёЈпјҢд»ҝдҪӣйў„ж„ҹйЈҺжҡҙе°ҶиҮігҖӮ
еҘ№и·ЁеҮәеәҷй—ЁпјҢиә«еҪұжІЎе…ҘеӨңиүІгҖӮ
иә«еҗҺпјҢиҖҒиҮЈзҳ«еқҗеңЁең°пјҢд№…д№…жңӘеҠЁгҖӮ
жҹҗдёҖеҲ»пјҢд»–зј“зј“жҠ¬еӨҙпјҢжңӣеҗ‘еәҷеӨ–ж ‘еҪұгҖӮ
йӮЈйҮҢз«ҷзқҖдёҖдёӘдәәеҪұпјҢжҠ«зқҖдҪҝеӣўдҫҚеҚ«зҡ„зҹӯз”ІпјҢжүӢдёӯжҸЎзқҖдёҖе°ҒеҜҶе°Ғзҡ„дҝЎгҖӮ
иҖҒиҮЈзһіеӯ”зҢӣзј©гҖӮ
йӮЈдәәзј“зј“жҠҪеҮәзҒ«жҠҳпјҢзӮ№зҮғдәҶдҝЎи§’гҖӮ
зҒ«е…үжҳ дә®дәҶд»–зҡ„и„ёвҖ”вҖ”жӯЈжҳҜжқҺеҙҮзҡ„дәІдҝЎгҖӮ
дҝЎзәёзҮғзғ§ж®Ҷе°ҪпјҢзҒ°зғ¬йЈҳж•ЈгҖӮ
иҖҢеҮӨжҳӯжӯЈиө°еңЁйҖҡеҫҖеҹҺеҚ—зҡ„е°ҸйҒ“дёҠпјҢжүӢжҢҮжҠҡиҝҮеҸ‘й—ҙзҡ„зҺүз°ӘпјҢжӯҘдјҗжңӘеҒңгҖӮ
еҘ№зҡ„иҖіз•”д»ҝдҪӣе“Қиө·дёҖеЈ°жһҒиҪ»зҡ„еҸ№жҒҜпјҢеғҸжҳҜжқҘиҮӘзҷҫе№ҙеүҚзҡ„е®«еўҷд№ӢеҶ…гҖӮ
дҪҶеҘ№жІЎжңүеӣһеӨҙ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ө¶е°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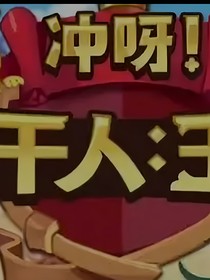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йҘје№ІдәӢи®°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еңЁејӮз•Ңзә№д№қйҫҷжӢүжЈә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Ҫ’е°ҳеҲӣдё–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家з”өи§ҶжңәиғҪз©ҝи¶ҠдёҮз•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