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з« пјҡзӣІеҘіеә”еҫҒпјҡиҚҜй“әжҡ—и—ҸжқҖжңәеұҖ
йһӢеә•йӮЈж №зәўдёқж–ӯејҖзҡ„зһ¬й—ҙпјҢеҮӨжҳӯи„ҡе°–еҫ®йЎҝпјҢдёҚеҠЁеЈ°иүІе°Ҷж®ӢзәҝеҚ·е…Ҙиў–дёӯгҖӮеҘ№жү¶зқҖиҪҰжқҝиҫ№зјҳиө°дёӢ马иҪҰпјҢи„ҡжӯҘиҷҡжө®пјҢеғҸжҳҜз«ҷдёҚзЁіиҲ¬жҷғдәҶдёҖдёӢпјҢеҸіжүӢжҗӯдёҠиҚҜй“әй—ЁеүҚзҡ„жңЁжҹұпјҢжҢҮе°–иҪ»иҪ»дёҖжҚ»пјҢе·Іе°Ҷж–ӯзәҝи—Ҹиҝӣиў–иўӢеӨ№еұӮгҖӮ
жҺҢжҹңз«ҷеңЁй—ЁеҸЈпјҢзӣ®е…үеңЁеҘ№и„ёдёҠеҒңз•ҷзүҮеҲ»гҖӮ
вҖңе…ҲеүҚиҜҙжҳҜе“‘еҘіпјҢжҖҺд№ҲеҸҲжҲҗдәҶзһҺзҡ„пјҹвҖқ
еҮӨжҳӯдҪҺзқҖеӨҙпјҢжҠ¬жүӢиҪ»жӢҚиҖідҫ§пјҢйҡҸеҗҺзј“зј“жҢҮеҗ‘еҸҢзңјпјҢжҜ”еҲ’еҮәе…ҲеӨ©иҒӢе“‘гҖҒеҗҺеӣ жғҠеҗ“еӨұжҳҺзҡ„жүӢеҠҝгҖӮеҘ№иҜҙиҜқж—¶еЈ°йҹіжһҒиҪ»пјҢд»ҝдҪӣжҖ•жғҠжү°дәҶд»Җд№ҲпјҢеҸӘиҜҙиғҪж„ҹзҹҘе…үеҪұиҪ®е»“пјҢе…¶дҪҷзҡҶжЁЎзіҠгҖӮ
жҺҢжҹңжІЎеҶҚиҝҪй—®пјҢеҸӘж·Ўж·ЎйҒ“пјҡвҖңиҝӣжқҘеҗ§гҖӮвҖқ
иҚҜй“әеҶ…йҷҲи®ҫз®ҖжңҙпјҢиҚҜжҹңжІҝеўҷиҖҢз«ӢпјҢеҮ еҸЈиҚҜзӮүж‘ҶеңЁеҗҺе Ӯи§’иҗҪгҖӮеҮӨжҳӯиў«е®үжҺ’дҪҸеңЁеҒҸеұӢпјҢдёҖй—ҙдёҚи¶іеҚҒжӯҘзҡ„е°ҸжҲҝпјҢеәҠиҫ№жңүзӣҸжІ№зҒҜпјҢжЎҢдёҠж”ҫзқҖзІ—з“·зў—е’ҢдёҖеҸҢж—§еёғйһӢгҖӮеҘ№иҝӣй—ЁеҗҺдҫҝеқҗеңЁеәҠжІҝпјҢеҸҢжүӢдәӨеҸ ж”ҫеңЁиҶқдёҠпјҢеғҸжһҒдәҶдёҖдёӘжё©йЎәжҖҜејұзҡ„зӣІеҘіеё®е·ҘгҖӮ
ж¬Ўж—Ҙжё…жҷЁпјҢжҺҢжҹңе”ӨеҘ№еҲ°еҗҺе ӮгҖӮ
вҖңд»Ҡж—ҘзӮјвҖҳиөӨйіһж №вҖҷпјҢдҪ жқҘжү“дёӢжүӢгҖӮвҖқ
иҝҷиҚҜжҖ§зғҲпјҢйҒҮзҒ«жҳ“зҲҶпјҢеҜ»еёёдәәйңҖз»ғжңҲдҪҷжүҚж•ўиҝ‘зӮүгҖӮеҮӨжҳӯеә”еЈ°дёҠеүҚпјҢдҪҺеӨҙзӣҜзқҖең°йқўпјҢдёҖжӯҘжӯҘжҢӘеҲ°зӮүеүҚгҖӮеҘ№дјёжүӢеҺ»еҸ–иҚҜеӢәпјҢжҢҮе°–еҲҡи§ҰеҲ°жҹ„з«ҜпјҢеҝҪ然вҖңдёҚж…ҺвҖқдёҖж»‘пјҢиҚҜеӢәзҝ»иҗҪпјҢж“ҰиҝҮзӮүжІҝи·Ңе…ҘзӮүиҶӣгҖӮ
зҒ«жҳҹеӣӣжә…гҖӮ
жҺҢжҹңзңүеӨҙдёҖзҡұпјҢжӯЈиҰҒж–ҘиҙЈпјҢеҚҙи§ҒзӮүдёӯиҚҜж¶ІеҺҹжң¬жө‘жөҠеҸ‘й»‘пјҢз«ҹеңЁзүҮеҲ»й—ҙиҪ¬дёәжҫ„зәўйҖҸдә®пјҢжқӮиҙЁе°Ҫж¶ҲгҖӮ
д»–зӣҜдҪҸзӮүйјҺпјҢеҚҠжҷҢдёҚиҜӯгҖӮ
вҖңдҪ вҖҰвҖҰж„ҹи§үдёҚеҲ°зғӯпјҹвҖқ
еҮӨжҳӯж‘ҮеӨҙпјҢжҢҮе°–еҫ®еҫ®йўӨжҠ–пјҢеҒҡеҮәз•Ҹжғ§зҒ«з„°зҡ„жЁЎж ·гҖӮ
жҺҢжҹңжІүй»ҳең°зңӢдәҶеҘ№дёҖзңјпјҢиҪ¬иә«зҰ»ејҖгҖӮ
еҪ“жҷҡпјҢеӯҗж—¶еҲҡиҝҮгҖӮ
й—ЁзјқеӨ–дј жқҘжһҒиҪ»зҡ„и„ҡжӯҘеЈ°пјҢз”ұиҝңеҸҠиҝ‘пјҢеңЁеҘ№жҲҝй—ЁеүҚеҒңдҪҸгҖӮй—Ёй—©ж— еЈ°ж»‘ејҖпјҢдёҖйҒ“иә«еҪұжӮ„然жҪңе…ҘгҖӮйӮЈдәәжүӢжҢҒзҹӯеҢ•пјҢиЎЈи§’жү«иҝҮй—Ёж§ӣж—¶з•ҘдҪңиҝҹз–‘пјҢйҡҸеҚійҖјиҝ‘еәҠиҫ№пјҢжҠ¬жүӢе°ұиҰҒеүІеҘ№жүӢи…•гҖӮ
еҮӨжҳӯж—©е·ІеҜҹи§үгҖӮ
зғ¬еҝғзҒ«ж—©еңЁеҜ№ж–№йқ иҝ‘ж—¶дҫҝжӮ„然еҚҮжё©пјҢе°ҶйӮЈиӮЎжқҖж„Ҹе°Ҫж•°еҗһдёӢпјҢеҸҚе“әзҒөеҠӣи®©еҘ№зҘһеҝ—жё…жҳҺгҖӮеҘ№еңЁеҲҖй”ӢиҗҪдёӢзҡ„еҲ№йӮЈзҢӣ然зқҒзңјпјҢзңёе…үеҶ·еҶҪеҰӮйңңпјҢзӣҙзӣҙжңӣеҗ‘жқҘдәәгҖӮ
йӮЈдәәеғөеңЁеҺҹең°гҖӮ
еҮӨжҳӯзј“зј“еқҗиө·пјҢе”Үи§’еҫ®жү¬пјҡвҖңжҺҢжҹңзҡ„пјҢеӨңеҜ’йңІйҮҚпјҢе°ҸеҝғзҒ«ж°”гҖӮвҖқ
еҘ№зҡ„еЈ°йҹідёҚй«ҳпјҢеҚҙеӯ—еӯ—жё…жҷ°гҖӮ
жҺҢжҹңжҸЎзқҖеҢ•йҰ–пјҢеҶ·жұ—йЎәзқҖйўқи§’ж»‘дёӢгҖӮд»–еҗҺйҖҖдёӨжӯҘпјҢж’һеҲ°жЎҢи§’пјҢжІ№зҒҜиҪ»жҷғпјҢеҪұеӯҗеңЁеўҷдёҠеү§зғҲжҠ–еҠЁгҖӮд»–жІЎиҜҙиҜқпјҢиҪ¬иә«жҺЁй—ЁиҖҢеҮәпјҢи„ҡжӯҘеҮҢд№ұгҖӮ
第дәҢж—ҘпјҢжҺҢжҹңжҖҒеәҰеҸҳдәҶгҖӮ
д»–дҫқж—§еҶ·и„ёзӣёеҜ№пјҢеҚҙз ҙдҫӢе‘ҪеҘ№жҠ„еҪ•йҖҒеҫҖиҙөж—ҸеәңйӮёзҡ„жұӮиҚҜжё…еҚ•гҖӮзәёйЎөйҖ’жқҘж—¶пјҢеҮӨжҳӯжҢҮе°–иҪ»жҠҡиЎЁйқўпјҢдёҖиЎҢеӯ—иҝ№жҳ е…Ҙи„‘жө·вҖ”вҖ”вҖңйӣӘеҝғе…°дёүй’ұпјҢдёүе№ҙз”ҹпјҢеёҰйңІйҮҮвҖқгҖӮ
еҘ№еҝғдёӯдёҖжІүгҖӮ
йңңеҺҹеҹҺең°еӨ„еҢ—еўғпјҢж°”еҖҷиӢҰеҜ’пјҢйӣӘеҝғе…°жң¬е°ұзЁҖжңүпјҢиҝ‘дә”е№ҙд»ҺжңӘжңүиҝҮжҲҗж Әи®°еҪ•гҖӮжӯӨиҚҜиӢҘйқһдјӘйҖ пјҢдҫҝжҳҜд»ҺеҲ«еӨ„з§ҳеҜҶиҝҗе…ҘгҖӮжӣҙи№Ҡи··зҡ„жҳҜпјҢеҚ•жҚ®дёҠеҠ зӣ–зҡ„еҚ°йүҙиҫ№зјҳзЈЁжҚҹдёҘйҮҚпјҢдјјжҳҜд»ҝеҲ»гҖӮ
еҘ№дҪҺеӨҙеә”дёӢпјҢжҺҘиҝҮзәёз¬”пјҢдёҖ笔дёҖеҲ’иӘҠеҶҷгҖӮжҠ„иҮіжң«е°ҫж—¶пјҢжҢҮз”ІиҪ»иҪ»еҲ®иҝҮвҖңйӣӘеҝғе…°вҖқдёүеӯ—пјҢе°Ҷеӯ—еҪўеҲ»е…ҘжҢҮз”ІеҶ…дҫ§гҖӮзғ¬еҝғзҒ«йҡҸд№ӢжөҒиҪ¬пјҢзҒјзғ§и®°еҝҶпјҢз•ҷдёӢдёҚеҸҜзЈЁзҒӯзҡ„з—•иҝ№гҖӮ
收е·ҘеҗҺпјҢеҘ№жү¶зқҖй—ЁжЎҶзј“жӯҘиө°еҮәеҗҺе ӮгҖӮжҺҢжҹңз«ҷеңЁжҹңеҸ°еҗҺпјҢзӣ®йҖҒеҘ№зҰ»еҺ»пјҢзңјзҘһйҳҙжІүгҖӮ
еӨңйҮҢпјҢеҮӨжҳӯзӢ¬еқҗжҲҝдёӯгҖӮзӘ—еӨ–ж— жңҲпјҢеұӢеҶ…жјҶй»‘дёҖзүҮпјҢеҘ№ж‘ҠејҖжүӢжҺҢпјҢжҺҢеҝғжіӣиө·дёҖдёқеҫ®дёҚеҸҜеҜҹзҡ„жё©зғӯгҖӮзғ¬еҝғзҒ«еңЁиЎҖи„үдёӯйқҷйқҷжёёиө°пјҢеҰӮеҗҢиӣ°дјҸзҡ„иӣҮгҖӮ
еҘ№зҹҘйҒ“пјҢиҮӘе·ұе·Іиў«зӣҜдёҠгҖӮ
дҪҶйӮЈеҸҲеҰӮдҪ•пјҹ
еҘ№дёҚйңҖиҰҒиў«дҝЎд»»пјҢеҸӘйңҖиҰҒиў«еҲ©з”ЁгҖӮ
еҸӘиҰҒиғҪжҺҘи§ҰеҲ°йӮЈдәӣйҖҒеҫҖиҙөж—Ҹеәңдёӯзҡ„иҚҜеҚ•пјҢеҘ№е°ұиғҪйЎәи—Өж‘ёз“ңпјҢжүҫеҲ°еҪ“е№ҙиЎҖжЎҲзҡ„иӣӣдёқ马иҝ№гҖӮ
зҝҢж—ҘеҚҲж—¶пјҢжҺҢжҹңеҸ«еҘ№иҝӣеұӢгҖӮ
вҖңжҳҺж—ҘжңүдёҖеңәиҢ¶е®ҙпјҢеҹҺдёӯеҮ дҪҚиҙөдәәиҰҒжқҘеҸ–иҚҜгҖӮдҪ йҡҸжҲ‘еҺ»гҖӮвҖқ
еҮӨжҳӯдҪҺеӨҙпјҢжүӢжҢҮиҪ»иҪ»ж‘©жҢІиў–дёӯж®ӢзҺүд»ӨпјҢжҜ”еҲ’жүӢеҠҝиЎЁзӨәжҳҺзҷҪгҖӮ
вҖңдҪ иҷҪзңӢдёҚи§ҒпјҢдҪҶжүӢи„ҡеҲ©зҙўпјҢеҸӘз®ЎеңЁж—Ғж·»ж°ҙйҖ’зӣҸпјҢиҺ«иҰҒеӨҡиЁҖгҖӮвҖқ
еҘ№зӮ№еӨҙгҖӮ
жҺҢжҹңзӣҜзқҖеҘ№зңӢдәҶи®ёд№…пјҢз»ҲдәҺејҖеҸЈпјҡвҖңжҲ‘дёҚз®ЎдҪ жҳҜд»Җд№ҲдәәпјҢд№ҹдёҚжғізҹҘйҒ“дҪ жҳЁжҷҡдёәдҪ•зқҒзңјгҖӮеҸӘиҰҒдҪ е®үеҲҶеҒҡдәӢпјҢжҲ‘дёҚй—®иҝҮеҺ»гҖӮвҖқ
еҮӨжҳӯеҳҙи§’еҫ®еҠЁпјҢйңІеҮәдёҖдёқжё©йЎә笑ж„ҸгҖӮ
еҘ№жҠ¬иө·жүӢпјҢзј“зј“жҜ”еҲ’пјҡеҸӘжұӮе®№иә«д№ӢеӨ„гҖӮ
жҺҢжҹңеҶ·е“јдёҖеЈ°пјҢиҪ¬иә«жӢЁеј„иҙҰеҶҢгҖӮ
еҮӨжҳӯйҖҖдёӢж—¶пјҢи„ҡжӯҘдҫқж—§зј“ж…ўпјҢиғҢеҪұеҚ•и–„гҖӮеҸҜе°ұеңЁеҘ№жҠ¬и„ҡи·ЁеҮәй—Ёж§ӣзҡ„еҲ№йӮЈпјҢе·Ұи„ҡйһӢе°–еҫ®еҫ®зҝҳиө·пјҢйңІеҮәйһӢеә•еӨ№еұӮзҡ„дёҖи§’жҡ—зәўвҖ”вҖ”йӮЈжҳҜеҘ№жҳЁеӨңж–°зјқе…Ҙзҡ„дёқзәҝпјҢйўңиүІжӣҙж·ұпјҢз»“жі•дёҚеҗҢпјҢдёүеңҲеӣһзә№дёӯеӨҡдәҶдёҖйҒ“йҖҶжҠҳпјҢиұЎеҫҒзҢҺзү©е·Іе…Ҙз¬јгҖӮ
еҘ№еӣһеҲ°жҲҝдёӯпјҢеҸ–еҮәи—ҸеңЁйһӢеә•зҡ„жҜ’дёёпјҢиҪ»иҪ»ж‘©жҢІиЎЁйқўгҖӮж–ӯйӯӮйңІе°ҡжңӘеҗҜз”ЁпјҢдҪҶеҘ№е·Іе—…еҲ°йҳҙи°Ӣзҡ„ж°”жҒҜгҖӮ
иҚҜзӮүж—Ғзҡ„зҒ°зғ¬иҝҳжңӘжё…пјҢж®Ӣз•ҷзҡ„иҚҜжёЈеңЁи§’иҗҪе ҶжҲҗе°Ҹе ҶгҖӮеҘ№и№ІдёӢиә«пјҢз”ЁжҢҮе°–жӢЁејҖиЎЁеұӮпјҢеә•дёӢе°ҡеӯҳдёҖзӮ№жңӘзҮғе°Ҫзҡ„иөӨйіһж №зўҺеұ‘пјҢжіӣзқҖиҜЎејӮзҡ„жҡ—зәўиүІгҖӮ
еҘ№е°ҶзўҺеұ‘收е…Ҙе°Ҹ瓷瓶пјҢеЎһиҝӣиў–иўӢгҖӮ
иҝҷиҚҜдёҚиҜҘеҰӮжӯӨзЁіе®ҡгҖӮжӯЈеёёж·¬зӮјеҗҺеә”е‘ҲзҒ°зҷҪпјҢиҖҢйқһжҫ„зәўгҖӮйҷӨйқһвҖҰвҖҰжңүдәәеҲ»ж„Ҹи°ғж•ҙзҒ«еҖҷпјҢдҝқз•ҷжҜ’жҖ§гҖӮ
еҘ№й—ӯзңјйқҷй»ҳзүҮеҲ»пјҢзғ¬еҝғзҒ«еңЁдҪ“еҶ…зј“зј“жөҒиҪ¬пјҢеҗһдёӢжҳЁж—ҘжҺҢжҹңйҖјиҝ‘ж—¶зҡ„жқҖж„ҸпјҢд№ҹеҗһдёӢдәҶд»ҠжҷЁд»–йҖ’жқҘиҚҜеҚ•ж—¶йӮЈдёҖзһ¬зҡ„иҜ•жҺўгҖӮжҜҸдёҖж¬ЎжҒ¶ж„Ҹйқ иҝ‘пјҢйғҪи®©иҝҷзј•зҒ«жӣҙзӮҪдёҖеҲҶгҖӮ
第дёүж—Ҙжё…жҷЁпјҢеӨ©еҲҡи’ҷдә®гҖӮ
еҮӨжҳӯжҚўдёҠж•ҙжҙҒеёғиЎЈпјҢеҸ‘дёқз”ЁжһҜи—Өжқҹиө·пјҢйқўе®№е№ійқҷгҖӮжҺҢжҹңе·ІеңЁй—ЁеҸЈзӯүеҘ№пјҢжүӢдёӯжҸҗзқҖдёҖеҸӘйӣ•иҠұжңЁеҢЈгҖӮ
вҖңиө°еҗ§гҖӮвҖқ
еҘ№жү¶зқҖеўҷж №зј“жӯҘеүҚиЎҢпјҢзңӢдјјдҫқиө–зҶҹжӮүи·ҜзәҝпјҢе®һеҲҷжҜҸдёҖжӯҘйғҪзІҫеҮҶиё©еңЁи®°еҝҶдёӯж Үи®°зҡ„дҪҚзҪ®гҖӮи·ҜиҝҮиҚҜжҹңж—¶пјҢеҘ№жҢҮе°–иҪ»жҺ иҝҮ第дёүж јжҠҪеұүпјҢйӮЈйҮҢи—ҸзқҖжҳЁеӨңеҘ№еҒ·еҒ·ж”ҫе…Ҙзҡ„еҸҰдёҖ瓶иҚҜзІүгҖӮ
马иҪҰеҒңеңЁй—ЁеӨ–гҖӮ
жҺҢжҹңе…ҲдёҠдәҶиҪҰпјҢеҘ№йҡҸеҗҺи·ҹдёҠпјҢеқҗеңЁи§’иҗҪгҖӮжңЁеҢЈж”ҫеңЁдёӨдәәд№Ӣй—ҙпјҢеҢЈйқўеҲ»зқҖз№ҒеӨҚиҠұзә№пјҢдёӯеӨ®дёҖжһҡй“ңжүЈжіӣзқҖеҶ·е…үгҖӮ
еҮӨжҳӯеһӮйҰ–пјҢеҸіжүӢжӮ„жӮ„жҺўе…Ҙиў–дёӯпјҢжҸЎдҪҸж®ӢзҺүд»ӨгҖӮ
иҪҰиҪ®еҗҜеҠЁпјҢзўҫиҝҮйқ’зҹіи·ҜйқўпјҢеҸ‘еҮәжІүй—·еЈ°е“ҚгҖӮ
еҘ№еҝҪ然жҠ¬еӨҙпјҢз©әиҢ«еҸҢзңјжңӣеҗ‘еүҚж–№пјҢеғҸжҳҜж„ҹзҹҘеҲ°дәҶд»Җд№ҲгҖӮ
вҖңжҖҺд№ҲдәҶпјҹвҖқжҺҢжҹңй—®гҖӮ
еҘ№жІЎеӣһзӯ”пјҢеҸӘжҳҜзј“зј“жҠ¬иө·жүӢпјҢжҢҮеҗ‘иҝңеӨ„иЎ—и§’дёҖй—ӘиҖҢиҝҮзҡ„й»‘иЎЈдәәеҪұгҖӮ
йӮЈдәәз«ҷеңЁе··еҸЈпјҢеёҪжӘҗеҺӢеҫ—еҫҲдҪҺпјҢжүӢдёӯжҸЎзқҖдёҖиҠӮж–ӯиЈӮзҡ„зәўзәҝпјҢдёҺеҘ№жҳЁж—Ҙж–ӯжҺүзҡ„йӮЈдёҖж №пјҢеҮ д№ҺдёҖжЁЎдёҖж ·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ө¶е°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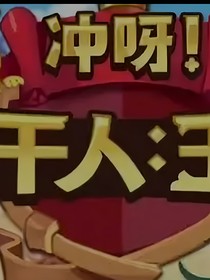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йҘје№ІдәӢи®°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еңЁејӮз•Ңзә№д№қйҫҷжӢүжЈә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Ҫ’е°ҳеҲӣдё–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家з”өи§ҶжңәиғҪз©ҝи¶ҠдёҮз•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