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жҲ‘йҶ’иҝҮжқҘж—¶пјҢзӘ—еӨ–зҡ„йҳіе…үе·Із»Ҹж–ңж–ңең°жү“еңЁең°жқҝдёҠпјҢеңЁйҷҲж—§зҡ„ең°жҜҜдёҠжҠ•дёӢеҮ йҒ“ж–‘й©ізҡ„е…үеҪұгҖӮжҸүдәҶжҸүй…ёиғҖзҡ„еӨӘйҳіз©ҙпјҢи„‘еӯҗйҮҢиҝҳж®Ӣз•ҷзқҖжҳЁеӨңйӮЈеңәжЁЎзіҠзҡ„жўҰпјҢжҢҮе°–дјјд№ҺиҝҳиғҪи§ҰеҲ°йӮЈеҶ°еҮүзҡ„жіӘз—•гҖӮиҪ¬еӨҙзңӢеҗ‘еҲҡеқҗиө·иә«зҡ„зҺ„йқ’пјҢд»–жӯЈдҪҺеӨҙжҸүзқҖеҸ‘йә»зҡ„и…ҝпјҢйўқеүҚзҡ„зўҺеҸ‘д№ұзіҹзіҹең°жҗӯзқҖпјҢзңјдёӢиҝҳжңүж·Ўж·Ўзҡ„йқ’й»‘гҖӮжҲ‘дјёиҝҮжүӢпјҢиҪ»иҪ»жӢҚдәҶжӢҚд»–зҡ„иғіиҶҠпјҡвҖңиө°пјҢжҚўдёӘең°ж–№зқЎпјҢе’ұеҺ»е®¶еҘҪзӮ№зҡ„й…’еә—гҖӮвҖқ
зҺ„йқ’й—»иЁҖзҡұдәҶзҡұзңүпјҢйӮЈйҒ“зңүеӨҙжӢ§жҲҗдёӘж·ұж·ұзҡ„е·қеӯ—пјҢд»–дёӢж„ҸиҜҶең°дјёжүӢж‘ёдәҶж‘ёиЈӨе…ңпјҢжҢҮе°–еңЁи–„и–„зҡ„еёғж–ҷдёҠжҚҸдәҶжҚҸпјҢиҜӯж°”йҮҢеёҰзқҖзӮ№жҳҺжҳҫзҡ„зҠ№иұ«пјҡвҖңе’ұжө‘иә«дёҠдёӢе°ұеү©дёҖеҚғеқ—дәҶпјҢеҘҪзӮ№зҡ„й…’еә—дёҖжҷҡе°ұеҫ—еҮ зҷҫеқ—пјҢиҝҷй’ұдёҖиҠұпјҢдёҮдёҖеҗҺйқўеҮ еӨ©иҝһйҰ’еӨҙйғҪеҗғдёҚиө·е’ӢеҠһпјҹвҖқд»–иҜҙзқҖпјҢи§Ҷзәҝжү«иҝҮжЎҢдёҠз©әдәҶзҡ„еҢ…еӯҗиўӢпјҢе–үз»“жӮ„жӮ„еҠЁдәҶеҠЁгҖӮ
жҲ‘еҝҚдёҚдҪҸ笑дәҶ笑пјҢдјёжүӢжӢҚдәҶжӢҚд»–зҡ„иӮ©иҶҖпјҢжҺҢеҝғиғҪи§ҰеҲ°д»–иӮ©иҶҖдёҠз»“е®һзҡ„иӮҢиӮүпјҡвҖңжҖ•е•Ҙпјҹе’ұдјҡзңӢйЈҺж°ҙгҖҒиғҪжҺҗдјҡз®—гҖҒиҝҳиғҪжҚүй¬јй©ұйӮӘпјҢиҝҷиә«жң¬дәӢеңЁиә«пјҢиҝҳж„ҒжҢЈдёҚзқҖй’ұпјҹвҖқйҳіе…үйҖҸиҝҮзӘ—жҲ·иҗҪеңЁжҲ‘жүӢиғҢдёҠпјҢжҡ–иһҚиһҚзҡ„пјҢеҖ’и®©еҝғйҮҢд№ҹз”ҹеҮәеҮ еҲҶеә•ж°”гҖӮ
зҺ„йқ’ж’ҮдәҶж’ҮеҳҙпјҢеҳҙи§’еҫҖдёӢж’ҮеҮәдёӘж— еҘҲзҡ„еј§еәҰпјҢд»–жҠ¬жүӢжҠ“дәҶжҠ“еӨҙеҸ‘пјҢжҠҠжң¬е°ұд№ұзіҹзіҹзҡ„еӨҙеҸ‘жҸүеҫ—жӣҙеғҸйёЎзӘқпјҡвҖңеҸҜе’ұи·‘дәҶеӨ§еҚҠдёӘжңҲпјҢе°ұжҲҗдәҶжқҺеӣӣе’Ңжһ—е©үжҹ”йӮЈдёҖ笔з”ҹж„ҸгҖӮжҲ‘зңӢе•ҠпјҢиҝҳжҳҜд№–д№–еӣһеӨ©жЎҘеә•дёӢи№ІзӮ№еҗ§пјҢиҮіе°‘йӮЈе„ҝдәәеӨҡпјҢжҖ»иғҪзў°дёҠдёӘдҝЎиҝҷдёӘзҡ„гҖӮвҖқд»–иҜҙзқҖпјҢејҜи…°жҠҠең°дёҠзҡ„иғҢеҢ…жӢҪиө·жқҘпјҢжӢҚдәҶжӢҚдёҠйқўзҡ„зҒ°е°ҳпјҢиғҢеҢ…еёҰеӯҗдёҠзҡ„зәҝи„ҡйғҪзЈЁеҫ—иө·дәҶжҜӣгҖӮ
жҲ‘жғідәҶжғіпјҢд»–иҜҙзҡ„еҖ’д№ҹжҳҜе®һжғ…пјҢдҫҝжІЎеҸҚй©іпјҢиө·иә«ејҖе§Ӣ收жӢҫдёңиҘҝгҖӮеҮ 件жҚўжҙ—иЎЈзү©еҸ еҫ—ж•ҙж•ҙйҪҗйҪҗеЎһиҝӣиғҢеҢ…пјҢзҷҪзӢҗзӢёжӯӨеҲ»жӯЈиң·еңЁжһ•еӨҙиҫ№жү“зӣ№гҖӮ
жҲ‘们еҮәй—ЁжӢҰдәҶиҫҶеҮәз§ҹиҪҰпјҢжҠҘдәҶеӨ©жЎҘзҡ„ең°еқҖгҖӮиҪҰзӘ—еӨ–зҡ„иЎ—жҷҜйЈһйҖҹеҖ’йҖҖпјҢи·Ҝиҫ№зҡ„е°Ҹиҙ©жҺЁзқҖиҪҰеҸ«еҚ–пјҢйӘ‘зқҖиҮӘиЎҢиҪҰзҡ„дәәеҸ®й“ғй“ғең°жҢүзқҖиҪҰй“ғпјҢдёҖжҙҫзғӯй—№зҡ„зғҹзҒ«ж°”гҖӮеҲ°дәҶең°ж–№пјҢеҲҡеңЁеӨ©жЎҘе…ҘеҸЈз«ҷзЁіи„ҡи·ҹпјҢзҺ„йқ’е°ұжё…дәҶжё…е—“еӯҗпјҢйӮЈеЈ°йҹіеёҰзқҖзӮ№еҲ»ж„Ҹзҡ„жҙӘдә®пјҢд»–еӯҰзқҖж—Ғиҫ№зӣёеЈ«зҡ„ж ·еӯҗпјҢеҸҢжүӢеҫҖиў–еӯҗйҮҢдёҖжӢўпјҢеҗҶе–қиө·жқҘпјҡвҖңжҚүй¬јз®—е‘ҪзңӢйЈҺж°ҙе’ҜвҖ”вҖ”дёҚеҮҶдёҚиҰҒй’ұвҖ”вҖ”вҖқ
еҸҜе–ҠдәҶеҚҠеӨ©пјҢе—“еӯҗйғҪеҝ«е–Ҡе“‘дәҶпјҢе‘ЁеӣҙдәәжқҘдәәеҫҖпјҢи„ҡжӯҘеҢҶеҢҶгҖӮжңүжҸҗзқҖиҸңзҜ®еӯҗзҡ„еӨ§еҰҲпјҢи·ҜиҝҮж—¶ж–ңзңјзһҘдәҶжҲ‘们дёҖдёӢпјҢеҳҙйҮҢеҳҹеӣ”зқҖвҖңе№ҙиҪ»иҪ»дёҚеӯҰеҘҪвҖқпјӣжңүиғҢзқҖд№ҰеҢ…зҡ„еӯҰз”ҹпјҢеҘҪеҘҮең°зңӢдәҶдёӨзңјпјҢе°ұиў«еҗҢиЎҢзҡ„дјҷдјҙжӢүзқҖи·‘ејҖдәҶпјӣиҝҳжңүз©ҝзқҖиҘҝиЈ…зҡ„дёҠзҸӯж—ҸпјҢи„ҡжӯҘдёҚеҒңпјҢд»ҝдҪӣжҲ‘们е°ұжҳҜи·Ҝиҫ№зҡ„зҹіеӨҙеӯҗпјҢиҝһдёӘеӨҡдҪҷзҡ„зңјзҘһйғҪжҮ’еҫ—з»ҷгҖӮеӨ§еӨҡеҸӘжҳҜзһҘжҲ‘们дёҖзңје°ұиө°дәҶпјҢиҝһдёӘй©»и¶ізҡ„йғҪжІЎжңүгҖӮ
жҲ‘жү“йҮҸдәҶдёҖеңҲпјҢеҸ‘зҺ°иҝҷеӨ©жЎҘеә•дёӢдәәзЎ®е®һдёҚе°‘пјҢеҸ°йҳ¶дёҠеқҗж»ЎдәҶж‘Ҷж‘Ҡзҡ„пјҢеҚ–иўңеӯҗзҡ„гҖҒдҝ®жүӢжңәзҡ„гҖҒиҝҳжңүеҘҪеҮ дёӘи·ҹжҲ‘们дёҖж ·жҢӮзқҖвҖңз®—е‘ҪвҖқзүҢеӯҗзҡ„гҖӮеҘҪеӨҡдәәжүӢйҮҢжҚҸзқҖзҡұе·ҙе·ҙзҡ„й’һзҘЁпјҢзңјзҘһеңЁеҗ„дёӘж‘ҠдҪҚеүҚйҖЎе·ЎпјҢеҸҜеӨ§еӨҡйғҪеҫҖйӮЈдәӣзңӢиө·жқҘе№ҙзәӘеӨ§зҡ„е…Ҳз”ҹи·ҹеүҚеҮ‘гҖӮ
вҖңзңӢжқҘиҝҳжҳҜе№ҙиҪ»еҗғдәҸе•ҠгҖӮвҖқжҲ‘дҪҺеЈ°и·ҹзҺ„йқ’еҝөеҸЁпјҢдёӢе·ҙеҫҖж—Ғиҫ№еҠӘдәҶеҠӘпјҢвҖңдҪ зңӢйӮЈдәӣиҖҒе…Ҳз”ҹпјҢиғЎеӯҗиҠұзҷҪпјҢз©ҝзқҖеҜ№иҘҹиӨӮеӯҗпјҢеҫҖйӮЈе„ҝдёҖеқҗе°ұйҖҸзқҖиӮЎвҖҳжңүйҒ“иЎҢвҖҷзҡ„еҠІе„ҝпјҢе№ҙзәӘи¶ҠеӨ§и¶ҠеҗғйҰҷгҖӮвҖқ
зҺ„йқ’д№ҹзӮ№зӮ№еӨҙпјҢи§ҶзәҝйЎәзқҖжҲ‘зӨәж„Ҹзҡ„ж–№еҗ‘жү«иҝҮеҺ»пјҢиҗҪеңЁж—Ғиҫ№дёҖдҪҚиҖҒиҖ…иә«дёҠгҖӮйӮЈиҖҒеӨҙеӨҙеҸ‘зҷҪеҫ—еғҸйӣӘпјҢжўіеҫ—дёҖдёқдёҚиӢҹпјҢйј»жўҒдёҠжһ¶зқҖеүҜиҖҒиҠұй•ңпјҢжӯЈжӢүзқҖдёӘдәҢеҚҒжқҘеІҒзҡ„е№ҙиҪ»дәәиҜҙеҫ—иө·еҠІгҖӮд»–жүӢжҢҮеңЁе№ҙиҪ»дәәи„ёдёҠзӮ№дәҶзӮ№пјҢеЈ°йҹідёҚй«ҳдёҚдҪҺпјҢеҚҙеҲҡеҘҪиғҪи®©е‘ЁеӣҙеҮ дёӘдәәеҗ¬и§ҒпјҡвҖңжҲ‘зңӢдҪ еҚ°е ӮеҸ‘й»‘пјҢйҡҗйҡҗйҖҸзқҖиӮЎжҷҰж°”пјҢиҝ‘жңҹжҒҗжңүиЎҖе…үд№ӢзҒҫе•ҠпјҒиҪ»еҲҷж‘”ж–ӯи…ҝпјҢйҮҚеҲҷвҖҰвҖҰвҖқд»–ж•…ж„ҸйЎҝдәҶйЎҝпјҢзңӢйӮЈе№ҙиҪ»дәәи„ёиүІеҸ‘зҷҪпјҢжүҚж…ўжӮ жӮ ең°д»ҺжҖҖйҮҢжҺҸеҮәйҒ“й»„з¬ҰпјҢвҖңд№°жҲ‘иҝҷйҒ“з¬ҰпјҢиҙҙиә«жҲҙзқҖпјҢдҝқдҪ е№іе®үж— дәӢпјҒвҖқ
е№ҙиҪ»дәәиў«еҗ“еҫ—еҳҙе”ҮйғҪе“Ҷе—ҰдәҶпјҢиө¶зҙ§д»Һе…ңйҮҢжҺҸеҮәй’ұпјҢеҸҢжүӢжҺҘиҝҮйӮЈйҒ“з¬ҰпјҢе°Ҹеҝғзҝјзҝјең°жҸЈиҝӣеҶ…иЎЈеҸЈиўӢпјҢдёҙиө°ж—¶иҝҳдёҖдёӘеҠІең°дҪңжҸ–йҒ“и°ўгҖӮ
еҶҚеҫҖж—Ғиҫ№зңӢпјҢиҝҳжңүдёӘ算姻зјҳзҡ„иҖҒеӨҙпјҢйқўеүҚж‘ҶзқҖдёӘеҶҷзқҖвҖңеӨ©е®ҡ姻зјҳвҖқзҡ„жңЁзүҢпјҢд»–жӯЈжӢҝзқҖйҒ“зәўз¬Ұи·ҹдёҖдёӘе°Ҹдјҷеӯҗеҗ№еҳҳпјҢе”ҫжІ«жҳҹеӯҗйғҪеҝ«е–·еҲ°е°Ҹдјҷеӯҗи„ёдёҠдәҶпјҡвҖңжҲ‘иҝҷз¬ҰзҒөеҫ—еҫҲпјҢд№ғжҳҜз”Ёзҷҫе№ҙжЎғжңЁеҝғзӮјеҢ–зҡ„пјҢжҲҙеңЁиә«дёҠпјҢдҝқиҜҒж–№еңҶеҚҒйҮҢзҡ„姑еЁҳ们йғҪиғҪй—»еҲ°дҪ иә«дёҠзҡ„вҖҳ姻зјҳж°”вҖҷпјҢеҜ№дҪ дёҖи§Ғй’ҹжғ…пјҢиҰҒдёҚиҰҒжқҘдёҖеј пјҹвҖқ
йӮЈе°Ҹдјҷеӯҗзңјзқӣзһ¬й—ҙдә®дәҶпјҢеғҸиў«зӮ№зҮғзҡ„зҒ«жҠҠпјҢеҝҷдёҚиҝӯең°иҝһиҝһзӮ№еӨҙпјҡвҖңиҰҒпјҒиҰҒпјҒз»ҷжҲ‘жқҘдёҖеј пјҒвҖқ
иҖҒеӨҙж…ўжӮ жӮ ең°жҚ»зқҖиғЎеӯҗпјҢдјёеҮәдә”ж №жүӢжҢҮжҷғдәҶжҷғпјҡвҖңдә”зҷҫгҖӮвҖқ
йӮЈе№ҙиҪ»дәәжғійғҪжІЎжғіпјҢз«Ӣ马д»Һй’ұеҢ…йҮҢжҠҪеҮәдә”еј зҷҫе…ғеӨ§й’һйҖ’иҝҮеҺ»пјҢеҸҢжүӢжҚ§зқҖйӮЈйҒ“з¬ҰпјҢе®қиҙқдјјзҡ„жҸЈиҝӣе…ңйҮҢпјҢиҪ¬иә«ж—¶и„ҡжӯҘйғҪеёҰзқҖйӣҖи·ғпјҢе–ңж»Ӣж»Ӣең°и·‘дёӢдәҶеӨ©жЎҘгҖӮ
жҲ‘е’ҢзҺ„йқ’еҜ№и§ҶдёҖзңјпјҢйғҪд»ҺеҜ№ж–№зңјйҮҢзңӢеҲ°дәҶж— еҘҲгҖӮзҺ„йқ’еҫҖең°дёҠе•җдәҶеҸЈе”ҫжІ«пјҢеҺӢдҪҺеЈ°йҹіеҳҖе’•дәҶдёҖеҸҘпјҡвҖңеӮ»зјәгҖӮвҖқйӮЈеЈ°йҹійҮҢеёҰзқҖзӮ№ж„Өж„ӨдёҚе№іпјҢеҸҲжңүзӮ№жҒЁй“ҒдёҚжҲҗй’ўгҖӮжҲ‘д№ҹеҝҚдёҚдҪҸж‘Үж‘ҮеӨҙпјҢзңӢжқҘиҝҷеӨ©жЎҘеә•дёӢзҡ„з”ҹж„ҸпјҢдёҚе…үиҰҒйқ жң¬дәӢпјҢиҝҳеҫ—йқ вҖңжј”жҠҖвҖқпјҢжІЎйӮЈд№ҲеҘҪеҒҡе•ҠгҖӮйЈҺд»ҺжЎҘжҙһPеҗ№иҝҮпјҢеёҰзқҖзӮ№еҮүж„ҸпјҢжҲ‘жҠҠжҖҖйҮҢзҡ„зҷҪзӢҗзӢёжҠұзҙ§дәҶдәӣпјҢе°Ҹ家-дјҷдёҚзҹҘдҪ•ж—¶йҶ’дәҶпјҢжӯЈз”Ёи„‘иўӢи№ӯзқҖжҲ‘зҡ„жүӢпјҢеғҸжҳҜеңЁе®үж…°жҲ‘гҖӮ
зӣёе…іжҺЁиҚҗ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ҝғйӯ”еү‘й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ҚҒе…«иӢұйӣҢ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ејҖеұҖй“ёе°ұж— дёҠж №еҹәпјҢжҲ‘й—®йјҺд»ҷи·Ҝпј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жҳҺе •д№қе№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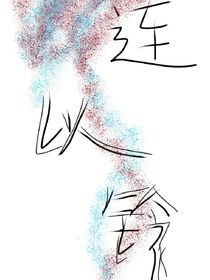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д»Ҙй“ғ
 иҝһиҪҪдёӯ
иҝһиҪҪдё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