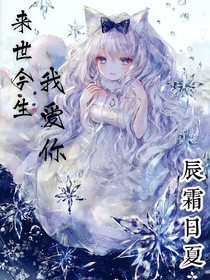第六十五章 (5-1)
自那次近乎粗暴的介入之后,我与温克之间并未发展出寻常意义上充满欢声笑语的亲密友谊。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共生的默契关系。
他没有因我那番关于“雪地撒尿”和“峨眉山猴子”的激烈言论而疏远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刻意的讨好或感恩戴德,他仿佛天生具备一种穿透表象的直觉,自然而然地接纳了我全部的怪异与冰冷,并以一种温和而坚韧的姿态,悄然融入了我那片刻意与世隔绝的精神领地。
我们最常共处的地方,依旧是图书馆那个被我视为“私人避难所”的僻静角落,当我在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或叔本华的“生命意志” 中陷入长达数小时如同深海潜水般的精神冥思时,温克会安静地坐在我对面,翻阅着他带来的关于北欧民间传说或深海生态学的书籍,偶尔抬起眼,用那双冰川蓝的眸子静静地看我一眼。
那目光中没有探究,没有打扰,只有一种近乎守护般的平静。
有时当我从繁复艰深的思辨中挣脱出来,感到一种灵魂层面的虚脱与疏离时,会发现他正望着窗外,淡金色的睫毛在斜阳下泛着柔和的光晕,整个人散发出一种能让最躁动的灵魂也安定下来的静谧气息。
这种无需言语却充满存在感的陪伴,像无声的细雨,悄然滋润着我那片因过度审视人性阴暗而变得荒芜龟裂的心田。
真正让我感到意外乃至一丝震撼的,是温克在音乐领域的非凡造诣。
他并非那种炫技型的演奏者,而是真正与乐器灵魂相通的艺术者,一次他带我去了学院那间坐落于古老钟楼旁,音响 效果宛如中世纪修道院祷告室的旧琴房。
当他的指尖如同被月光亲吻的精灵般,轻柔地落在那架饱经风霜的斯坦威三角钢琴的黑白琴键上,流淌出斯克里亚宾《升D小调练习曲》那神秘而充满灵性追问的旋律时,我第一次被一种超越语言和逻辑的纯粹美感所俘获。
那不具侵略性却直抵灵魂深处的音符,像一双无形而温柔的手,精准地抚平了我内心深处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而产生的褶皱与焦虑。
此后,当我陷入某些过于黑暗或自我缠绕的哲学悖论中而精神濒临枯竭,眉头紧锁时,他就会默契地坐到钢琴前,弹奏一些巴赫的赋格曲或埃里克·萨蒂的空灵之作。
音乐成为了我们之间一种无声语言,有效地平衡了我过于理性的思维惯性,缓解了我那与现实的严重脱节感。
在这段关系中,我始终保持着心智上的绝对主导和情感上的严格节制,我会与他深入探讨柏拉图“洞穴隐喻”在当代信息茧房现象中的映射,会分享我对混沌理论中“蝴蝶效应”与个体命运随机性之间微妙关联的猜想,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他论证过程中出现的逻辑跳跃或证据不足。
他则以其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中特有的对自然律法的敬畏和对简约智慧的追求,时常为我提供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考路径。
我们之间的交流,剥离了所有世俗社交的伪饰与功利性,直达思想与存在的本质,这让我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洁净与深度共鸣。
温克如同映照着雪山倒影的清澈冰湖,不仅映照出我这面镜子的冰冷,更以其本身的纯净,悄然中和着我因映照过多人性阴暗而积累的毒素。
然而,在我现实生活的“冰层”之下,还潜藏着一个完全匿名的“我”。
幻之镜像-d498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来世今生我爱你
- 蓝天画:比起让你们知道我要死?那么我宁愿断绝这场友情关系。东方末:我知道真相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如若不回来,我等你十年,你如若十年不回来,......
- 8.0万字10个月前
- 仙穹传
- 一部爆甜纯爱修仙文!!内含作者自创经典名言!!一定要看
- 0.7万字10个月前
- 血色月光谜案
- 讲的是女主-叶知夏与男主谢知许面对灵异事件重重困难消灭心魔,与女主的记忆找回的故事……
- 0.4万字5个月前
- 女生寝室的逃亡
- 0.2万字5个月前
- 前行—异变
- 关于丧尸的小说,女主通过重生不断壮大队伍,末日生存,异变觉醒异能量,不断斩杀丧尸。
- 1.5万字4个月前
- 灵异事务所档案
- 《灵异事务所》的衍生,一点补充世界观的东西
- 0.4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