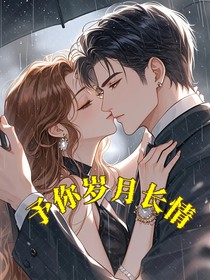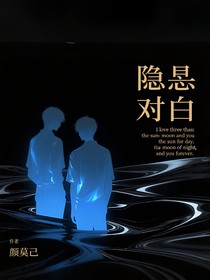第十六章 未送达的信与沉默的守望 (2-1)
陆淮之没有离开纽约。
他无法离开。那座城市里住着他的骨血,住着他亏欠了整个世界也无法弥补的女人。他像一头受伤的狼,舔舐着伤口,却不肯远离自己的巢穴——即使那个巢穴早已将他驱逐。
他没有再试图靠近那所公寓,没有再去早教中心。他知道,任何形式的出现,对Lynette而言都是打扰,都是她口中“提醒痛苦的幽灵”。他不能再让她因他而感到一丝不快。
但他也做不到真正放手。
他在曼哈顿的顶层公寓里,对着巨大的落地窗,一站就是整夜。城市的灯火璀璨如星河,却照不亮他心底的荒芜。他开始疯狂地工作,用近乎自虐的强度处理着跨国事务,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暂时麻痹那无时无刻不在啃噬他的悔恨与思念。
更多的时候,他对着空白的信纸,或者电脑闪烁的光标,试图写下些什么。
道歉?解释?忏悔?
他写了又撕,打了又删。任何语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他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逻辑和口才,在情感的真空中,完全失去了效用。
最终,他放弃了组织华丽的辞藻,只是开始记录。记录他看到的关于小星星的点点滴滴——她在公园滑梯上咯咯大笑的样子,她踮着脚尖试图够超市货架的模样,她抱着那个他送的洋娃娃(他后来才知道她真的收下了)时满足的小表情……他也记录下自己的悔恨,记录下他迟来的、汹涌却无处安放的父爱。
这些文字,支离破碎,情感浓烈到几乎灼伤纸张。它们从未被寄出,只是被他加密存在一个文件夹里,命名为《未送达的信》。
他的行动,也从笨拙的物质补偿,转向了更沉默、更迂回的方式。
他通过数层中间人,联系上了林肯中心艺术节的主要赞助商之一,以匿名的方式,为那个名为《基石》的、尚在筹备中的舞剧项目,提供了一笔不设任何条件、不要求回报的巨额资金支持,唯一的要求是“确保艺术家的创作自由”。
他聘请了纽约最好的、同时也是最低调的私家看护,伪装成社区志愿者,定期关注Lynette母女所住公寓楼的安全与公共设施维护,确保她们生活环境的基本舒适与安全,却又绝不会让她们察觉到任何异常。
他甚至开始学习儿童心理学,了解三岁幼儿的生长发育特点,偷偷查阅了无数关于单亲家庭孩子情感需求的资料。他像一个最用功的学生,恶补着所有他缺席的、关于父亲身份的课程。
这些行动,依旧带着陆淮之式的、习惯于用资源和手段解决问题的烙印,但内核却悄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不再是试图掌控的介入,而是一种……卑微的、小心翼翼的守护。他不再期望被看见,被感激,他只希望她们能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
---
Lynette的生活,似乎真的回归了平静。
小星星的病彻底好了,又恢复了活蹦乱跳的样子。林肯中心艺术节的筹备进展顺利,那笔“匿名赞助”解决了她最大的资金困扰,让她可以更纯粹地投入到创作中。《基石》的编舞日趋成熟,她将所有的情感——离乡背井的孤独、养育女儿的艰辛、挣脱过往的决绝、以及重建自我的力量——都倾注其中。
只是,偶尔,在深夜,当她结束一天的工作,看着身边女儿恬静的睡颜时,陆淮之那张苍白而痛苦的脸,会不受控制地闯入她的脑海。
他站在病房门口,如同被遗弃的影子。
他听到驱逐时,眼中那一闪而过的、近乎绝望的碎裂感。
他离开时,那沉重得仿佛背负着整个世界的背影。
碎月成诗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爱的靠近
- 1.0万字9个月前
- 予你岁月长情
- 乡野丫头替嫁成了京都二爷的小娇妻,两人互相看不顺眼,在这闹剧中,两个人暗生情愫……
- 2.9万字8个月前
- 穿越之扭转炮灰白月光人生
- 【单男主+发疯+白月光文学+不带脑甜宠文】林沅穿越进一本古早言情小说中的作死白月光后发现为什么故事情节根本不一样?不是说好了作死白月光,为什......
- 0.4万字4个月前
- 尘埃里的阳光
- 《尘埃里的光》讲述了出身偏远山村的少年陈默,在贫困中挣扎着走出大山,从工地苦力到写字楼勤杂工,再到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的成长历程。他的人生轨迹......
- 1.0万字4个月前
- 月光烫红了狼耳朵
- 在这座连微笑都被规定的小镇上,昭临从未想过,一个暴雨夜敲开家门的狼人家族,会成为她生命里最温暖的意外。初遇时,小狼人云朗缩在墙角,浅棕色的狼......
- 7.0万字4个月前
- 隐恳对白
- 枫辞忆十六岁生日那天,奔回家时没看到门口等他的妈妈,只有冲天的浓烟和议论的人群。别墅在火里蜷成一团,父母再也没出来。十六岁的他搬去奶奶家,奶......
- 11.7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