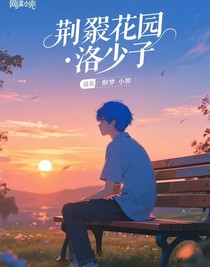第二十五章 阁楼旧物里的墨香,与砚台边的光阴 (2-1)
入夏的蝉鸣刚起时,林深在老宅阁楼的角落发现了个落满灰尘的樟木箱。箱子上着把黄铜锁,锁身爬满青绿色的铜锈,却在锁孔周围留着圈常被摩挲的亮痕——想来是当年常被人打开的缘故。他费了些力气才撬开锁扣,一股混着墨香、樟脑和旧纸的气息扑面而来,像有人在陈年的时光里撒了把晒干的桂花,清冽又温厚。
沈念安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上来时,正看见林深蹲在箱子前,手里捏着支紫毫笔,笔尖还凝着点未干的墨——那墨竟还带着点湿润的光泽,像是昨天才刚蘸过砚台。“这箱子藏得够深的,”她扶着积灰的横梁站稳,目光扫过箱里的物件,忽然被叠在最上面的宣纸吸引,“这不是沈清沅的字吗?你看这撇捺里的兰草气。”
宣纸是上好的生宣,边缘微微泛黄,上面写着半阙《兰亭集序》,字迹清润如溪,却在“引以为流觞曲水”的“流”字处顿了笔,墨点在纸面上洇出个小小的圆,像滴落在宣纸上的晨露。林深用指尖碰了碰那墨点,竟还能感觉到点微涩的湿度,惊得他赶紧缩回手:“这墨……怎么像刚写的?”
“许是樟木防潮的缘故。”沈念安蹲下身,小心地抽出宣纸下的砚台。那是方端砚,砚池里还盛着小半池墨汁,表面结着层极薄的墨皮,轻轻一吹就散了,露出底下泛着光泽的墨汁,凑近了闻,能嗅到松烟混着麝香的气息——是沈清沅常用的“兰台墨”,当年她总说这墨里掺了晒干的兰草末,写起字来能闻到春山的味道。
砚台边压着本线装的字帖,封皮写着“清沅习字录”,翻开第一页,是陈景明用铅笔写的批注:“三月廿八,清沅写‘之’字总爱把最后一笔拖得太长,像院里垂到水面的柳丝,虽好看,却失了帖里的筋骨。”字迹旁还画了个小小的柳树枝,枝桠上歪歪扭扭挂着个“之”字,显然是在模仿沈清沅的笔锋。
“你看这页,”林深翻到中间,指着沈清沅写的“兰”字,“她把草字头写得像两瓣展开的兰花瓣,下面的‘阑’字竖钩带着点弧度,倒像兰草的茎。”
沈念安凑近了看,果然见那“兰”字透着股草木气,仿佛笔尖落纸时,真有兰草的清香顺着笔锋淌下来。字帖里夹着张极薄的蝉翼纸,上面是陈景明抄的《兰草赋》,字迹比沈清沅的要硬朗些,却在“幽芳自赏”的“赏”字处故意弯了笔,像只展翅的蝴蝶停在纸上——想来是写的时候被沈清沅打趣了,故意画的俏皮话。
箱子底层藏着个竹制的笔帘,摊开来看,里面插着七支笔:狼毫、羊毫、紫毫、兼毫,笔杆都刻着极小的字,分别标着“抄经”“画兰”“题跋”“写信”“记账”“画竹”“点染”。其中支“写信”用的狼毫笔杆上,缠着圈褪色的红绳,绳结处还系着片干花,凑近了看,是片压平的兰草叶,叶脉在阳光下能看得一清二楚。
“这定是陈景明弄的,”沈念安拿起那支笔,笑着说,“上次在沈家老宅看到他们的通信,沈清沅总抱怨写信时笔尖太滑,陈景明就在笔杆上缠了红绳防滑,还说‘这样你握笔时,就像牵着我的手’。”
笔帘底下压着叠信笺,最上面那封写着“景明亲启”,信封上画着朵简笔画的兰草,草叶上站着只歪头的小鸟——是沈清沅的笔迹没错。林深拆开信封,信纸边缘裁得极齐整,显然是用裁纸刀仔细划过的,信里写着:
“昨日试写了你带回来的徽宣,比宣纸更韧些,写‘风’字时能把最后一笔拉得很长,像能卷走院里的落叶。只是砚台里的墨总磨不匀,你说该顺时针磨还是逆时针磨?陈先生说顺时针磨的墨更稠,可我觉得逆时针磨的墨里能看到星子……”
信末画了个小小的砚台,砚池里画着几颗星星,旁边用小字注着:“昨夜磨墨时,砚台里真的映出了星子,你信吗?”
“我信。”林深轻声说,像是在回答当年的沈清沅。他想起小时候在爷爷的书房,也曾在磨墨时看砚池里的星子,那时总觉得是墨里的银粉在发光,长大后才明白,那是心里的光落在了墨里。
槐安遗珠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震惊!伍六七穿越了!
- 新来的小作者,文笔不怎么好,请见谅⊹
- 0.4万字9个月前
- 女配她又茶又媚
- 喜欢官配的勿入哈。因为是个搅黄官配的系统(❁´ω`❁)女主人设,绿茶,白莲,不是好人第一世宋墨第二世厉尘澜第三世应渊第四凌霄
- 4.0万字3个月前
- 荆棘花园:洛少爷
- 不剧透
- 2.3万字3个月前
- 我是特种兵之火凤凰一切重来会怎样-d177
- 小说以雷战和叶寸心为主角,讲述了在一切重新开始的情况下,他们的故事将如何展开1。作品属于正剧风格,视角为女主视角。
- 14.4万字3个月前
- 蓦然再回首
- 重生后来到了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家庭,甚至因此转性,离心爱之人几百公里,接下来该怎么办?
- 0.6万字3个月前
- 可恶的恋爱魔女
- 极其普通的主角遇上了自称为恋爱魔女的女孩。女孩表示她可以让主角遇上经典漫画情节,主角当即拜女孩为师,只是,这个漫画情节…………
- 3.3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