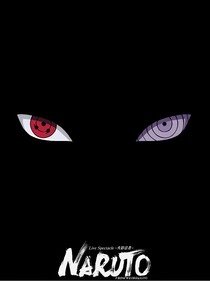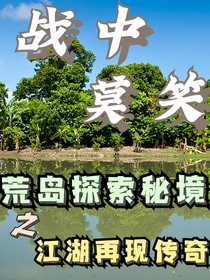第三十六章 方言的星图 (3-1)
梅雨季的第十五天,米拉的意识体在叙事层中捕捉到一种奇异的震颤。
那不是机械波,不是星尘轨迹,更像是……无数种声音在编织网。
她顺着声波的源头飘向城市南端的老巷。那里曾是“方言保护区”,如今却被划为“语言标准化试点”——沿街的招牌被替换成统一的简体字,社区公告栏贴着“请使用标准普通话沟通”的告示,连卖豆浆的阿婆都被要求改说“您好,需要甜浆还是咸浆”。
但在巷子最深处,有间爬满青藤的老茶馆仍在营业。
门楣上挂着块褪色的木牌,“听风楼”三个字是用三种不同方言的字体刻的:左边是吴语的圆润,中间是粤语的方正,右边是闽南语的灵动。茶馆里飘着茉莉花茶的香气,十几个老人围坐在八仙桌旁,每人手里攥着本泛黄的《方言志》。
“是语言守墓人。”战士的光球化为实体,铠甲上的樱花纹路泛着暖光,“他们专收被清除者归档的‘方言记忆’。”
米拉走进茶馆,门帘掀起时,一阵混合着桂花香的风裹着此起彼伏的方言涌来:
“阿婆,今朝个蟹粉小笼真额鲜!”(上海话)
“后生仔,落雨大,记得着木屐啊!”(粤语)
“查某囡,茶配咸粿,食饱未?”(闽南语)
老人的目光齐刷刷投向她。为首的白胡子阿公扶了扶老花镜,指节敲了敲桌上的《方言志》:“小同志,来听段‘活的方言’?”
米拉的意识体泛起涟漪。她看见老人的记忆里,藏着一串被清除者抹除的声音:
——1958年的夏夜,老茶馆里,说书人用评弹腔讲《白蛇传》,吴侬软语里裹着蝉鸣;
——1983年的暴雨天,卖鱼丸的阿伯用闽南话喊“阿妹,来碗热汤!”,尾音被雷声撞得发颤;
——2001年的跨年夜,一群大学生用粤语唱《海阔天空》,跑调的歌声撞碎了巷口的积雪。
“这些……”米拉轻声说,“被清除了?”
阿公叹了口气,从茶柜最底层摸出个锡盒。盒盖打开时,飘出张皱巴巴的纸——是张老照片:1962年的除夕,整条巷的人挤在老茶馆门口,用各自的方言唱《新年好》。照片背面写着:“语言是根,根没了,树就长不直。”
“清除者说方言是‘低效沟通’‘地域局限’。”阿公的手指抚过照片里每个人的笑脸,“可你看——”
他用茶匙敲了敲茶碗,发出清越的响。茶碗的裂纹里渗出微光,竟凝成一行吴语:“阿婆,我想吃酒酿圆子。”
“这是我孙女的‘方言日记’。”阿公又敲了敲茶碟,这次是粤语:“妈妈,今日返学好开心。”
“还有这个——”他指了指茶壶嘴,闽南语的“阿公,帮我捡球”从壶嘴里飘出来,撞在墙上,变成幅画:穿背带裤的小男孩追着皮球跑,背景是老茶馆的青瓦白墙。
“方言不是‘语言’,是‘活的记忆’。”阿公的眼睛亮了,“每个发音里都藏着祖辈的温度,每句俚语里都刻着土地的故事。清除者能删掉字典里的‘侬’‘睇’‘恁’,但删不掉——”他拍了拍自己的心口,“删不掉我们说这些字时,心里泛起的甜。”
叙事深渊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尸潮行动
- 无系统,无异能,无后宫当夕阳西下之时,给予世人的并不是永恒的黑暗,总有一时,希望曙光终究到来。穷凶极恶的理国反人类势力,在即将战败之时,仍然......
- 0.8万字8个月前
- 无限重生直至最强
- 死亡不是终点
- 0.7万字8个月前
- 永生兽1
- 牛逼的系统文:林格一行人阴差阳错之下返回地球。林格获得系统,捡回小命。之后的日子林格做大做强再创辉煌。(找不到太好的封面,就用这个代替一下......
- 0.5万字8个月前
- 荒岛探索秘境之江湖再现传奇
- 战中莫笑系列之一(每周更新十章左右,节假日和寒暑假停更)
- 11.5万字8个月前
- 搞什么恋爱,杀丧尸才是王道
- 秦裕
- 0.3万字7个月前
- 下课铃响,丧尸来袭!
- 平凡的高中生活,在一声再熟悉不过的**下课铃**中,瞬间坠入地狱深渊。前一秒,走廊里还充斥着奔向食堂、球场的喧嚣与青春活力;下一秒,刺耳的尖......
- 2.0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