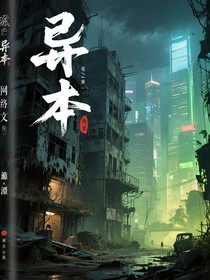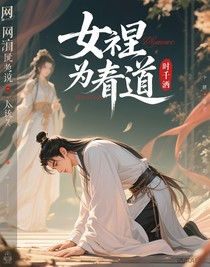年轮深处的光 (2-1)
霜降这天,纸坊的晒架上摆着最后一沓桑皮纸。李雪正用红绸带把纸捆成束,带尾的“始”字被岁月磨得浅了,却在霜气里透出温润的光,像老玉盘上的包浆。赵老师抱着本厚厚的拓字集走进来,封面上的“纸坊记忆”四个字,是用十年间孩子们写的弯钩拼起来的,最中间那个“雪”字,笔画里还能看见当年李雪掌心旧伤的影子。
“王老板的孙子今年考上了林业大学。”赵老师翻开集子,某页夹着片文竹叶,叶脉的纹路和油库文竹的根须重合,“他说要研究怎么让桑树皮长出更韧的纤维,还说要把爷爷的信刻在纸坊的石碑上——信里说‘欠的已清,剩下的是念想’。”
李雪的指尖抚过那片文竹叶,忽然想起十年前在看守所石缝里挖的那株幼苗。如今它的枝干已能撑起半面院墙,树皮上的刻痕被新长出的木质包裹,只留下圈浅浅的隆起,像账册上被红结盖住的旧账。“老纸工张叔的重孙今天满周岁。”她从柜里取出张桑皮纸,上面拓着个小小的“喜”字,弯钩处嵌着粒文竹籽,“按当年我爸的规矩,满月要赠纸,拓字的墨里掺了松脂,能留到孩子长大。”
沈砚之的车停在文竹丛旁时,正看见李雪在油库旧址埋新的纸砖。砖面拓着“第二十年”,边缘的红绸带是新换的,却和当年那根在阳光下泛着同样的金芒。“老周去年退休了,临走前寄来套纤维检测仪。”她拍了拍砖上的土,霜气在指尖凝成细珠,“说这砖里的纤维,每年都会长出新的纹路,就像树的年轮,能记着风调雨顺,也能记着霜雪雷电。”
纸坊的油灯下,李雪在补记最后一页账册。旧账册的纸页已经泛黄,新添的字迹却依旧清亮,记着:“今日桑田收桑皮三百斤,够造纸百张,其中十张拓‘建’字,赠入学学子。”落笔的弯钩比十年前更圆融,却在收笔处藏着点当年的锐,像被岁月磨过的刀,鞘里依旧有光。
深夜的纸浆池泛起微光,是月光透过纤维的缘故。李雪蹲在池边,看水里自己的倒影,鬓角已有了些白发,像当年纸坊老头的头发混在浆里。她忽然摸到池底个硬东西,捞上来一看,是那半截带头发的捣浆棍,棍头的暗红胶质里,新裹了圈细密的纤维,是这十年间每次捣浆时缠上去的,如今已成了层坚固的壳。
“当年的胶质终于和新纤维长在一起了。”她对着棍头的白发轻声说,像在对十年前的自己说话,“我爸说纤维拧成股才耐烧,人凑成团才耐活——您看,孩子们在学造纸,学子们在学种树,连文竹都在记着往事,咱们没输。”
冬至的雪落进纸坊时,李雪在晒架旁摆了排松脂烛。烛火透过桑皮纸,在墙上投出晃动的影,像无数双手在捣浆、拓字、栽桑。沈砚之推门进来时,正看见她在教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拓“建”字,孩子的指尖缠着根红绸带,是从老槐树枝桠上解下来的,带尾的铜戒指在烛火里泛着暖光。
“这是赵德发女儿的女儿。”李雪笑着说,小姑娘的弯钩已经写得有模有样,“她说长大要当造纸匠,说要把‘李记纸坊’的招牌擦得比阳光还亮。”
沈砚之接过李雪递来的纸卷,是用这二十年的桑皮纸装订的,首页拓着李建国抱着小女孩的照片,纸角的纤维里嵌着根灰白头发——是当年从油库灰烬里捡的,如今已和新纸的纤维长在了一起。“老周说,这叫纤维记忆。”李雪的声音在烛火里有些飘忽,“烧过的、泡过的、撕裂过的,只要还连着根,就总能长回原样。”
离开时,雪已经停了。沈砚之回头望,纸坊的灯光在雪地里像块融化的金子,李雪的身影正站在晒架旁,青布衫的衣角扫过纸页,带起的风里有松脂和文竹的香。远处的文竹丛在月光里泛着银,根须穿透铁皮的地方,新的幼苗正顶开积雪,像无数个“雪”字的弯钩,在年轮深处,向着光的方向生长。
纸间魅影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奥特曼:闪耀的月亮
- 赛罗梦女青梅竹马一个平行世界,女主也是一个奥特曼ooc是一定的,不喜勿喷好作者不剧透
- 3.2万字7个月前
- 诸天美食家:从炼丹到料理的跨次元盛宴
- 当顶级炼丹师误入“诸天美食聊天群”药尘,站在炼丹巅峰的传奇人物,炼丹之术出神入化。一次意外,他竟误打误撞加入神秘的“诸天美食聊天群”。群成员......
- 1.1万字7个月前
- 羡忘:破镜重圆
- 我想带一个人回“云深不知处”带回去,藏起来。
- 0.3万字6个月前
- 在落幕前夕
- (异能、无限流、灵异、死亡游戏)【无系统】【无后宫】【不无敌】不知何时人类早已被卷入灵异,世界即将陷入无尽的黑暗之中。在亡界最终落幕前夕,高......
- 3.2万字2个月前
- 异本
- 1.1万字2个月前
- 女尊当道-d995
- 1.3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