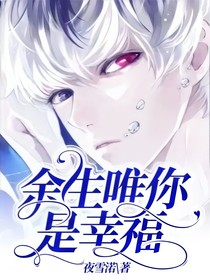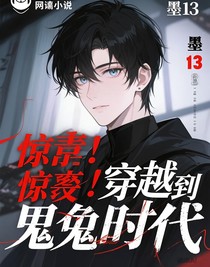透光处的回响 (2-1)
又是一年春深。纸坊的晒架在暮春的雨里泛着潮意,李雪正用松脂膏修补被雨打湿的桑皮纸,指尖的茧子蹭过纸页的“李”字,把洇开的墨痕轻轻压平。架下的青石板上,摆着排新做的拓字板,“建”“雪”“发”“王”……每个字的弯钩都被摩挲得发亮,是赵老师带着孩子们练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成果。
“王老板的孙子来学造纸了。”赵老师牵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走进来,孩子手里攥着半截松脂块,是从油库文竹丛里捡的,“他说爷爷在信里教他,磨松脂要顺着纹路转,就像写字的弯钩,得跟着心走才自然。”
李雪把孩子拉到纸浆池边,看他伸手搅弄池里的纤维。小家伙的手指在水里划出的圈,和当年李建国抱着她在池边画的一模一样。“你看这纤维,”她捞起一缕桑皮丝,在雨光里像条透明的线,“十年前在油库的火里烧过,十年后在这池水里泡着,照样能织成纸——就像人心里的事,藏得再深,也会在某个雨天慢慢浮上来。”
沈砚之的车停在镇口时,正赶上孩子们举着拓字纸跑过。每张纸上的弯钩都迎着雨,像无数只向上翘的指尖。他走进纸坊时,看见李雪在翻那本记满红结的账册,最新一页写着:“王姓孩童今日拓‘建’字,弯钩如雨后新竹,无滞涩。”字迹旁画着个小小的文竹芽,是用新榨的竹汁描的,绿得像能滴出水来。
“老周寄来的化验报告说,油库文竹的根须已经穿透了当年的铁皮。”李雪指着窗外的雨帘,后山的方向隐有绿意,“他说那些根须里检出了桑皮纤维的成分,是当年混在焦土里的纸灰长进去的——植物比人更懂怎么把碎片拼起来。”
雨停时,孩子们在油库旧址的文竹丛里发现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打开时,里面躺着卷被胶质裹住的旧账页,是当年李建国没来得及烧毁的最后几页,上面记着给每个纸工的福利:“张叔家孙儿满月,赠桑皮纸十张,拓‘喜’字用”“李婶老伴忌日,备松脂烛一对,燃之无烟”……字迹的弯钩里还嵌着点暗红,是文竹汁混着的血,和李雪掌心的旧伤在阳光下泛出同样的暖光。
“这些账,我要替我爸补记进新册里。”李雪把旧账页铺在晒架上,用新桑皮纸小心翼翼地托住,“老纸工们说,当年我爸总在账册空白处画小画,画纸坊的晒架,画后山的桑田,画我扎羊角辫的样子——您看,这里就藏着个小小的‘雪’字,被胶质裹了十年,还能看清收笔的钩。”
赵老师带着孩子们拓新发现的账页,拓出来的“喜”字“福”字在晒架上排开,每个弯钩都带着旧账页的韧劲。有个小姑娘忽然指着“雪”字的钩:“李阿姨,这个钩像文竹的卷须!”李雪蹲下身,看孩子指尖点过的地方,阳光正从纸页的纤维缝里漏下来,在青石板上投出细碎的光斑,像十年前那个大晴天,父亲举着桑皮纸对她笑时的模样。
沈砚之准备返程时,李雪送他一沓用新旧桑皮纸混造的纸。最上面那张拓着完整的“李记纸坊”,四个大字的笔画里,旧纤维的焦痕和新纤维的莹白交织,像圈年轮里套着圈年轮。“这是用最后一点油库焦土纸灰做的。”她的指尖抚过纸页,“老周说,这纸的纤维能保存五百年——五百年后,要是有人对着光看,或许还能看见今天的雨,今天的孩子,今天的我们。”
车驶过老槐树时,赵老师带着孩子们在树下唱新教的歌谣:“桑皮韧,松脂香,纸页透光记旧账……”歌声顺着风飘进车窗,和纸页翻动的哗哗声混在一起,像无数纤维在轻轻共振。沈砚之低头看那沓纸,阳光穿透处,旧账页的暗红胶质和新纤维的浅绿竹汁慢慢晕开,最后融成一片温暖的黄,像极了李建国照片里那个晴朗的午后。
纸间魅影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相见与相遇
- 他们从这里开始,又从这里结束只是时间不同而以没有一个相同的梦想,为什么不能在以起呢?他们之间没有结束,只有无数的未完待续而以,他们分开后可以......
- 0.3万字7个月前
- 疯子心理学
- 疯子心理学欣赏一群疯子们在末日的日常(本文后期刀子会很多请各位理性看待)
- 0.8万字7个月前
- 余生唯你是幸福
- 如果爱有界限,那你一定是我的破界之人。夜瞑爵,星爵娱乐总裁,Z市帝王。白络炎,偶像歌手,天之骄子。两人相识于酒店,殊不知这场相遇改变了两人的......
- 8.2万字6个月前
- 坠落下界的我只想过平凡生活
- 下界,这里是上界之中的“失败者”被上界放逐后来到的地方,这里曾经坠落了无数的上界世界泡与上界神灵,各种体系混杂,机械,血肉,恶灵,教会,诡异......
- 2.2万字6个月前
- 棋逸长梦
- 骗子,骗子。骗子!喜欢就直说啊。说再见还真的不会再见了啊—除了你其他人都是棋子
- 0.7万字3周前
- 震惊穿越到诡异时代
- 意外闯入诡异戏班的祁墨染,面对恐怖的戏伶诡追杀,在生死边缘挣扎。此时,清冷神秘的陆凛出现,他身负异能,看似冷漠却心怀正义,后续他们是否能相遇......
- 1.9万字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