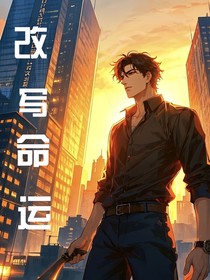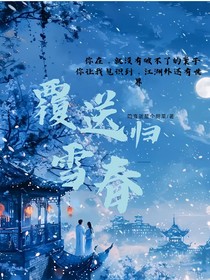纤维织就的年轮
秋阳透过纸坊的窗棂,在晒架上投下细长的光斑。李雪正把新晒的桑皮纸码成摞,纸页边缘的“李”字在光里泛出浅金,松脂墨的痕迹比去年更深了些,像老槐树的年轮又添了圈。小王抱着个藤筐走进来,筐里装着孩子们拓的字,每张都有个倔强的弯钩,最底下那张的“雪”字旁边,画着个举着捣浆棍的小人,是赵老师教的简笔画。
“老纸工们说今年的桑皮纤维特别好。”李雪拿起张纸对着光看,纤维的纹路在秋阳里像条透明的河,“熬胶质时加了新采的文竹汁,比去年更韧——您看,能承受三倍的拉力还不断。”她轻轻扯着纸角,纤维拉伸的弧度和后山桑树枝在风里的弯度重合,都是经得住岁月的韧。
沈砚之的目光落在墙角的账册上。新记的页码已经超过了当年李建国停笔的第三十七页,最近一页记着:“今日还张老纸工后代工钱五吊,其孙拓字‘建’字,弯钩如老桑枝。”字迹的收笔处比去年更稳,少了些尖锐,多了些圆融,像被雨水泡透的文竹刻痕。
“王老板的儿子寄来最后一笔还款了。”小王递过汇款单,附言栏里写着“父嘱:欠的已清,愿桑田长青”,字迹的弯钩和照片背面的“欠的总得还”如出一辙,只是尾端多了点暖意,“他说春节要带孩子回来,看看这片桑田。”
李雪把汇款单夹进账册,指尖划过纸页上的红绸带标记——她在每笔结清的欠薪旁都系个小红结,如今整本册子已像串挂满红果的枝桠。“后山的新桑苗长到齐腰高了。”她推开后门,文竹的枝叶已爬过院墙,最高的那枝顶着串浅白的花,“今年结了文竹籽,我收了些混在桑籽里,老纸工说这样长出的桑树,纤维里会带着点竹香。”
镇口的老槐树下,赵老师带着孩子们拓新做的“纸”字模板。有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总把最后一笔弯钩写歪,李雪蹲下身握住他的手:“想想文竹怎么从石缝里钻出来的,先往下扎根,再往上抬头——写字和扎根一样,沉得住气才能立得住。”男孩的笔尖顿了顿,终于划出个又稳又韧的钩,像极了十年前李建国照片里的桑皮纸纤维。
油库废墟的位置如今种满了文竹,深秋的叶尖泛着点红,像当年未烧尽的纸灰里掺了胭脂。沈砚之看着李雪把块新做的纸砖埋进土里,砖面拓着“第十年”三个字,边缘缠着的红绸带是从旧红绸上剪下的,带尾还留着“始”字的残痕。“老周说这砖能保存百年。”她拍了拍手上的土,“等孩子们长大了,再挖出来看看,就知道当年的纤维怎么长成了年轮。”
纸坊的油灯在夜里亮到很晚。李雪坐在灯下整理账册,窗台上的文竹影投在纸页上,像片晃动的森林。她忽然在旧账册的夹层里摸到个硬东西,掏出来看,是半块被胶质裹着的桑皮纸,上面有个模糊的指印,是十岁的她在油库外攥纸时留下的,和新纸角的指纹在灯下慢慢重合,像两个时空的纤维终于织在了一起。
冬至那天飘起了雪,孩子们在纸坊门口堆了个雪人,手里插着半截捣浆棍,棍头的胶质里嵌着片新叶。李雪站在晒架旁,看新纸在雪光里泛出莹白,纤维的纹路里似乎能看见无数个影子:举着刀的年轻人、仿字的赵德发、躺进枯井的老头、抱着女孩的李建国……最后都化作透光的纤维,在纸页上织成圈温暖的年轮。
沈砚之离开时,李雪送他一沓压平的文竹花。花瓣里夹着张桑皮纸,上面用松脂墨写着:“纤维会老,纸会泛黄,但光永远在纹路里。”纸角的“雪”字弯钩里,嵌着粒文竹籽,是今年新结的,像个等待被春天泡开的句号。
车驶过镇口,老槐树的枝桠在雪光里像幅剪纸。沈砚之回头望,纸坊的灯光在雪雾里亮得像颗星,灯下的人影正弯腰码纸,青布衫的衣角扫过晒架,带起的纸页在风里哗哗响,像无数纤维在轻轻诉说:岁月的账,终会被时光的笔,一笔一画,写进透光的年轮里。
纸间魅影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穿越之改写命运
- 系统:恭喜宿主死了,真是可喜可贺。傅谨琛:滚面对自己爱人徐轩逸的傅谨琛:我好爱你,轩逸————徐轩逸:我要你帮我杀了他
- 17.9万字6个月前
- 震惊!伍六七穿越了!
- 新来的小作者,文笔不怎么好,请见谅⊹
- 0.4万字6个月前
- 覆雪送春归
- 盛唐年间,一场阴谋席卷而来…一场场连环杀人案,杀的竟是妙龄女子;皇宫中失窃的名画和一件珍宝,何去何从?;江湖上风云起伏,却令有人在操控;最后......
- 0.5万字5个月前
- 海贼王:可爱天马
- 私设,禁止以任何形式的搬运、抄袭姓名莉莉·D·星歌称号:
- 16.6万字2周前
- 火影忍者:佐鸣成殇
- 双男主文中图片侵权立删
- 11.9万字4天前
- 风宁愿
- 陆颖凝太傅孙女江南富商外孙女温思敏尚书令幺女苏卿溪定王之女江南富商外孙女
- 0.9万字昨天